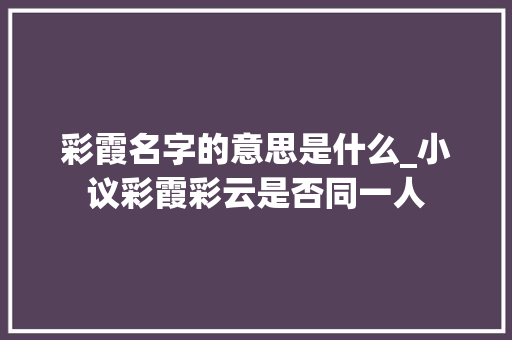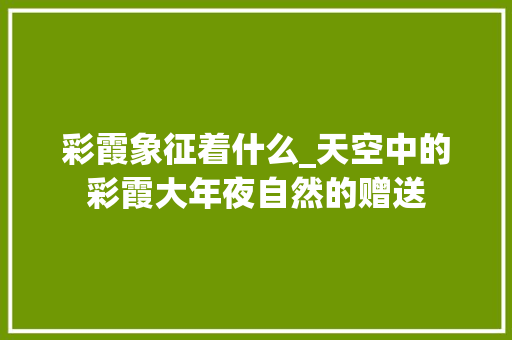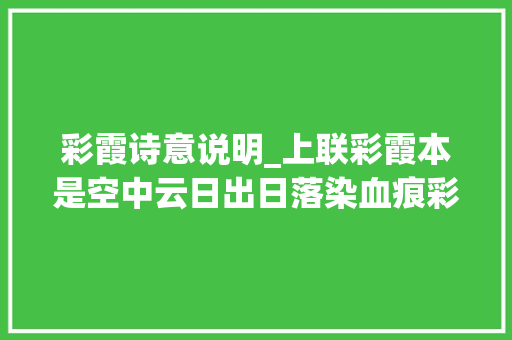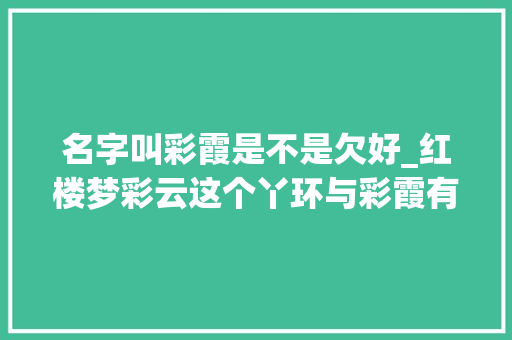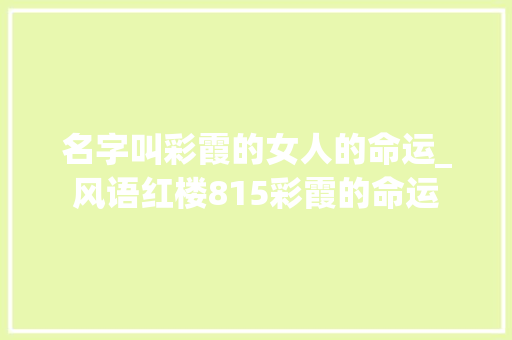她跟漂流瓶跑的时候,把儿子——也便是阿欢——也抛弃了。其实话说回来,叔叔只管恨她,还是把朱欢当成亲儿子对待。
下大雨了,肯定过不了河。叔叔每一次都会从坝上踩水过去,然后背着他又从坝上走回来。有一次,朱欢故意在叔叔背上恶作剧挣扎,差点儿把两个人都弄栽进急流当中卷走。那时候,河水还在猛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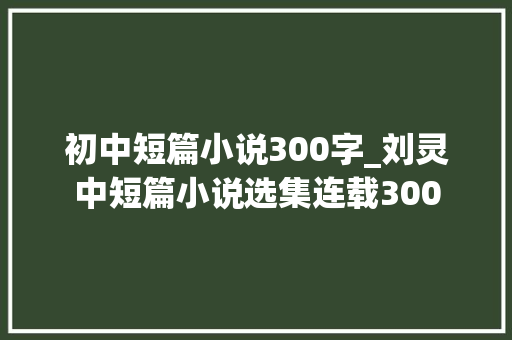
“欢儿,你别动!
”叔叔连头都没敢抬,命令说,“不然我俩都会被大水冲走。”
耳朵边正下着瓢泼大雨衣服湿透了,又沉甸甸的。朱欢假装听不见。他便是故意。
“不能动啊。”他吼。
“叔叔,你在说啥?”
“欢儿,我叫你别动!
”
“我没动。”他说,“我根本就没动。”
“莫非我冤枉了你。”他气急败坏叫喊。
阁下有一个堂哥立即伸手捉住了叔叔的胳膊,五人一齐努力,他们才重新站稳。这样,过了半个月,朱欢就偷偷把堂哥家的两只红公鸡和一只鸭子用奶奶赶场天买回来的耗子药毒去世了。他本来是想毒去世他家猪,但耗子药剩太少,也不想让他丢失过于惨重,随便给他点教训就够了。朱欢后来又想在叔叔喝的茶里放进点什么,当真在坡上让他找到了,先晒干,偷偷搁搪瓷缸里。结果,爷爷欠妥心把茶水喝了,翻白眼,虽然说没去世,也弄得上吐下泻。
喝茶的时候,“这茶水的味道有点怪怪的,臭了。”爷爷说一句,就没敢多喝。
阿欢想起景象很闷,当时打了个炸雷。持续串车轮子在大家头顶上滚过,带着股炸药味道。叔叔大概是嗅出来了一种去世亡气息,也就不敢连续在家呆。他两口子跑到广东打工去了,连过春节都没有再回来。诚笃说,阿欢现在最想整顿的人并不是朱彩霞——已爱上她了——而是他亲叔叔。
可惜了,鞭长莫及。
反正,朱彩霞锁在磨盘上跑不掉。
现如今,他能够理解,直接站在朱彩霞面前,非常沉着地把带过来可以吃的、干净的东西带给她。有时候乃至是蛮横地硬塞在她手上。“我撑去世你!
”他恶狠狠说。阿欢脖颈僵直,面庞灰冷。由于,当时她顾看地上十几只黄蚂蚁正跟一只金龟子的搏斗了。金龟子也是他捉来偷偷摆放的。
博她一笑。有可能便是想利用这个办法吸引她的把稳力,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把锁砸烂。为了保护锁(她最值钱的财产)可能会跟他冒死。他溘然想到个搞笑剧情,一但放了她,先带朱彩霞去把叔叔的小木楼烧掉,迫使他无家可归。然后再杀她。
“我想帮她彻底解脱。”
再说,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就会连累好几家烧屋子,说不定是全体寨子。别个是无辜的,但他现在暂时管不着。反正又不是由他亲自点的火,内心深处少有愧疚,他想这个策划好,别人怎么也怪不到他头上。倒是反而有点担心,被锁在一个沉重磨盘上十把年,别人夸年夜说朱彩霞放过火——看上去不像——会不会是乡下谣言。
她会用打火机?会划得燃火柴?
他思忖,统统材料都会事先替朱彩霞准备好的。只须要选一个天干、风大的晚上就成了;彷佛把她开释已经是满有把握。至于引火的东西呢?毛桠柴,最好,再替她弄半瓶石油。阿欢清闲清闲坐在磨盘上,看她狼吞虎咽吃着他偷来煮熟的鸭腿。
朱彤霞彷佛长得个头一贯都没有她姐高,也可能是瘦了才显高的。阿欢摇头,嘲笑她光用饭不长肉,两姐妹一样,一准儿她比姐更软弱,当然也没有朱彩霞的皮肤白。但她的头发比姐的长,更光滑,每天都梳,当妹妹的头发乌黑发亮。谁乐意帮锁在磨盘上的人梳头呢,而且洗干净梳了又给哪个看。朱欢发觉自己很喜好瞥见妹妹长长的、用塑料发箍箍起来的头发。阿欢乃至有点吃惊。他想起朱彩霞从前(小时候)头发也是乌漆麻黑的,没有妹妹的亮是由于住在灰堆上,还有草渣。他更喜好闻她们头发散发出的一股皂角水气味。
古老的皂角树在桃花寨背后半山腰上,多得有好几十棵,看起来像是满山遍野。有人还拣皂角赶场天卖,问题有谁乐意买?现在,朱彩霞的头发比从前(小时候)长得长了一些,朱彤霞偶尔也会帮她梳头,用一根缠毛线胶圈替姐姐扎了起来。
“别总爱说小时候小时候的,阿欢你喜好冒老,实际上,你没有我姐年事大。”
“她多大?”
“我不知道,反正比你和我都大。”
“那是当然!
”阿欢承认说。
如果头发太长了,就动手给她剪掉一些。长了洗的时候不好洗,她又挣扎,杀猪似的尖叫,不管她,又怕成了龙卷窝。
朱彤霞替姐姐洗头长期用的是洗衣粉,她说,皂角水洗不去世她头发里那些虱子蛋。
但洗衣粉还是洗不完的,连虱子都杀不去世,你说气人不。除非是利用农药或者帮她剪个秃顶。她咯咯咯笑起来,说就像一个电视剧里边的和尚。不对,她当尼姑才精确。她家的黑白电视机早都修睦了?朱欢实在并不知道,打早年次她妈中风三四年了,他都没有再走进过那间伯妈坐在那里的厢房,包括厨房。他读初中二年级下雨那天,阿欢又被朱彤霞从后门领进去。
“我不喜好看到你姐剃秃顶。”
“那就把头发给她留下,让她长虱子。”
“也讨厌农药味。”
“这个啊,我还舍不得摧残浪费蹂躏。”
这是末了一次偷偷溜进她家厢房或者说厨房了。阿欢已经下过一百次这种决心。
朱彤霞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她要留在家照顾瘫痪坐门背后的母亲和锁磨盘上那个疯子姐姐。他害怕看到伯妈,虽说她整天半睁不开眼睛。她彷佛百事不管。
她身上皮肤也没变,反而,脖颈更白,也更光滑了。阿欢和朱彤霞躲开她母亲的监视,她说,我要你亲我,你都亲过了我姐姐,不然我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他俩都姓朱,还是亲戚,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些他们都知道。不然他就带她跑出去打工了。阿欢咬住她薄薄的耳垂,闻着那一股好闻的皂角水气味,在她耳朵边低声细语唠叨:“我会的,我会替你把事情办完。你找一把铁锤把狗链子的锁砸烂,我就把她哄到水磨房去。”把她推下大水渠就成了,这样朱彤霞不只心愿达成,也轻松。
“还是把她留下来,让她活着。”朱彤霞说,“等她锁在烘房门口,习气了。再讲我睡觉才踏实,也睡得着。”
有一次阿欢差点咬烂她舌尖。
他特殊惊异。在早两三年的时候,朱彤霞总喜好催他动手,会问他:“你究竟帮她还是乐意帮我啊,受不了啦。你答应我的事情,到底啥时候才肯干。看到她烦。”
阿欢问:“你现在怎么又对她好了呢?”
看来当月朔向拖着,这办法是对的。
“便是不想了。”
“你见告我一个情由。”
他实在猜到的,怕她妈溘然去世了,丢下朱彤霞单独一个人,有可能她更加孤独。
“朱彩霞可以打个伴。”
“我以为也是。”
“我警告你,警告你,不准再想这事。”
想过,所有办法貌似都行不通。他却对她说:“水磨房又不在乎多一个鬼。”
他当时想,从来就没有打算真干,本身便是帮她两姐妹,彼此有依赖。都到了这耕田地,彷佛早都弄假成真,也就由不得任何人不愿意。仔细想,这事在心里已生根萌芽多年。她说:“我看她都快好了。”
恍然大悟,朱彩霞确实是多年没再咬人。
差不多便是在那一年,朱彤霞把她姐的长指甲整整洁齐剪掉了。三伯妈大概听到了厨房里边的动静,在厢房有气无力叫喊:
“彤霞,彤霞,你到哪去躲煞气?赶紧看看,碗柜里是不是钻进去一个大耗子。”
她咕噜咕哝,那种话也只有朱彤霞才懂。
朱欢就抓紧韶光从厨房后门溜掉了。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阿欢有苦处总喜好找坐灰堆背靠土墙或者磨盘的朱彩霞说叨,一边看着她啃完火烧包谷。有好多次他半夜三更也去,给她带个粑粑或者馒头。连搂抱她都蹑手蹑脚的,她也不吱声。他把想烧掉叔叔屋子的打算见告她,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点都不遮盖,压根也不须要朱彩霞回应。说完后朱欢觉得到轻松了许多。她光顾着吃,也不知道听没听懂。每次朱欢直接要呆到鸡叫头遍,然后,他就从坝上过河回民族中学。
后来,有一次他半夜去,被朱彤霞堵在间隔小磨房不远拖沓机路中间,那天月色很好,面庞表情都看得一目了然。她说:
“我警告你,再次警告你。别祸害她!
”
她那意思恐怕是说不准让朱彩霞有身。但朱彤霞迟疑五分钟后又说:“我见告过你必须要让她活下来。你再敢胡乱来,我就到派出所告。到处宣扬,让你臭名声。”
“别这样,”他说,“我还想考大学。”
“晓得就好。”朱彤霞说。
朱欢怔了怔,在路中间溘然伸双手把她抱紧,想拖她进水磨房。朱彤霞没有反抗。
他闻到了那股浓浓皂角水气味,鼻子在她光滑头发上到处搜索,探求。非常好闻。
就这样,朱欢读高三上半学期的时候,有一天他从县城坐地巴车回来,大老远就瞥见了蔡涛在他对面。两人站着,横目而视。桃花寨的特大新闻。当他还连续走在枫喷鼻香窝小学阁下马路上正胡思乱想,就听那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卖完鱼跟他一起坐车回来的塌鼻子说,他们河对门的疯姑娘朱彩霞招了一个上门半子。四个同车搭客差点惊掉下巴。“她可能招上门半子?”
“怕是说彤霞哟。”
“她那种,谁敢要她!
”
“男多女少,是个女的都有人要。”
“她长得那样俊秀。”
“天呐,俊秀能当饭吃。”
“她家缺个劳力。”
朱欢不信,但他没敢多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