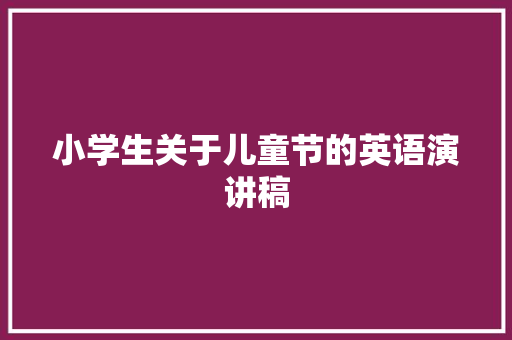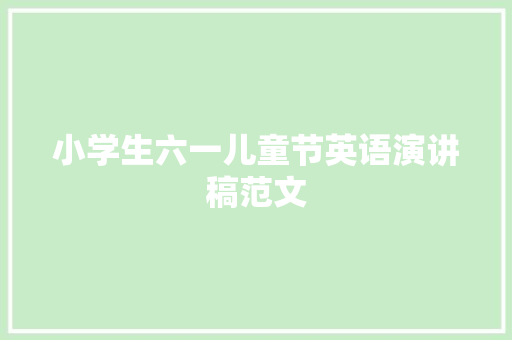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我被一面写满文字的墙吸引。从左而右,每个年份下面都记录着当年世界发生的重大武装冲突和自然灾难,几近环绕了整层圆形展厅。入口处的1859年是起点,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写到的那场战役距今正好150年。截点在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后面的空白只是暂时的,因为所有发生过的战争和灾难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程度评估以后,才能决定是否永久记录到这面墙上,这种评估需要大约20年时间跟踪比较。
即便标准严格,目前可见的每一个年份下,战争和灾难也都是长长一串,白墙黑字肃然压迫着它面前的观看者。那一瞬间我感到挫败和绝望,脑子里蓦然跳出梁漱溟先生一本谈话录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反应是行动,是帮助”
1862年7月,60岁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流放中写完他的《悲惨世界》,出版后洛阳纸贵,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让人道主义的悲悯和拯救成为读者最动容的谈资。这年11月,34岁的瑞士公民亨利·杜南也在日内瓦印行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本记录个人亲历的小书,4万多字,讲述3年前一场惨酷的战争以及后面两星期里发生的战场救助。杜南是个商人,没有出版商会对他写的这样一本书感兴趣,这一点他早就想到,自己掏钱印了几十本,寄给朋友,还有他能想到的贵族和王室成员——他觉得,这些拥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可能对他希望达成的目标提供帮助。这个年轻商人的设想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也不合他当时无足轻重的身份:他呼吁成立一个能被国际协议保护的伤兵救助委员会,在所有战争中维护一定的人道标准,保护生命和尊严。
1862年,就这样先后诞生了两本将被世人永远纪念的人道主义杰作,影响着他们的时代直到100多年后的世界。维克多·雨果和亨利·杜南,身份悬殊,年龄也悬殊,却同样渴求世人能够认同和追随自己的理想世界:仁慈、善良和博爱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
在日内瓦总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人力资源部主任马库斯·多尔德谈到创始人杜南时充满敬意。多尔德在非洲和亚洲武装冲突一线执行任务17年,经历过卢旺达大屠杀,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到战场杀戮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巨大冲击。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杜南本是一个商人,途经意大利为的是生意、是利润,但他的现实世界在目睹了他人苦难后瞬间翻转,人道运动成为他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也许我可以这样说,能够如此谦恭地去帮助他人的人,一定来自天性。不管怎样,杜南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博爱思想的影响。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并实践为一个运动,19世纪的博爱思潮显然是一块足够滋养他的土壤。”
杜南出生在日内瓦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向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的工作人员打听杜南故居如今在哪条街道,回答说不太清楚,平时也很少有人问起。如果想了解他的生平,多数人会选择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参观,这里每年接待将近9万人。博物馆紧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对面坡脚下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只隔了一条马路。和其他博物馆不同,总面积3600多平方米的三层空间全部设在地下,里面展示了1万多件杜南个人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历史档案、纪念实物。瑞士还另有一个亨利·杜南博物馆,建在海登。那座小城是杜南最后20年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孤独离开人世的地方。
从小随母亲到贫民窟救济穷人,杜南天性中的慷慨被不断放大。成年后,他加入了基督青年会。在杜南还是少年时,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创办的这个组织就开始影响欧洲大陆,也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教徒的欢迎。杜南成为瑞士基督青年会的创办者之一,常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去参加活动,但根据现任“日内瓦亨利·杜南协会”主席罗热·迪朗的研究,这个教会青年组织主要从事文化方面的活动,没有涉及多少人道救助工作。1853年,26岁的杜南在阿尔及利亚开始了他作为商人和银行家的职业生涯。
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据为殖民地,吸引了很多年轻冒险家去做发财梦。如同多数日内瓦公民的家族历史一样,杜南祖上也是从法国避居瑞士的加尔文教徒。拿破仑时代法国在欧洲重新变得强大,杜南希望恢复自己的法国公民身份。他像法国青年一样跑到阿尔及利亚去创业,依靠家族在日内瓦上层社会一些朋友提供的资金做起了玉米贸易,还开了采石场。1858年杜南向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递交了恢复法国籍以及公司用水权的申请,无人理会他。杜南决定自己去面见拿破仑三世,陈述开发阿尔及利亚的设想。
已经可以看到,在青年杜南身上,人性和神性、生而平等和强权崇拜,就如同他所处的19世纪欧洲一样缠杂难分。他同情身陷苦难之人,在北非6年最爱读的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激烈反对贩奴贸易和奴隶制,但他也发自内心地仰慕强权拿破仑三世,对欧洲各国王室以及上层社会十分认同。当人道主义者雨果因为抨击拿破仑三世而被迫流亡的时候,人道主义者杜南却对这位法国皇帝抱持敬意,带着致敬信从阿尔及利亚赶往前线。对青年杜南产生重大影响的,更多是文艺复兴时期萌生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人道理念,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所主张的平权思想并不相同。如果把杜南在1859年后所做的事情放到整个19世纪欧洲的思想背景里去观察,他的设想和行动实际上是对早期人道主义观念的现实实现,即肯定并寻求一种为了人的普遍性价值和尊严。
传记文章中提到,在杜南生长的年代和从小生长的阶层,周围人热衷讨论的问题是废除死刑、改善监狱条件、增加受教育的机会,作为虔诚教徒的母亲则带他看到穷人的世界并懂得悲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性冲击神性。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为欧洲描绘了理想王国,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称其为“华美诺言”。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这种人道主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各种思潮都围绕着人本主义蔓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希望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把主观精神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这些,都影响到杜南精神世界的形成。
1859年6月24日,杜南路过了索尔费里诺,一个即将改变他命运、也因为他而影响世界150年的意大利北部小镇。一心要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兰西帝国建功立业的日内瓦公民杜南,偶然目睹了19世纪伤亡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历史记载,法、奥双方投入兵力30万人,在长达15英里的战线上血肉相搏15个小时,死伤4万多人。3年后,杜南在他的《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看见的可怕场景:伤兵被丢弃在战场上,炮车和骑兵马队从他们身体上无情轧过,数千人因为缺少包扎、药品和食物哀嚎死去。杜南此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来此地的目的,他跑去面见法军指挥官,说服他释放战俘中的奥地利外科军医,让他们为伤兵动手术救命。在附近村庄一位神父的帮助下,他动员组织了当地几百名妇女和路过的人把4000多名伤兵安置到教堂和村民家里。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滞留两个星期,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包括写信请求日内瓦的朋友们寄送衣服、食物和急救药品。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的办公室里,全球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和我谈起150年前杜南做的这一切,他说:“杜南身上最让人铭记的地方,是当他在索尔费里诺面对可怕的受难场景时,第一反应是行动,是帮助。他的不平凡,是他不满足个人做这样一次善事而由此努力推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立,并促成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签订。”杜南回到日内瓦后,很多有身份的人邀请他到家里甚至宫廷里做客,讲述索尔费里诺的救助经历。如果到此为止,对商人杜南来说就是一个完满的结局——荣誉、身份、友情、信任,他成了日内瓦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人,财富也将随之而来。但杜南觉得他还应该做得更多。3年后他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后半部分写下了自己对人类战争的思考:“在一个有着诸多进步与文明的年代里,我们也不会幸免于战争,因此,加快步伐,用人类的文明去防止或至少减轻战争的恐怖,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