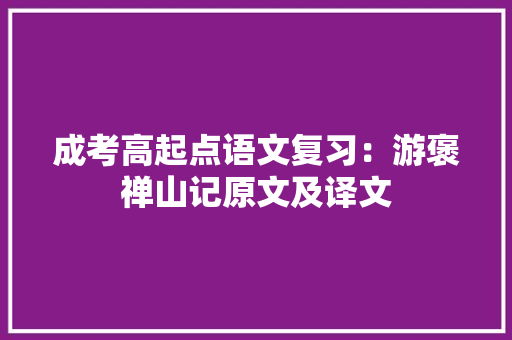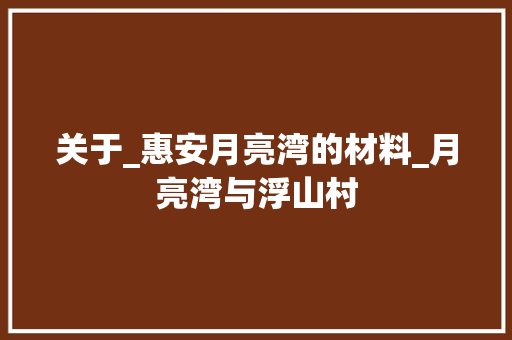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师,数言白云、浮渡之胜,相期筑室课耕于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犹未归,独与宗六上人游。每天气澄清,步山下,岩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华严寺门庑,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释,莫可名状。将行,宗六谓余曰:“兹山之胜,吾身所历,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时,士女杂至。吾常闭特室,外键以避之。夫山而名,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祸作,余牵连被逮,窃自恨曰:“是宗六所谓也。”
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圣恩,给假归葬。八月上旬至枞阳,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宁,因展先墓在桐者。时未生已死,其子移居东乡;将往哭,而取道白云以返于枞。至浮山,计日已迫,乃为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会于宗六之居而遂行。白云去浮山三十里,道曲艰,遇阴雨则不达,又无僧舍旅庐可托宿,故余再欲往观而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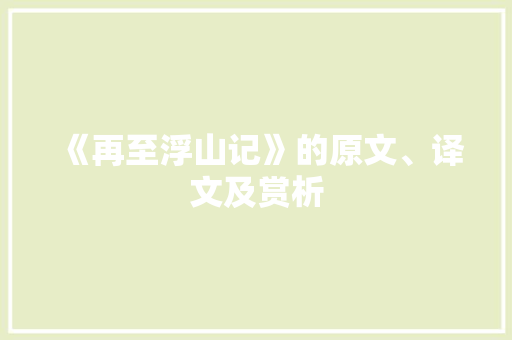
既与宗六别,忽忆其前者之言为不必然。盖路远处幽,而游者无所取资,则其迹自希,不系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粤间,与永、柳之山比胜而人莫知者众矣;惟子厚所经,则游者亦浮慕焉。今白云之游者,特不若浮渡之杂然耳。既为众所指目,徒以路远处幽,无所取资而幸至者之希,则曷若一无闻焉者,为能常保其清淑之气,而无游者猝至之患哉!然则宗六之言盖终无以易也。
余之再至浮山,非游也,无可记者,而斯言之义则不可没,故总前后情事而并识之。
译文
从前我的好友左未生、刘北固在京城,多次说白云、浮渡是当地名胜。曾相约一道在那里建个房子、种种地。康熙己丑年,我到了浮山,左、刘二位君子外出还未回来。我就独自与名叫宗六的和尚一道出游,每当天朗气清之时,我们就走到浮山下,浮山的峰影倒映入方形的池塘,等到月亮刚刚升起时。我们就坐在华严寺门楼或廊下,望着浮山的最高峰出现在大叔的树梢,感到心神完全融汇于优美的自然景象之中,那种美不可言喻。我要走了,宗六和尚对我说:“此山之优美,是我所从未亲身经历过的,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恰逢春天之时,男男女女就纷至沓来。我就常自己躲在独室里,锁上外门来避开喧嚣。山有名,则游人杂至,就像这样破坏了此地的优美清静。”辛卯年冬天,《南山集》之祸爆发,我受牵连而被逮捕,私下里独自遗憾的说:“这跟宗六和尚所说的山有名泽易遭败坏的道理相当!”
又过了十二年,雍正甲辰年,我才承蒙圣恩请假回乡办理先人坟墓迁葬等事。八月上旬到了枞阳,我选择吉日把祖父的灵柩改葬在江宁,于是先察看在桐城的祖先墓地。当时左未生已经死了,他的儿子移居在东乡。我要前往哭奠,就取道白云山,然后返回枞阳。我先到浮山后,算着时间已经很紧张,就相约在某一夜相见,我就招来左未生的儿子秀起在宗六和尚的住处相会。然后就出发了。白云山距浮山三十里,道路曲折艰难,每逢阴雨天气就道路不通。途中又没有僧舍旅店可以托身住宿,所以我再想前往观赏浮山也是不能了。
与宗六和尚分别后,我忽然回忆起他前面所说的话,想想也不一定对。如果路途遥远地处幽僻并且游玩这有没有可以借助的东西,则它情况自然不为人知,与山有名无名也没有关联。接着又想到楚、蜀、百粤这些地方的山水。和永州、柳州之山水同位名胜但很多人却并不了解,只是因为柳子厚经过了那里,于是前去游玩这也就慕名往游了。现在白云山的游人,还不如浮渡山那样人多混杂。这里是被众人纷纷推荐,只不过因为路途遥远、地处偏僻,途中有无所借助,所以有幸到达的就少了。既然这样,哪如全然不被人所知,又能常常保有其清静优美,并且没有游人突然到来的祸患呢?这样看来,宗六和尚说的话无法更改,到底是正确的。
我再到浮山,不是为了游玩啊。也没什么可记的,但这其中的含义却不能埋没,所以就总结了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一并记下了它们。
赏析
方苞的记游散文不多,文集今仅有数篇。这些作品,一般都不单纯写景,而常借景抒杯,表现他对人生的见解。写景中常兼以议论。在这一点上,与戴名世的某些记游散文有类似之处。此文借写游浮山发了一通名山因其胜而反被败坏的感慨,文中点出他在“《南山集》案”中的遭遇,可见其感慨其实不在名胜,而在人生,说明对“《南山集》案”,方苞是始终耿耿于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