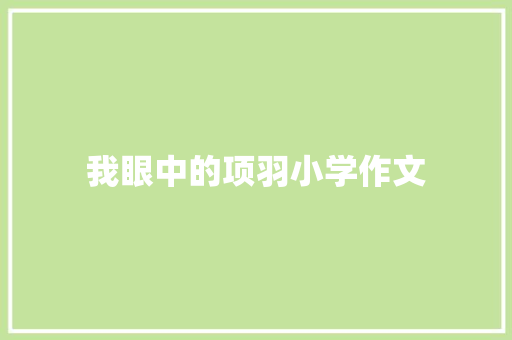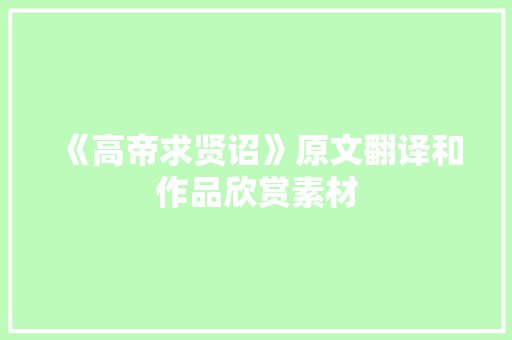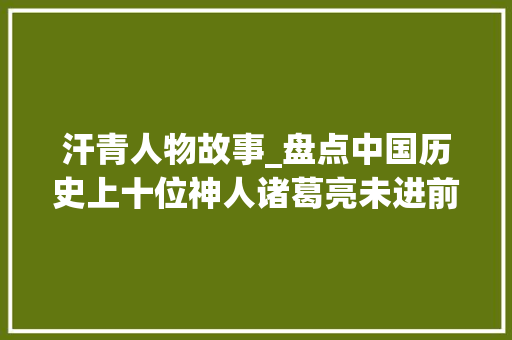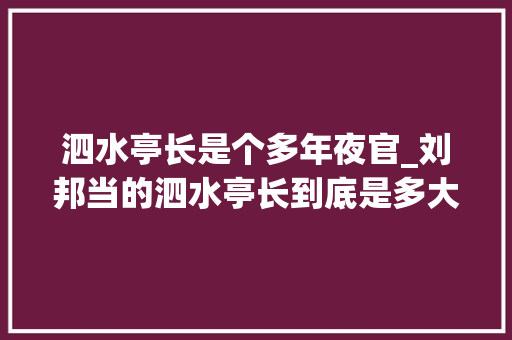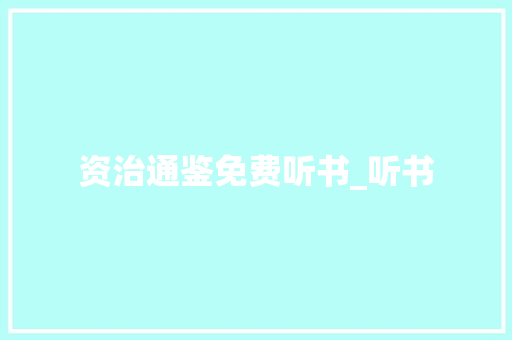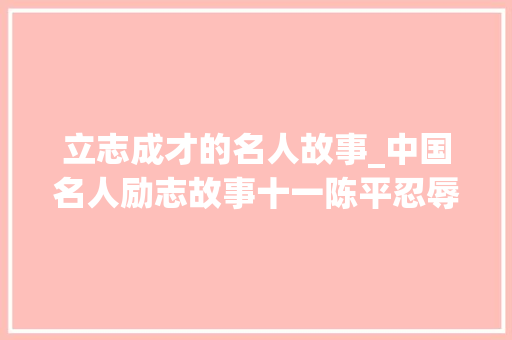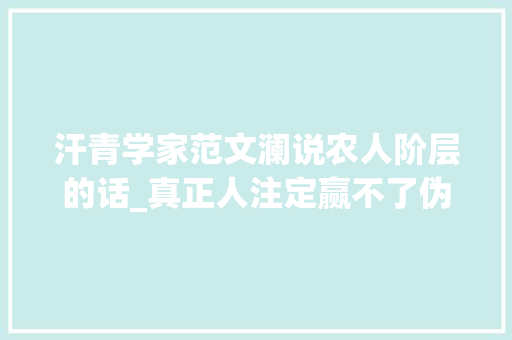刘邦家族间隔战国时期最顶级的“学问家”,远比其他人近得多。
他的幼弟刘交,受业于浮丘伯,是大儒荀子的再传弟子,更故意思的是,这样一位风骚人物,在《史记·楚元王世家》中没有一笔的业绩,反倒是“羹颉侯”的得名故事写得绘声绘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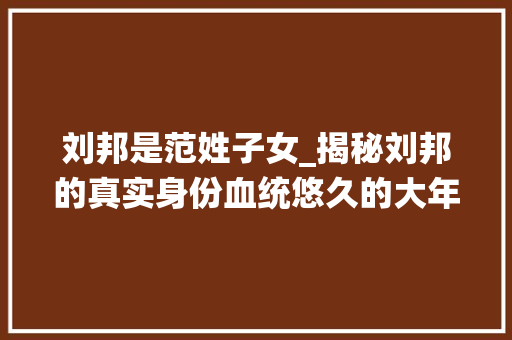
如果没有《汉书·楚元王传》,很多事实可能我们永久无从知晓: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主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
这里详细写明了楚元王刘交的师承,又提到了兄弟四人,伯、仲、季、交,刘伯早去世,在景驹自主为楚王时,刘邦留二哥刘仲与审食其守家,带着少弟刘交和萧何、曹参一起见景驹,又碰着了项梁,一同在薛地拥立了楚怀王,自此后,刘交参与刘邦一系列的战事,直到刘邦称帝,仍与卢绾这个“发小儿”一起“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也便是最亲近的个人参谋和传声筒。
也便是说,刘交在汉初得天下的过程中是绝对“亲贵”的人物,在《史记》中却不见一字,正好印证了三解在《七国之乱:一个复仇者同盟的集体自尽》文中的判断,在“诛除诸吕”的大变革时期,这位宗室父老站在了齐王刘襄一边,在之后的文帝一脉统治下,属于被“禁忌化”的人物,直到改朝换代,很多信息才重新面世。
这些都是题外话,刘交的主要角色,正好解释,汉高祖并非厌弃“儒学”,正是由于幼弟的“多材艺”,而对“儒生”的眼界过高,又通过他秦吏本性的“实用主义”而有所取舍。
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大略单纯。……叔孙关照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这两段话都能看出来,刘邦对付“繁文缛节”的厌恶,以是,讨厌“儒服”,讨厌“繁礼”,那么,他的这种讨厌的来由是什么?
正好是“知儒”,也就类似于墨子“非儒”,实在学儒之后看到了儒家哀求的“厚葬”而愤怒,由于理解,以是厌弃,就算他本人不理解,荀子的再传弟子,汉初诸多儒学大家的养活人——楚元王刘交也不理解?
至于说刘邦作为“秦吏”对儒生的厌恶,完备可以理解,一贯到东汉年间的王充写《论衡》时,在东汉这样一个“儒化程度”远远高于战国、秦、西汉的时期里,仍旧可见对儒生的“厌恶”,见《论衡·程材》:
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
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落,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
这两段话比较有代表性,前者说的是“地方长吏”选用属吏中的“文吏”与“儒生”之别,“文吏”能够完成繁芜的业务,能完成“长吏”交付的职责,以是,“长吏”尊重“文吏”的能力。而“儒生”则哆抖动嗦地不能承担烦剧的事情,在领导有困难的时候,无从效力。
“力无益于时”,自然就没有官职升迁,而“长吏”又以官来考察你的才能,世俗自然会高看文吏而鄙薄儒生。
后一段话,则是说,世间有耿介之节操,对“长吏”进行行为道德匡正的,每每是儒生,而阿谀奉承,顺意取容的,每每是文吏。以是文吏胜在能办事上,却在“忠实”大节上有亏,而儒生的节操精良,却在奉公称职上差得多。
把稳,《史记·六经叔孙通列传》中也有类似“力无益于时”的话:
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贤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太史公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革,卒为汉家儒宗。
实在总结一下上文一大段,便是俩字:
“没用”。
涉及详细业务、职守,儒生百无一用,身为“秦吏”的刘邦当然深知这一点,至于行为匡正,叔孙通、陆贾、刘敬、郦食其都有效验,并未由于他们的儒者身份而受到排斥,至于制礼作乐,也要等天下大定之后才有必要,这时候,任用、赏赐起来也绝不暗昧: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
刘邦不是不懂,只是没到时候罢了。
在过往的讲述中,刘邦的“楚人”身份非常时髦,证据大概多,包括用“楚爵”、“好楚服”之类的,但是,《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条有趣的材料: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天子。各有时。
刘邦在长安设置的女巫,包含了“梁巫”、“晋巫”、“秦巫”和“荆巫”,在这之中,显而易见的是“梁巫”地位最高,卖力“祠”天、地等,而“荆巫”排位最末。
对付这条记载,《史记集解》中注释:
应劭曰:“先人所在之国,及有灵施化和颜悦色,又贵,悉置祠巫祝,博求神灵之意。”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晋,故祠祝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
意思便是,这些国别的“巫”,正是刘邦先人迁徙所在之国,先祖范氏世代在晋国出仕,以是有“晋巫”,范氏的支流在秦国为刘氏,以是有“秦巫”,刘氏随着魏国迁都大梁,以是有“梁巫”,后人徙居丰邑,丰邑又属楚国,以是有“荆巫”。
对此,李祖德在《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对付这段记载中表示的刘氏先祖迁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刘邦先人公元前430年被魏国所获,移居大梁,年夜公元前275年避秦国进攻而迁楚国丰邑,距刘邦出生19年或28年,而据三解《实在你一点都不理解刘邦》考证,应以28年为确。
刘邦家族真正在丰邑的韶光并不长,以是《汉书·高帝纪》中说“其迁日浅,宅兆在丰鲜焉”,也便是一家祖孙三代,其祖父丰公、父亲刘太公、刘邦本人。
也正由于如此,刘氏先人宅兆在“梁”的韶光远远超过在“荆”,“梁巫”的地位也远远高于远祖所居的“晋巫”、“秦巫”和自身所居的“荆巫”。
不仅如此,李祖德还指出,“枌榆社”应为刘氏祭祖之“巫社”,按照礼法,“家”的“社稷”要植树分明爵位,“枌”是一种白色的榆树,还是“榆”,而“士”家种“榆”,则刘邦一族当属“士”的阶层无疑。
由于有传承,有谱系,以是,刘邦家族有“氏”,属于范例意义上的“六国旧贵族”。
在司马迁的时期,已经明言姓氏稠浊,不再遵照先秦的古制,出土的汉简中也表示出姓氏合一的特点,而在史籍和律令公函中,每每又只称“名”,不称姓氏,也就导致了秦朝和之前的战国末期是否也已经普遍性不在分别“姓”、“氏”而颇多辩论。
但是,正如在《六国旧贵族复辟毁灭大秦帝国》一文中引用的里耶秦简“户籍简”中的记录,“荆不更”与“不更”的最大差异,该当便是名前有“氏”,而在《史记》记录的秦末大乱之中,却没有一个没有“姓氏”的人物,反不雅观出土简牍,“无氏者”绝对占大多数,当然,这也与干系秦代简牍多为基层政府运作干系的档案、公函有关。
也便是说,要么,《史记》上记录的“大人物”们,都有后人给他们“添上”了“姓氏”,要么,便是生动在秦末汉初历史舞台上的人们,至少能够留名青史的,全部都是“士”以上阶层的人物,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哪怕是陈胜,也是有“氏”、有“字”、有“爵”的“诸侯子”,所谓的“秦末农人叛逆”,仍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身份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