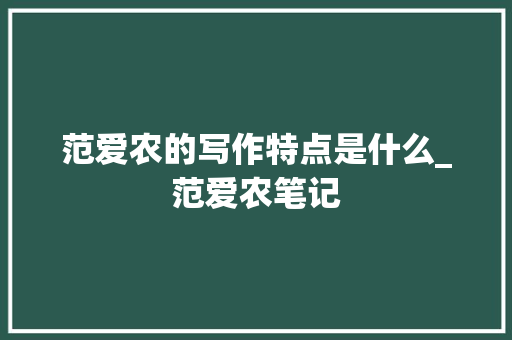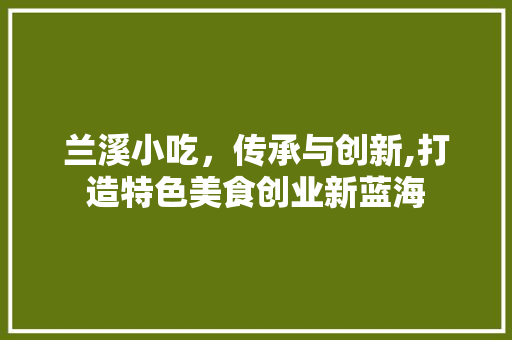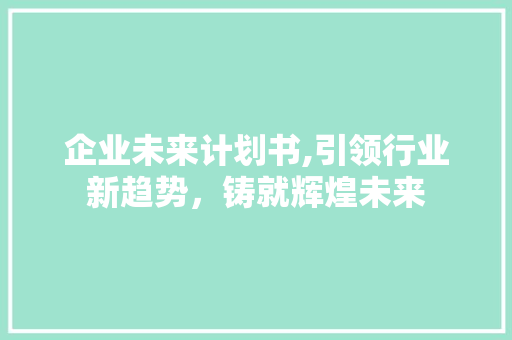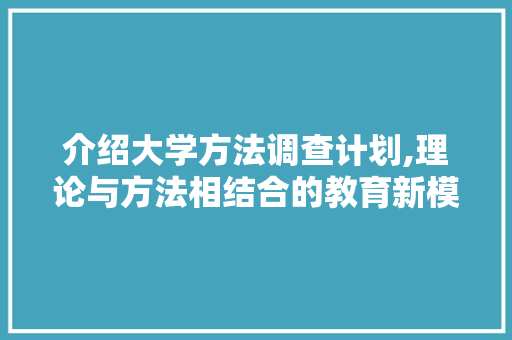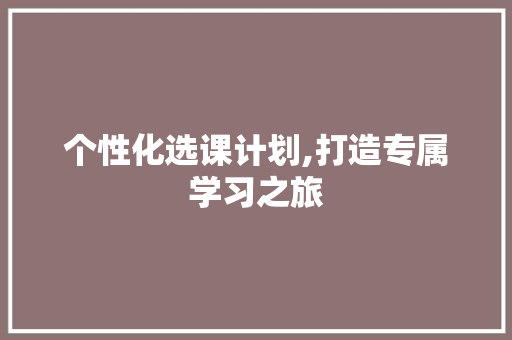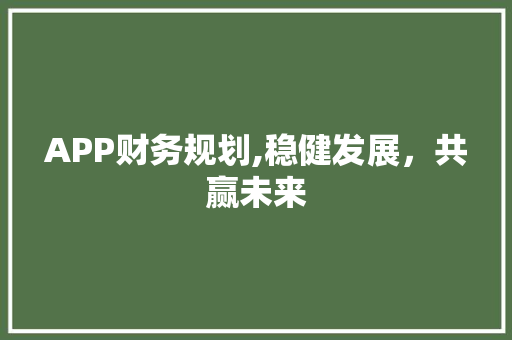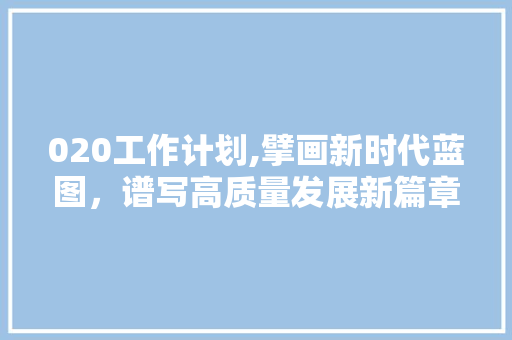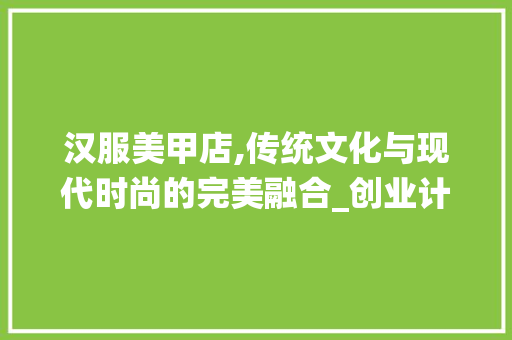在东京旅舍的时候,每天都和报纸打交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还有关于社会琐事的《二六新闻》。溘然有一天来自中国的电报:安徽巡抚被刺杀。
大家研究刺客来历:徐锡麟。预测刺客被极刑或者连累家庭。后来秋瑾被害,徐锡麟被挖了心,民气很愤怒。几个人秘密开会筹集川资,他去接徐伯荪家属。同乡会,凭吊义士,骂满洲。有人主见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无人性。涌现发与不发的不合,我主见发,范爱农主见不发“杀的杀掉了,去世的去世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范爱农引起我的把稳: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渺视。打听他:徐伯荪的学生。发电报的事少数服从多数,发电报的居多,又由于推出拟稿人而产生抵牾。他以为主见发电报的人拟稿,我以为这话像是针对我,便提出由深知义士平生的人去拟稿。不欢而散,两个人都没有拟稿。从此以为范爱农很离奇,很可恶。要革命必须撤除像范爱农这样的人。韶光长了逐步淡忘,从此再也没见面。知道革命前一年的春末忽然相逢,相互的嘲笑和悲哀不溢言表。他有了白发,穿着寒素,谈起过往,没钱不能留学,返国后受到歧视,排斥,伤害,甚至险些无地自容,躲在乡下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有时以为朝气烦闷就进城透透气。他见告我他爱饮酒,后来他每次进城都会找我,我们一起饮酒,非常熟习了。喝醉后说一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还聊起曾经反对我的往事。问他那一天专门反对我是什么缘故原由,他说一向讨厌我,是从那次在横滨我看不起他开始的。大概七八年前,子英约我去横滨接留学的同乡,由于检讨行李里带绣花鞋,火车上相互让座跌倒这两件事,我不经见地摇摇头让他误以为我看不起他。误会解开了,绣花鞋是师母的。冬初的时候,景况更窘迫。武昌叛逆,绍兴光复往后,范爱农进城,那笑颜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不饮酒,同去看光复后的绍兴。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旧乡绅组织的军政府,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器司长·········都督王金发让我做了校长,范爱农做监学,不大饮酒,也很少工夫谈闲天。有一个听过我讲义的少年须要以我,子英,德清三个人为发起人办一种报,我答应了。五天后见报,开头骂军政府和里面的职员,又骂都督········有认为我拿了都督的钱办学校,还骂他,都督会暗杀我。事实证明都督没有要杀我,然而学校经费是不会再给了。得知爱农的一种让我很难堪:收了王金发的钱,还要连续骂。我去验证事情的真假,的确是真的。我和他对质,我认为不该收王金发的钱,而司帐认为是股本,我认为是贿赂,不是股本,司帐依然认为是股本···········我没有再说下去了,虽然我不附和。怕他会说我太爱惜不值钱的命,不肯为社会捐躯。凑巧许寿裳写信催我去南京,爱农也附和。辞职不做校长决定去南京,接任者是孔教会会长,处理了交卸事宜。到南京后不久,以三人名义成立的报馆被捣毁了。子英没事,德清大腿被尖刀刺了一刀,拍照发文向各处分送,宣扬军政府横暴。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 爱农的学监被孔校长设法去掉了。他成立革命前的爱农,我想在北京帮他找点事做,但是没有机会。景况愈困穷,言辞愈凄苦,开始寄住熟人家里后来又搬出来了,各处漂浮。末了从同乡那里得知他掉水里淹去世了。我疑惑他是自尽,由于他水性很好。独坐在会馆里,一壁狐疑的不愿定,一壁又以为该当是真的。写了四首诗怀念他,个中几句快要忘却了。后来回抵家乡,才理解到关于爱农比较详细的事。由于大家讨厌他,以是没什么是做;很困难,朋友请才有酒喝;很少和人往来,大家也不愿听他牢骚。他常说:“大概来日诰日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有一天几个新朋友约他坐船看戏,回来的时候半夜了,风雨交加,喝醉了,偏要去船舷上小解,末了掉下去了,从此起不来。第二天打捞尸体,直立着。我至今不明白他是失落足还是自尽,他去世后空空如也,遗下幼女和夫人。有几个人想集点钱作为他女儿将来的学费,又怕有了这笔钱会有族人来争———本来实在这笔钱是不存在的。大家以为无聊,就作罢了。现在也不知道他唯一的女儿怎么样了,如果上学,中学也该毕业了。#故事# #我,无条件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