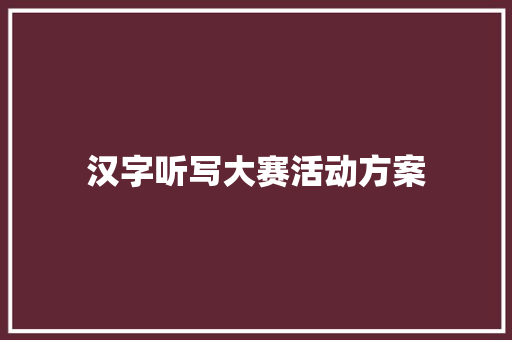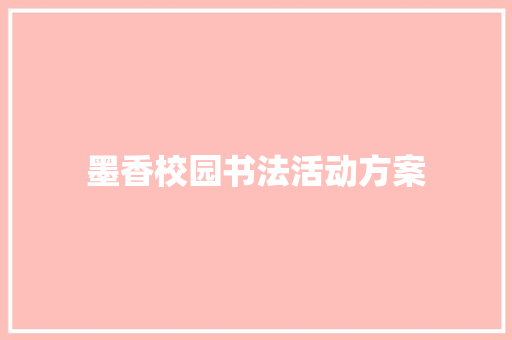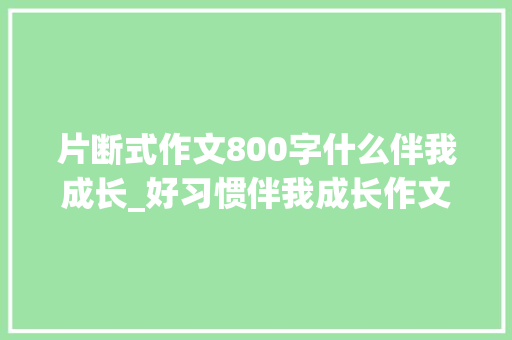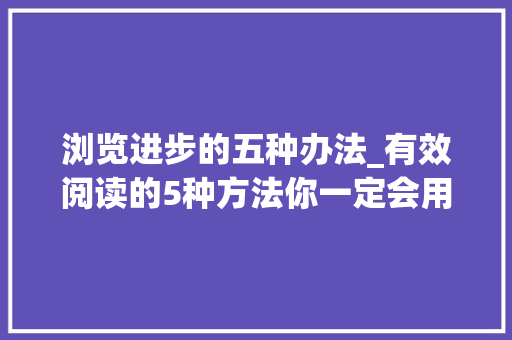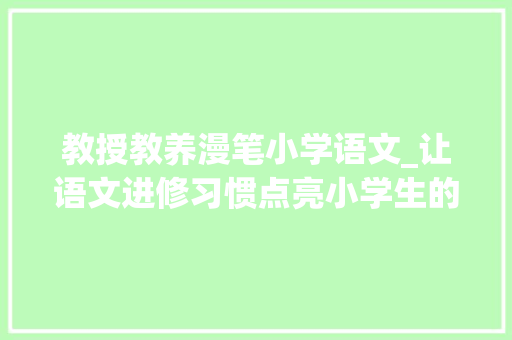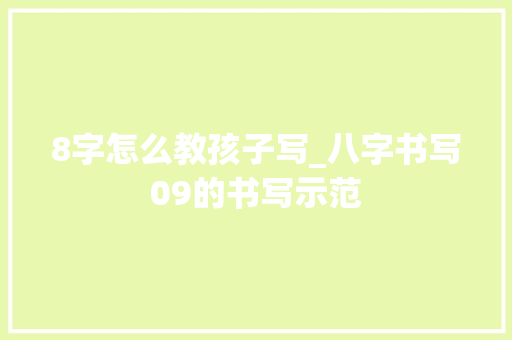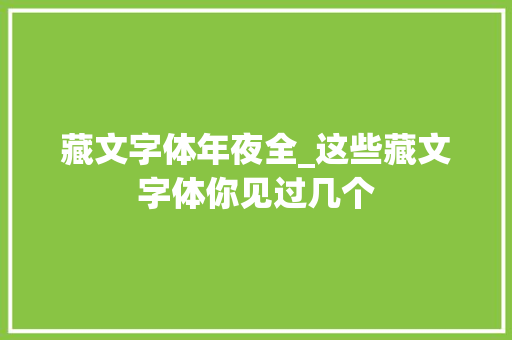紧张是受书本的书写或排版办法影响而形成。
在这个问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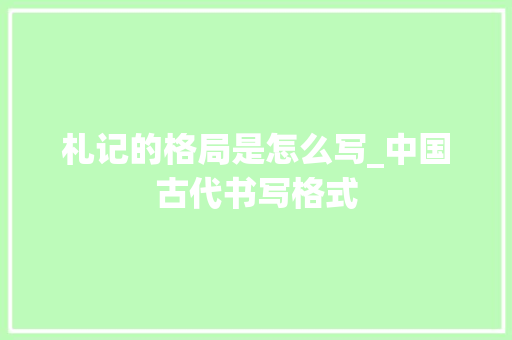
连人的生理适应力也退居其次
古书的体例、编排、形制、流传等情形,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随着近百年来出土资料的不断创造,学界对古书的认识更为丰富。从前的王国维、余嘉锡、劳干、马衡、陈梦家、钱存训等师长西席,近年的李零、李均明、汪桂海、张显成等师长西席,都先后对古书以及与古书密切干系的官私文书的许多问题作过十分精彩的探究和论说。但关于古书的书写格式,彷佛还可再作探究。
所谓“书写格式”,是指书写习气。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气是自左向右书写、从上往下移行,是为横行。我们古人的书写习气却是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是竖行。钱存训认为:
这种直行书写的缘故原由虽不可确考,但羊毫书写的笔划,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只能容单行书写的狭窄的简策等,都是匆匆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这大概是是由于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气,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气。
劳干在为此书所写的《后序》中特殊提及这点,并就此揭橥了自己的认识:
对付中国书法的行款问题,在本书第九章中,存训师长西席曾经提到中国笔墨的排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缘故原由,和右手有关,是十分确切的。如其再找一下书写和竹简的关系,就更为明白。由于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样平常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轻便利起见,空缺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缺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环境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样平常人手执苗条之物是与人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两位师长西席都将这一书写格式的形成归因于简的利用以及旁边手在书写时的合营。李零在谈到简文书写一样平常为竖行左行时,括注称:
古人以左行为顺势,右行为逆势。
不雅观念的角度作理解释。
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竹木简之前,西周时的金文的排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富商甲骨文的排列,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而在旁边行的问题上,有的是从右向左,有的则是从左向右。 如以右行为逆势,何以在占卜这样的活动中,会选择逆势右行来刻卜辞呢?
在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格式中,自上而下是根本,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都是由自上而下这一点来决定的;只假如从上往下书写,就从根本上打消了向上而下移行的可能性。换言之,远在富商期间,人们的书写习气就已是从上而下书写了。但是,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上的;龟甲不同于修成一条一条的竹木简,它是成片的,从刻写的技能角度和方便角度来说,横行刻写与竖行刻写恐无太大差别。 那么时人纵向书写的习气是何以形成的呢?当时是否还有其它用于书写的材料呢?
目前虽然尚无实物创造加以证明,但亦并非毫无踪迹可寻。《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已有“册”字,象竹木简编联之形。于是,有学者指出富商已有竹木简册。 西周金文中的“册”,亦指简册。据陈梦家的研究,西周的册命之制,是先将王命写在简册上,当庭宣读,然后再铸到铜器上。其时王旁边有两史,一执简册,一读册命之文。以是,铜器上的王命便是预先写在简册上的册命的迻录。 可见,西周铜器上笔墨的由上到下、从左向右,是据简册而来。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富商的甲骨、西周的金文,并不是当时书写的惟一载体,乃至不是紧张的载体,而是一种分外的载体。并不存在从甲骨、金文、石刻到简牍这样一个依次发展的过程。我们本日所见到的《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籍,并不是靠甲骨文、金文保存、流传的。人们平常用于书写的,绝不可能是甲骨和铜器。当时纵然没有私人著作,至少也有史官的记录;加上数量更多的官私文书,参以其后出土的大量简牍,我们认为当时用于书写的紧张应该是竹木简。
从书写的角度看,简册与甲骨、青铜是同时并用的;当时人根据他们的理解,用不同的书写载体来记录意义不同的内容。不仅如此,在书写格式上,日常用作书写载体的简册,影响了在分外情形下才利用的甲骨、青铜。换句话说,作为书写载体的简或简册,在韶光上要早于甲骨、青铜。
因此,古书的书写习气是由人们日常紧张利用竹木简书写所造就的。这一点,钱、劳两家的认识是精确的。但是,何以利用竹木简书写就会造成人们自上而下(而不是从左到右)地书写、从右到左(而不是从左到右)地编联呢?劳干师长西席认为从右到左的排列,是书写者为了使写过的简与空缺简不相混,“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环境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但是,这个问题完备可以用给简编号的办法办理。我们也的确见到了这样的实物,如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每支简的背后都有编号,共有廿六枚简,顺序编为第一至第廿七(中间缺第十五)。
就目前所知,在纸发明以前,人们日常用于书写的紧张是竹木简。在书写时,未必是左手举着简、右手书写——就目前所见的实物,许多简十分狭窄——恐是将简置于类似于今日的桌子上,左手扶简、右手书写。诚如是,则何不将简横置,从左至右书写?写成后,将简编联,自可从上而下、自左而右阅读。对此,钱、劳两家的阐明似尚未达一间。此未达之一问,便是要阐明为什么文籍要自上而下书写、从右向左移行。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一是书写的方便,二是阅读时舒卷的便利。
就书写方便而言,需分两种情形加以谈论。如果是先书写、后编联,那么横行抑或纵向书写,彷佛并无不同;但如果是在先已编联好的简册上书写,情形就会不同。
事先已编联好的简册,一定是已经卷成了一卷一卷,利用时边写边打开。如果是横着写,那么这卷编联好的简册,只能放在自己怀里,一边写一边往对面推。如果将已编联好的简册旁边放开,于书写者则更为方便;但这样放置,便只能从上往下,竖着书写。至于从左向右写,还是从右向左写,则与书写者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密切干系。如果是用左手写,显然应将卷着的简册放在右边,这样在左手握笔时,右手可以放开简册;如果是用右手书写,则应将卷着的简册放在左边,右手握笔写字,左手合营放开简册。由于我们大多数人的书写习气是右手,以是,从右向左书写就会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气。
于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古人是先编联后书写,还是先书写后编联。
目前所创造的简册,有的是先编联后书写,有的则是先书写后编联。陈梦家在整理武威汉简时,就据《汉书·路温舒传》“截以为牒,编为书写”,《后汉书·周盘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以及武威出土竹木简《仪礼》和王杖十策的实际情形,指出“先编简而后写经文”。商承祚在阐明韦编三绝的“韦”字时,也谈及文籍是先编后写,杂事简因无连续性,是先写后编。李零谈到竹木简的制作时说:“竹简是截竹为筒,破筒为片,编联成册,用以书写。”谈论简的抄录时,说“简文有先编后写(在编好的册上直接写),也有先写后编(先写单简,然后合编),前者最普遍。刘洪师长西席特殊指出,如果是长篇著作,宜先编后写,而一样平常账目、札记则先写单简,等积成一定数量,再编为长册。马先醒师长西席则有不同见地,认为“就实用方便而言,逐简而书,自较整册而书方便,尤其长达二尺四寸之经书,若编卷成整篇整卷而后书之,笨重不便之外,犹恐根本不太可能”。
所谓文籍的书写,实际上是缮写。文籍的流传,也紧张是靠缮写。汉代有专业的抄书者,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已经抄好的书。如果是先写再编,就需将每支写就的简都编上号,以便全部写成后能很方便地编联成册,如上举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文籍的缮写,一卷至少要抄完完全的一篇,否则就不可能“单篇别行”,故其分量远较诏书为大,所需简亦远比诏书为多。如此之多的简,也给先写后编带来很大麻烦。龙岗秦简(抄的是奏律)刚出土时,整理者据其简文为编绳所压,推断此系先写后编。后来则据这批简数量颇多(三百余枚),且无编号,认为简文被压是因编绳滑动所致;它们应是先编后写。目前出土的文籍简,确是先编后写。看来,文籍紧张通过缮写这一形式来流传,决定了要先编联后缮写。事先编就的简册,就犹如我们现在利用的本子;我们是在已经装订好的本子上书写。
如果先写后编,对书写者来说,横行与竖行并无不同;就阅读而言,当然是横行阅读比纵向阅读更符合眼睛生理的哀求。但是,在阅读简册的时候,我们不仅须要考虑眼睛,还要考虑双手与眼睛的合营;在翻阅简册时,旁边的摊移更符合双手的生理哀求。当翻阅捆成一卷的简册时,旁边方向的舒卷比高下方向的舒卷更随意马虎、更方便。读卷轴装或经折装时,这一体会更为深刻(立轴字画当为特例)。直到本日,我们阅读的书本,也是旁边翻页者占绝大多数,险些没有装订成高下翻页者(这当然也有背面笔墨的印刷问题)。换言之,纵然所有的简册都是先书写、后编联,那么在编联时,人们也会选择自右向左渐次编联;编联是为了保管,而保管又是为了日后的翻检、阅读。书写者在业已编联好的简册上书写,则旁边书舒卷显然也要比高下舒卷更为方便。
我们暂且承认在私家著述涌现之前,是史官文化;那时,史官们卖力的紧张可能是两件事,一是记录言行史事,二是管理档案。就记录而言,他们恐怕是在事先就已编联好的简册上记录。《左传》曾记载过一位秉笔直书的史官:
太史籍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去世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去世,执简以往。既书矣,乃还。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职位,故兄去世弟继。这位“执简以往”的南史氏,不仅是要记录下“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而且是要继任史官,连续秉笔直书。以是他恐怕不会是抱着几支或十数支没有编联好的散简去,而应该是抱着已经编联好的简册去的吧。
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简来书写者,绝不会是长篇大论。这些随手书写的短篇东西,彷佛不必采纳长篇文籍那样的书写格式,但事实却相反。——我认为,大多数人日常随手的书写习气,是受文籍熏陶而成。于是,我们看到,公私文书纵然是先写再编联,也采纳了文籍的编联方面,即从右向左。
纸发明之后,人们仍旧保持了这种习气,直到1949年往后。在推广简体字的同时,书本变成横排,同时,本子和印线或印格纸均采取横行之后(这实际是一种变相逼迫),这一书写习气才完备改变。是书本的改变,带动了人们日常书写办法的改变,而不是相反。现在,台湾由于打算机办公的遍及,为了与打算机排版相适应,政府已明令公函采纳横行办法。但是,书本排版办法不变,大众的日常书写办法恐怕不会因公函书写办法的改变而完备改变。
书写材料决定了人们的书写习气,但习气一经形成,只要新的书写材料与这一习气不冲突,纵然有所不便,也不会改变,除非利用逼迫办法;而书写习气的改变,终极要通过书本排版的改变来实现。换言之,大众的书写习气,紧张是受书本的书写或排版办法影响而形成。在这个问题上,连人的生理适应力也退居其次(眼睛更适应旁边阅读),更无论生理成分了。
本文所及,只是就汉字而言,未及其它笔墨的书写。纵然汉字,也只是就其主流形式而言,而未及其它各类分外的书写办法。只有将汉字与其它笔墨进行比较,大概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汉字的这种书写格式;但囿于学力,有待于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