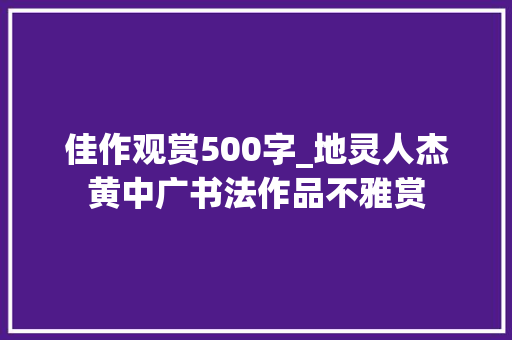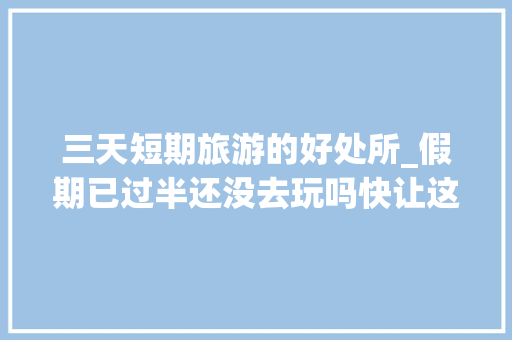来源:当代广西网
桂系首领之一黄绍竑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其生平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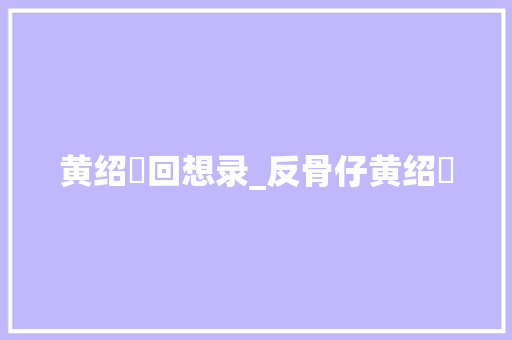
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役以桂军失落败告终,粤军攻进广西,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桂军分解,部分桂军分开陆荣廷、谭浩明(陆谭)体系,接管革命政府的领导。个中,驻守百色的马晓军接管任命为田南防备司令,黄绍竑、白崇禧、夏威为其麾下三个营长。
粤军入桂,纪律极坏,引起广西百姓愤恨。陆谭残部逐渐集结,形成广西自治军,以图自卫自治。自治军发展迅速,粤军无法整顿,被迫撤离广西,接管孙中山任命的马君武也几遭不测,接管革命政府领导的刘震寰、马晓军等,亦被称为“反骨仔”,受到自治军的围攻。
黄绍竑在其《五十回顾》中专门回顾了这段经历,他说:
所谓自治军者,虽以自卫自治相号召,实际不过地方强烈仇恨意识的表现,并无真正的自治主见与操持。他们第一个敌对目标为客军。粤军、滇军、黔军等,皆无妥协余地。其次则为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编之军队。马省长君武为当时一省人望,亦几遭不测。余如刘震寰、马晓军等及其所部,皆为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绍慧(伯山)、谭元翰(伯章)、甘尚贤、甘振贤、黄彤阶、何其多、梁培、谭葆谟等,皆与陆谭有乡土的私谊与多年部属的关系,因陆谭已溃,不忍地方腐败,与新政府靠近,而故意整顿改革者,竟皆为谭浩明旧部所杀。彼等对这班人统名曰“反骨仔”(即背叛的分子),得之即行屠戮。[ 黄绍竑《五十回顾》,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作为马晓军的部下,自然属于“反骨仔”之列,亦曾被刘日福的自治军包围缴械,幸得逃脱,组织余部反击,后在凌云集中,部队改编,黄绍竑任第一统领,辖冯春霖、黄炳煊、岑润博三营;白崇禧任第二统领,辖夏威、陆炎、韦云淞三营。由凌云到百色,由百色到田东,在田东时,白崇禧因足伤赴广州医治,其部由黄绍竑统领。马晓军、黄绍竑率领部队打破自治军的拦截,从田东经隆安到南宁,再从南宁到灵山。途中,马晓军与陈雄离开部队赴广州。黄绍竑率领部队从灵山到廉江,从廉江到博白车田圩,在车田圩接管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约请,任李宗仁麾下第三支队司令。这是李黄互助的出发点,也是新桂系形成的出发点。
把稳,黄绍竑最初是陆谭桂军马晓军模范营部,粤军攻入广西后,马晓军部接管广东方面的任命,在陆谭旧部看来,即是叛变了广西,成为广西的“反骨仔”,并因此被广西自治军缴械。作为马晓军的部下,在广西自治军的围追堵截中,黄绍竑率领马晓军的部队转战千里,用他本人的话说,有时候是“一日须经二三次战斗”,[ 黄绍竑《五十回顾》,5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末了从广东回到广西,竟接管广西自治军李宗仁的体例,这究竟是“迷途知返”还是“叛变革命”,确实难以评价。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在黄绍竑接管李宗仁体例的时候,跟随他转战千里的一个主要统领陆清,就认为黄绍竑骗卖他们,另一黄绍竑麾下主要战将冯春霖部下的一个班长,亦带兵数人离开了黄部。对此,黄绍竑在《五十回顾》中亦有记录:
(李德邻)委我为第三支队司令。此事除了几个主要干部知道大概之外,别的尚未清楚个中底细。至是我不能不向大众公开宣告。内中有与我部同时退出南宁的陆清统领,是广东钦州人,亦革命老同道。我们在粤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将实情奉告,此时他自然有些不满,说我骗卖他。我在当时情势之下,为防万一起见,不能不将该部百余人缴械。又有冯营一个班长,带兵数人,自由行动去了。我派人追去劝他,他说:“如果要在广西当自治军,就不必退出南宁,行乞到这里了。”[ 黄绍竑《五十回顾》,5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对自己这一次调换门庭彷佛也有自知之明,因此,对陆清和那个班长的选择,黄绍竑也抱理解之心。在上面这段笔墨之后,他专门有所评论:“这事,我至今犹耿耿不忘。由于他们的见地,是有相称情由的啊!
”[ 黄绍竑《五十回顾》,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由陆谭桂军接管广东方面改编的时候,被称为“反骨仔”。所谓反骨,指的是脑后枕骨。常日枕骨突出者被认为生有反骨,也便是有背叛之心、不忠不义的人。历史上最著名的“反骨仔”该当是《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他便是由于生有反骨而不被诸葛亮重用。黄绍竑从陆谭旧部成为革命新军,这是他的第一次背叛;不久从革命新军回归广西自治军,这是他的第二次背叛。人们或许认为人生有两次背叛已经足矣,哪里想到这对付黄绍竑来说才仅仅是他背叛的开始。黄旭初在其回顾录中对黄绍竑的多次背叛有一个统计: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造广西集团,但他个人的行动颇为奇特,对他自己手创的团体曾作过三次的分合。计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广西自治军蜂起,他不能与之同流,皇然无归,李宗仁邀其互助,他以志同道合,概然归入李部,这是第一次合。十二年夏,他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得“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和讨伐沈鸿英而盘踞梧州的密令,于是在梧树起新帜,与在郁的李宗仁分道扬镳,这是第一次分。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击陆云高,打通梧郁在大河方面的联系;十三年夏,讨贼军与定桂军再互助以击倒陆荣廷,盘踞南宁,黄推李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这是第二次合。十九年夏,广西相应北方的扩大会议以共同倒蒋,出师向武汉,到湘而败归,他自此厌恶内战,主见和平,年末即离广西而到南京,这是第二次分。廿六年秋,抗日战役起,全国同等共赴国难,所有政敌都捐除成见共御外侮,这是第三次合。卅八年夏,国共和谈分裂,李白坚持连续对共作战,他却主见和平而投共去了,这是第三次分。[ 《黄旭初回顾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392-39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根据黄旭初的这个统计,在接管李宗仁任命之后,黄绍竑还经历了与他创造的广西集团,也便是后来所说的“桂系”的几度分合。“三合三分”,这是黄旭初的统计,足以解释黄绍竑这个人物的变革多端,乃至用“重复无常”来形容也未尝不可。对此,黄绍竑本人也不避讳。他在其《五十回顾》的弁言中说: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确当事人。在满清时期成长,而参加满清的革命。在广西旧军阀底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互助,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推戴中心,而又反对中心,后来仍旧推戴中心。在许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变成仇敌,或者由仇敌而变为朋友。中间的变革,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不雅观点来看,切实其实是一种儿戏。但是事实的演化,确实是如此繁芜。[ 黄绍竑《五十回顾》,弁言,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如果按黄绍竑的这个说法,那么,黄绍竑的变革可能就不但三合三分,可能是四合四分或者五合五分。常日而言,以变革太多来定性一个人,该当不是褒义。但黄绍竑却坦然承认自己变革太多,变革得犹如儿戏。何以故?考虑黄绍竑的思想,可以看出,黄绍竑认为他的多变虽然是客不雅观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并不虞味着他本人如何善变,他的多变是由于他所处的时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作为时期中人,他自然卷入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格局。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黄绍竑在不同的政治集团间游走不定,变革无常,但他也有不变的地方。1930年,当他决定分开桂系的时候,同时也在内心中作出了一个决定,那便是:第一是不再毁坏国家,第二是不再毁坏团体。他把这个内心的决定视为他往后行动的原则,为人干事的最高准绳。[ 黄绍竑《五十回顾》,213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所说的团体当然指的是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形成的桂系团体,综不雅观其生平,虽然他后来接管了蒋介石的约请,先后出任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军委第一部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主座等职,虽然蒋介石多次想借他打击李宗仁、白崇禧,但黄绍竑确实从未做过有损桂系的事情,反而利用各类机会,帮助“李白”摆脱困境,或者,匆匆成蒋介石与“李白”的和解。
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颇有建树之外,黄绍竑生平最热衷的是经济培植,无论是执政广西还是执政浙江,黄绍竑都在经济培植上有诸多古迹。可以说,发展经济是黄绍竑生平不变的欲望和追求,他对经济培植的激情亲切远远超过对政治和军事的激情亲切,这一点早在桂系北伐出征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黄旭初在他的回顾录中如此说:
当在省内谈论北伐问题时,已经涉及广西部队究竟由谁统率出征呢?本来李宗仁与黄绍竑都是军长,谁也适任。但黄自己表示对付地方培植感兴趣,自从十四年玄月临时省长张一气辞职后,大家便推他当广西民政长了,以是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他推李担当军长,统军北伐,而他自己愿留在省内任省政府主席,并兼第七军党代表。[ 《黄旭初回顾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02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当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大军从镇南关到山海关的时候,黄绍竑则在后方激情满怀地培植广西:
我们站在政府态度,不管先天不敷也好,后天失落调也好,并不因此灰心,而仍旧是勇往直前地去做,希望人定可以胜天。以是对付他们的各类说法,均当他是禁绝确的批评,而不自馁意志。在那短短的韶光内,工业方面,完成了三酸厂、酒精厂、机器厂、制革厂、机器厂、砖厂、纸厂。农业方面,成立了全省农务处,各区设置拓荒局及兵农委员会,实施兵农政策,并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为县长的考成。全省的公务员,均须身体力行,首由省级公务员做起,我亲自率领垦地植桐,在南宁辟有一个广大的公务职员桐场。全省高下,热烈进行经济培植的事情。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当我们兴趣勃勃的时候,突于十八年春,接到广东方面的电报,说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急速到广州去。当时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务员挥锄掘地。急速抛下了锄头,踏上了汽车,放弃了统统的事情,重复走入政治战役的漩涡。广西培植的事情,便从此停顿下来,又受了几年的磨折。[ 黄绍竑《五十回顾》,16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由于政治争端导致战役的发生,由于战役的发生导致经济培植的结束,从黄绍竑回顾的字里行间,可以感想熏染到一个培植者深深的惋惜。
正是由于意识到战役对国家、对地方、对社会、对民生的毁坏,他才当仁不让地离开他参与首创的政治军事奇迹。将战役与培植相比拟,他痛切地认识到战役是多么无谓,而培植又是多么名贵:
我以为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
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公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漩涡。……我那时由于不能出省,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林场,栽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事情。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黄旭初去参不雅观这个农场,当年所栽种油桐幼苗,今日已乔木参天,十五年前彷佛是一个无聊极思的玩意儿,今日则成为社会上一宗很大的财产。比到十余年来誓不两立,此起彼仆,那些“夺帅印”“取成都”的活剧,意义深长得多,使我对付以往的统统,引起了无限的感想!
[ 黄绍竑《五十回顾》,21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这是一个曾经在政治军事领域有过重大成功的人的反思。理解这些反思,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宁肯背负善变的恶名。他做过陆谭的部下,终极背叛了陆谭;他做过孙马(孙中山、马君武)的部下,不久投奔了自治军;他做过李宗仁的部下,曾经与李宗仁分道扬镳;他投奔过蒋介石,末了抛弃了蒋介石;他认同了共产党,也批评过共产党。从中国政治传统看,他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他的生平中有过许多次改弦易张,另寻高就。然而,这个对领袖从来都不从一而终的人,对培植却有着从一而终、痴心不改的执著。原来,他的善变,他的不惜分开他热爱的团体,全由于他对培植的激情亲切。这种激情亲切在他那里一以贯之,无论是在广西省主席任上,还是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湖北省主席任上,他都对培植充满了激情亲切,也有过一些建树。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期对他过于吝啬。那是一个为政治家、军事家而非为培植者供应舞台的时期。不过,纵然如此,黄绍竑在培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直到本日仍旧值得我们铭记。当然,更主要的是,他对政治、战役和培植的反思,彷佛尤其值得本日的我们所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