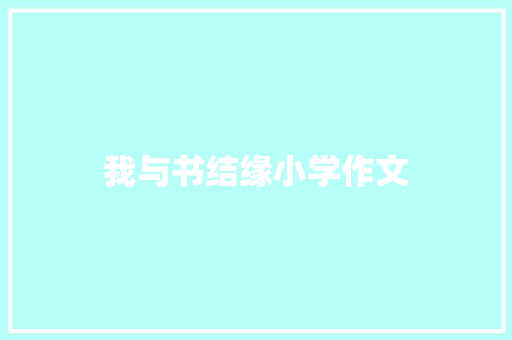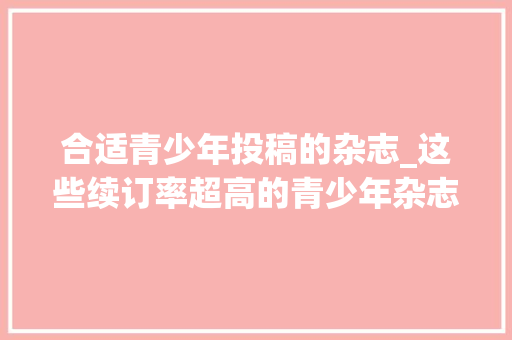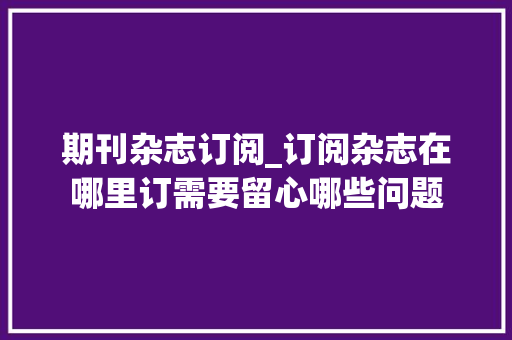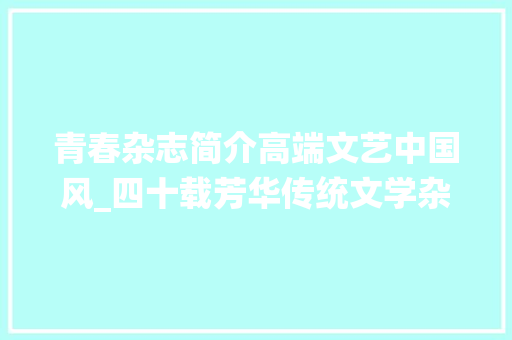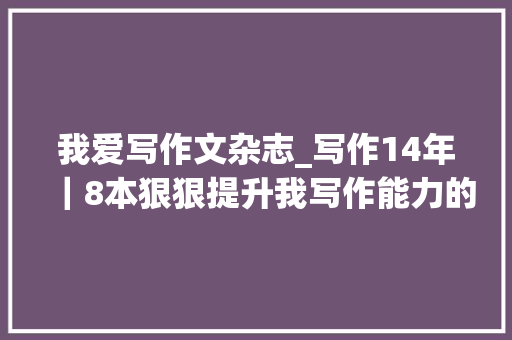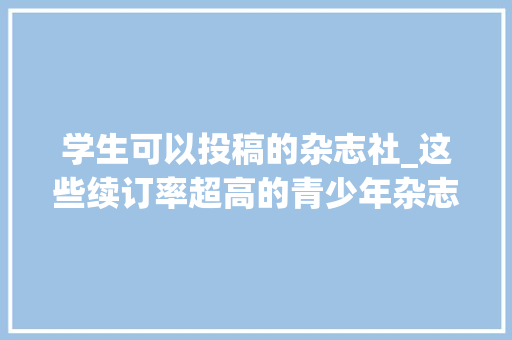“当前无网络连接”,屏幕上赫然几个字,已经不知道是本日第几次了。不知道门外闹哄哄的是不是跟这断网有关系,也不知道那帮人要捣鼓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自己慌什么。不便是没网了?有了也不用,没了还惦记。往远了讲,人类没有网络的历史何其漫长,距今也并不迢遥,不知是有网日子的多少倍;往近了说,二十四小时持续在线,没有网就失落联的日子也便是这十来年吧,大学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支付宝微信,高中之前上网也不是为所欲为,聊个QQ、写个空间、发个伊妹儿就可以跻身冲浪少年(女)了。
没有网络的日子人也毫发无损,信息的匮乏催生了不少已沦为“时期眼泪”的快乐,这些快乐大略而原始。个中有一种快乐,与此刻帮我阻挡屋外喧华的这扇门颇有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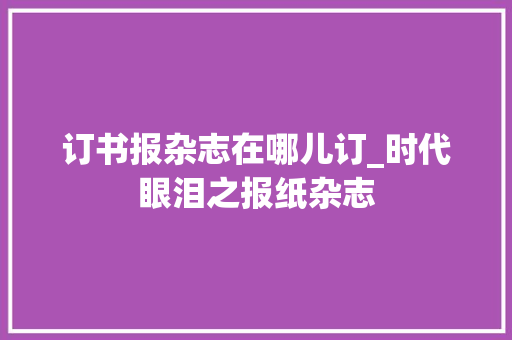
斑驳的防盗门上,贴着忘了去年还是前年的福字,装牛奶的箱子也被拆了,现在那个位置该当是空的了。奇怪的是,倘若要我闭上眼,去想象那扇门的样子,我还是会第一韶光想到一个黄色以及一个蓝色的报箱,一个是《华商报》的,另一个是《三秦都邑报》或是《西安》的吧。纵然那个订报纸、送报纸、看报纸的年代距今颇为迢遥,可那个韶光彷佛持续了很长,有多长,大概,便是一拃那么长。
最近有人问:要去哪里订杂志?我想最官方的答案该当是邮局吧,可是想到院子里曾经阔气的住户报箱墙也落得跟门上的报箱一样的被拆除了局,就不敢以笃定的口吻回应对方了。现在在邮局订书报杂志该当跟在“杂志铺”这样的网络平台差不多吧,网高下单,送货上门,毕竟邮政也承揽了快递业务。实在,如果报刊亭这种古早的举动步伐还广泛存在的话,大多数人是
我所住的这条街,东西走向,二十年前最为壮盛期间,此街两端和中间各一个报刊亭,若是范围再延伸的话,连接的南北方向两条街和那一边东西方向另一条街——这四条街组成的方块街区,顶点和四边无一不设有报刊亭。神奇的是,在当时人并没有觉察到其分布之密集,有时反倒还显得不敷用。买本杂志,这家卖完了,就跑到下一家,这是不能再顺理成章之事。报刊亭这东西,不像商店是封闭的,而是一年四季对外洞开的,各种花花绿绿的报纸杂志,散发着纸质印刷品特有的味道:一种不是大家喜闻的现在人称其为书喷鼻香、墨喷鼻香的油墨纸张气味。当有一天,一样东西开始唤起了人的怀旧之心并对其巧饰,那它多数是被送上了祭坛,一如这下架了的久违书卷气。
杂志顶峰的年代,数量铺张,同质化严重,为了打破重围,博人眼球,不少杂志盛行起塑料纸外包装,里面还附带各种书签卡片等小礼物。最夸年夜的是,我记得《米老鼠》杂志还常常赠予给读者各种价格不菲的迪士尼小玩具,还有互助方供应的诸如高乐高之类的食品试吃装,其销量与传播力、影响力可见一斑。类似如今书书都有却大家调侃的、写满各种名人推举语的腰封,仿佛没有这玩意你都不配做一本脱销书。那个年代,没有华美包装和小礼物的脱销杂志,尤其是少儿读物,也是异类。那些年,学校组织订阅的报刊,大多都是跟学习有关的,小学时的《作文精选》、《小哥白尼》到中学的《21世纪英文报》等。小学时,假如谁能在集体订阅的某作文杂志上揭橥一篇作文,一夜之间就成为全校老师表扬、学生倾慕的模范生。只是,多年往后,我创造了一个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学生时期大家争相揭橥作文的刊物,多为一些本地的收录学生习作的不有名杂志社,不管文学代价还是作品含金量真的不高,险些都是辅导老师推举的应试作文范本集结成的册子,而诸如全国性的少儿文学期刊,像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是不会刊登这些流水账式小学生作文的,学校也很少组织订阅,我都是自己去买或者订的。
《儿童文学》封底
提起订杂志,最先想到的便是这一本:《儿童文学》,不要被它略带几分稚气的名字迷惑,此刊封底赫然印着:本刊适宜9至99岁公民阅读,俨然一本整年纪向读物。
个中,印象蛮深的里面有一篇中篇小说:《杨梅》,那是2003年旁边它们社搞了一次中篇小说擂台赛,每期杂志都会选登几篇参赛作品,后面彷佛是陆陆续续还办了几届吧,但都没有第一届那么让人线人一新,大概只是先入为主?至今还记得住名字的几部作品:《七年》、《从冰点到沸点》也都是第一届的,参赛者险些都是青年作家,也不乏一些后来成名的作家,比如名噪一时的“花衣裳”丛书作家:饶雪漫、伍美珍、郁雨君,当时她们已小有名气,出版了不少或许是“青春文学”鼻祖的读物,大多数人,纵然获了奖,也并不出名。文学这东西,彷佛不是也不可能因此出名和赢利为目的的,有也只是一种极为有时的附属品。能让一个心智还未健全的不知道自己喜好什么的小学生喜好上阅读,几十年后还记得你的作品,纵然早就忘了你的名字,这对书写者便是最贵的稿费和最大切实其实定,他的初心也罢、野心也罢,也就此实现了。
就像不爱吃杨梅的我却记得那篇《杨梅》,那是一个讲述叫做“杨梅”的小女孩和她继母的故事,故事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大概便是以小女孩的视角描述了成人间界各种繁芜深长的爱恨纠葛,许多当时匆匆入眼的小细节却还影象犹新:杨梅继母的劣质帆布包、杨梅家每天的晚饭只有土豆萝卜芽菜三选一以及一盘万年不变的虎皮辣椒。小说里的杨梅吃虎皮辣椒吃到反胃,辣得涕泗横流。她认为那是继母对她的厌恶与惩罚,当然,也是由于她家实在是穷。有一天她实在不愿意再吃了,就赌气没吃晚饭。半夜,杨梅实在饿得睡不着,阴郁中钻进厨房,蹑手蹑脚地从橱柜盘子里抓起那虎皮辣椒就往嘴里塞,一韶光,泪水翻滚,那是被辣到哭的情不自禁,也是委曲仇恨的自然流露。这时,继母无声地走到她身后,灯亮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辣辣地扇在她泣涕涟涟的脸上。那个时候,读到这里,我多么想要冲进书里奉还她后妈一记耳光。今后的很多年,我都冒死脑补那道恐怖的虎皮辣椒是什么滋味,还问身边大人,他们见告我:特殊辣,你吃不了。也是,一点点辣椒都不沾的我,想到那种直冲耳根的火辣,都眼泪不止。看来这辈子是无缘虎皮辣椒了,就让它一贯保留在行文里杨梅家的餐桌上吧。
书和杂志也遵照着先来后到的规矩。抬眼望去,书架上还有整整两层的《儿童文学》,旧书也罢,旧杂志也罢,总是无法跟其他旧物一样光明正大地沦为垃圾,哪怕它们的主人比谁都清楚自己再次会晤这群故人故友险些是不可能之事。站在凳子上,从书架上扶下老态龙钟的它们,掸掉灰尘,感想熏染满页的泛黄与陈墨,想来都是艰巨费力之举动。再看看新买的书、新到的杂志已无立足之地,被敷衍地堆在桌面,而它们的前辈仗着多面世了几年得以安然居住,新人之处境其实尴尬。
订杂志与报刊亭买杂志比较,我更中意前者,很大略,有一种预定的知足感,用现在盛行的话讲,便是牢牢把握的确定的幸福吧。每到月初那几日,每天我都会早中晚定时去报箱,钥匙探进孔隙迁徙改变的那几秒是最为紧张的时候了。随着亮光射进幽暗的报箱,箱门陡然迸开,一本崭新到发光还未褪去印刷气味的杂志傲娇地伸展着它聪慧的身体,淡然躺在里面。我仿佛中了彩票一样平常愉快地把它抽出来。借使没看到它的倩影,就略微惆怅地锁上门,期待着下一次赴约的奇迹瞬间。
即便是订杂志乐趣浩瀚,有的书也是不能光明正大去邮局订的,这是一类跟与学习有关的“正经书”对立的大人称之为“闲书”、“课外书”的编外书刊。各种漫画,《龙珠》、《机器猫》、《乌龙院》、《老夫子》等等,青春文学杂志,像是《新蕾STORY100》,以及各种印刷粗劣、光是看封面就惊悚无比的灵异故事集。好比是茶、咖啡、烟酒这类瘾物,几天不碰,甚是难度,瘾越大,越难忍。此类书也是,好奇地翻了翻,就放不下了,沉迷个中,若是挣扎着一阵子不碰,竟也逐步淡了兴致。不管好赖,瘾物的诱惑总也敌不过饭菜的刚需。
有另一本我不间断买了三年的杂志,后来之以是停买还是由于刊物停更了,便是这样一本介于瘾物与饭菜之间的极具魔力的刊物:《魔力w.i.t.c.h》。看它比看《哈利·波特》还要早,毕竟它2001年就出版了。这本意大利迪士尼公司出版的,定位为“魔幻少女漫画”的杂志,讲述了五个来自五大洲的拥有不同魔力的少女(女巫)的故事。可以这么讲,如果你之前没有打仗过任何有关魔幻题材的读物,大概率会被它牢牢锁住。当时学校的小伙伴还常常角色扮演个中那五个女孩:薇儿、爱玛、塔拉妮、柯妮利娅和海琳。那时我自然是薇儿,唯一和她相似之处便是短发吧,不过她可是和安妮一样的红头发。《魔力》和《米老鼠》都是童趣出版公司旗下刊物,报刊亭售卖10元一本的情形下还时常缺货,比拟一下彼时3元的《读者》,绝对算奢侈级别。
报刊亭后来越来越热闹了,买饮料冷饮,买Q币充值,手机还未遍及的年代乃至还可以在这煲电话粥。而现在,一句“在吗”都足以让社恐们惊吓万分,猛然响起的手机铃声瞬间冲破迷人的安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谋而合把手机调成静音。一个朋友说,如今还会打给他的,大概只有贷款保险和诱骗电话了吧,接与不接全靠心情全凭缘分。以至于最常说的一个谎,便是明明手机响却故意不接,过一阵子复书息说刚刚没听见,对方也谅解地说没紧要,彼此心照不宣地进入“对方正在输入”模式。
玩命拓展业务的报刊亭终极以时期遗珠的命运黯然离场,我最近一次留神家附近的报刊亭是在2015年了,当时为了考试期期必买《半月谈》。去年的某日,途经,才创造它也拆了,是早就拆了还是刚刚拆的,我真不知道。当一个事物存在与不存在都已被人视而不见,乃至麻木到感想熏染不到了,就真的是目中无其立足之处了。
旧杂志还在,旧报纸却难觅踪影。现在想买一份报纸绝非易事,报刊亭都拆了,随手买份报纸就烟喝茶的时期一去不复返。当年,在“订整年报纸送米面油”的刺激下,不少情面愿自掏腰包;现在,订报纸的该当只有公司单位了吧?毕竟不是自己拿钱。报纸是订了,看的人又在哪里?翻起一页页沉重守旧的报纸,不如打开手机,鸡汤、养生、八卦、揭秘迎面而来,内容丰富,任君挑选,以前站在书店、报刊亭只看不买,都跟做贼似的如履薄冰。听凭喜好精准定位,貌似是选择更多,事实果真如此么?
大街上背着书包赶去补习班的小孩们一茬又一茬,我自然是妒忌他们的年轻。但在某些方面,我是相称光彩自己早生了几十年。比如阅读,或者说小一点,便是看报纸这件事。那个年代,没有机会挑食,没有工夫矫情,拿到一份报纸,管你想看什么,它都霸道地充斥在全体版面:时政新闻、社会民生、娱乐新闻,各种种别一应俱全。哪怕你对某一方面毫无兴趣,它的笔墨图片也会不由自主地跃入视野。因此,那时候商家热衷在报纸登广告,尤其钟爱整版的大幅广告,就算是不起眼角落里见缝插针的迷你广告也是寸土寸金。也因此,不是体育迷的人也叫得出不少项目的赛事名称;不关心楼市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最近又有什么新楼盘、房价几何;不太看电视的人也能在别人聊热播剧时插上几句话……这些,都仰仗报纸广泛的内容体量和分散的信息获取办法。
而现在,算法霸占了信息分发主流,你想看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也就更加加深你固有的认知,以偏好之名,人毫无知觉地被困在信息茧房里,得意其乐。由被动的通读到主动的精读(更多的只是泛读),读什么、怎么读的选择看似愈来愈多元和主动,实则隐含太多的被动吸收身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讲:时期的哲学景象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不只是哲学景象,还有恐怖伶仃的见地景象。于是,最保险也是最无奈的做法是:当一棵随风向摇摆的小草,一枚任鞭子抽打的陀螺,天下的丰富性、原形的繁芜性被悄然掩埋。一颗草是弱小的,一枚陀螺是沉默的,一片草地、一群陀螺便是无比壮不雅观乃至恐怖的。逐渐地,我们都是拥有相同社会皮肤的吃瓜群众。
今年以来,事实反转的新闻事例看得人眼花缭乱,原形在后原形面前心悦诚服,致使我常以围不雅观八卦小报的心态看待严明新闻,真实与杜撰并进,纵使统统底细毕露的那一刻,还是会出于本能的疑惑:哦,是么?
“我们是谁?不便是我们获取过的履历、得到过的信息、阅读过的书、做过的梦的复合体吗?”卡尔维诺的这番话现在仍不过时。在履历、信息日渐趋同的时候,书与梦是一个人特立属性与光鲜风格的罕有来源,纵使如今中国真正读书的人不会超过两万人——这是一群精神上的锐利与行为上的笨拙并存的人,严明而羞涩,埋没于人海。消逝的报刊亭、邮箱和书店,由看到的征象而展开的论证会不会被某种更加强大的论据批评?我还是更相信亲眼所见,毕竟没有什么比这5.76亿像素的视觉感官更为可靠。
一条老旧的街道,一个孤独的报刊亭,一本后进的《儿童文学》,遇见的话,算你交运。
后记:
本日在街上看到《儿童文学》了,可惜又可悲的是它已然变了,按年事段分好几册,随手一翻,充斥着五颜六色的稚子插图,乃至还有作文版的,我一度疑惑是粗制滥造的盗版。想起最近热议的海内儿童文学界风波,只追求童真、低幼、纯洁的阅读氛围,轻微“出格”的作品就被哀求下架,再一次光彩自己生在那样一个原谅万象、乃至有点野有点狂的自由年代,得以小学就看完《苔丝》、《茶花女》、《笑面人》等书,什么讽喻影射、大尺度、纪实文学、险恶惨淡……都在从前尽收眼底,渐悟世事。于内心,我从来不是温室花朵。现在的小孩,在家长的庇护下,就乖乖待在温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