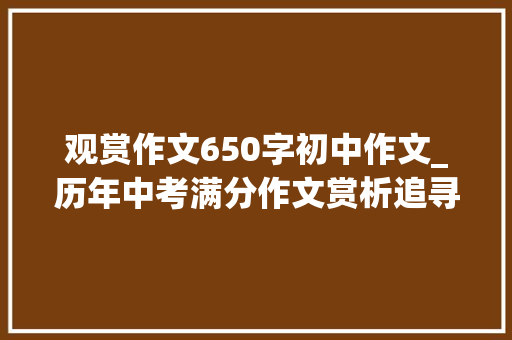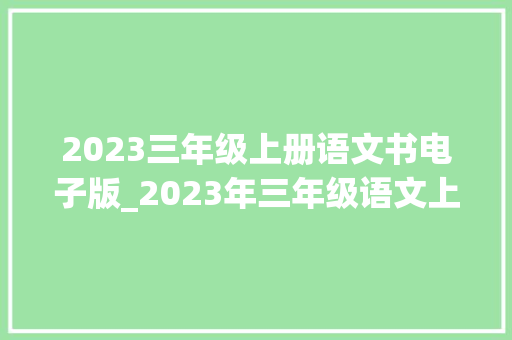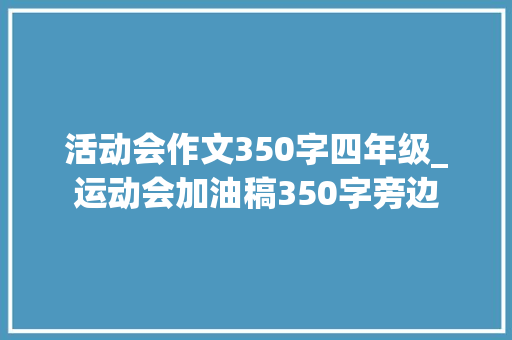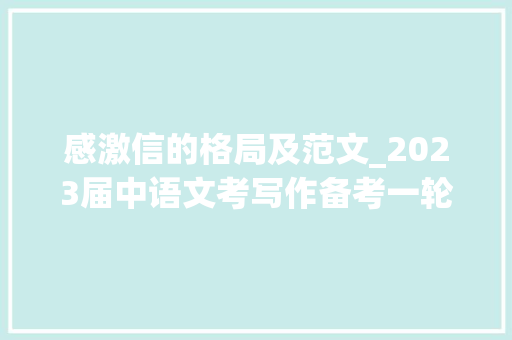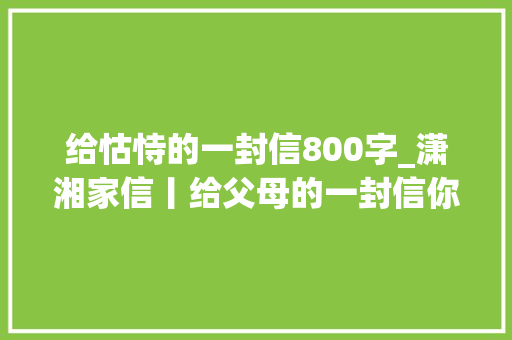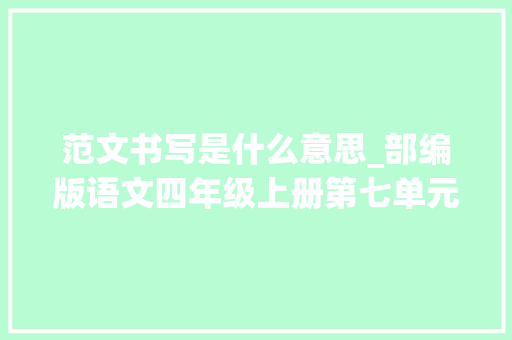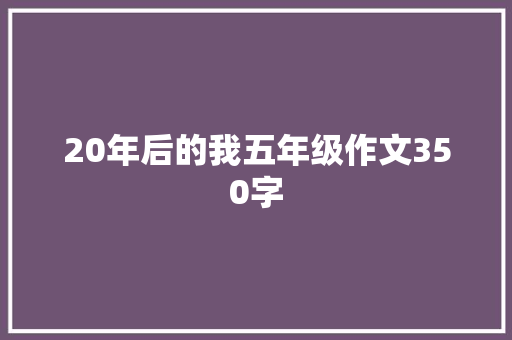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颂白杨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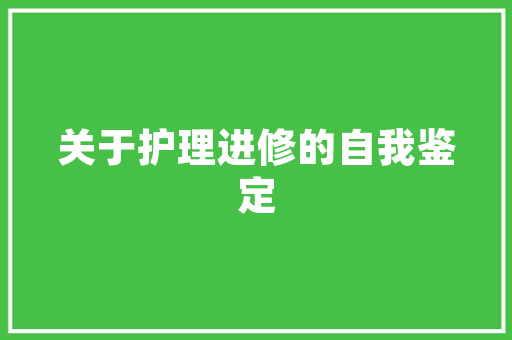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而成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降服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至心佩服前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由熬炼的措辞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开阔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你会忘却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大概是“雄壮”,大概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大概以为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 “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吧?
然而霎光阴,假如你猛抬眼瞥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乃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象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感情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便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图提高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常日是丈把高,像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牢牢靠拢,也像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险些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特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便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大概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派,朴质,严明,也不缺少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倔强不屈与挺立,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瞥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特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以为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明,倔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人?难道你竟一点也不遐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地皮上,到处有倔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特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联络,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本日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人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人相似。我赞颂白杨树,就由于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人,尤其象征了本日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倔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执拗的倒退的人们去赞颂那贵族化的楠木,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成长的白杨吧,我要年夜声赞颂白杨树!
荷塘月色
作者:朱自清 朗诵:林如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玉轮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弯曲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动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彷佛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天下里。我爱热闹,也爱镇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 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喷鼻香月色好了。
曲弯波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散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暗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顷刻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样平常,悄悄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以是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正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样平常;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屈均;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模糊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垂头丧气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彷佛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大抵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时令,也是一个风骚的时令。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棹⒁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拖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 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弗成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举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故都的秋
作者:郁达夫 朗诵:傅成励
秋日,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日,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殊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凄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遇上青岛,更要从青岛遇上北平来的情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喷鼻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抚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得当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日,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纵然不出门去吧,便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清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上苍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觉得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玄色次之,淡赤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便人遐想起秋来的点辍。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清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优柔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以为细腻,又以为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以为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奥深厚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由于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以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野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切实其实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彷佛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邑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清闲的音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
作者:梁实秋 朗诵:陈淳
到四川来,以为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软弱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屋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范例的屋子。不消说,这屋子有砖柱,有竹篦墙,统统特点都搜罗万象。讲到住房,我的履历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茆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算夜厦”,各式各样,我都考试测验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屋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逐渐觉得它并不能蔽风雨,由于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了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阁下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池塘,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意。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由于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壁高,一壁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逐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付鼠子,我很惭愧的承认,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
“雅舍”最宜月夜——阵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
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旧逼进窗来,助我悲惨。小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溘然倾圯,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散乱,抢救无及。此种履历,已数见不鲜。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贵显,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甜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好翻新支配。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好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好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支配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纵然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实在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永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分缘。
给我的孩子们
作者:丰子恺 朗诵:刘纪宏
我的孩子们!
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
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
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甚么事体都象拚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落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喷鼻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落手把他冲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频年夜人们的破产、broken-heart(极度伤心——编者)、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 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负责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姊姊讲故事给你听,说到“玉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不才面看”的时候,你何等冲动大方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姊姊不才面看!
”乃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至心肠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急速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审察,继而大失落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犹如对被剖断了去世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喷鼻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喷鼻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激情亲切!
大人间的所谓“沉默”、“蕴藉”、“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物化然!
”“生活的艺术化!
”“劳动的艺术化!
”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
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去世!
你们的创作力,频年夜人真是壮大得多哩:瞻瞻!
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般动它,与她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玉轮出来,要天停滞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宜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聪慧力不敷以搪塞壮大的创作欲、表现欲的使令,因而遭逢失落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以是你的遭逢失落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玉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以是愤愤地哭了,你们的天下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
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忆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
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刬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邋遢了袜子!
”急速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目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确当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罢!
瞻瞻!
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
瞻瞻也会裁了!
”瞻瞻!
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畅,何等得意的作品!
却被我一个惶恐的 “哼!
”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罢!
软软!
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瞥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年夜夫来,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乃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叫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倒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性的野蛮举动罢!
孩子们!
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畅;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象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象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关的人们 做了叫做“上课”的一莳花招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畅!
惭愧我为甚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畅我又得暂时放怀统统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期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履历过来的环境,也是大人们谁也履历过的环境。我眼瞥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豪杰,一个个退缩、屈服、妥协、屈从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
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久挽留这黄金时期在这册子里。 然这真不过象“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
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小橘灯
作者:冰心 朗诵:吕中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野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村落庄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惨淡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便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下子,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瞥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瞥见我彷佛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壁爬下竹凳,一壁点头说:“我要XX 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
”我问:“你知道XX医院的电话号码吗?” 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转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 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加倍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举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瞥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阁下。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大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探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表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逐步地从橘皮里取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逐渐地暗了下去,表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壁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 “入夜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
我讴歌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末了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
”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机动的小橘灯,逐步地在阴郁湿润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沉着、年夜胆、乐不雅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彷佛以为面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瞥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 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往后王春林也失落踪了,听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落,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由于我们“大家”都“好”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作者:鲁迅 朗诵:曹灿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个中彷佛确切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意见意义。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样平常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羽化,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由于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溘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衲人看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去世,而那老衲人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还是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真来了,沙沙沙!
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表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衲人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去世了。
结末的教训是:以是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以为做人之险,夏夜乘凉,每每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衲人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阁下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须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以是不合适,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弗成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壁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落的缘由,他只悄悄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大概是由于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大概是由于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大概是由于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师长西席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见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师长西席。
第二次见礼时,师长西席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由于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朴实,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由于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师长西席。
师长西席,‘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
”他彷佛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由于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每每如此,我遇见过好几次了。
我就只读书,中午习字,晚上对课。师长西席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逐渐加多,对课也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事情是捉了苍蝇喂蚂蚁,悄悄静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弗成了,师长西席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
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弗成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
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师长西席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快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狐疑这是极好的文章,由于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读书着迷的时候,于我们是很合适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名流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
再别康桥
作者:徐志摩 朗诵:张家声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边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