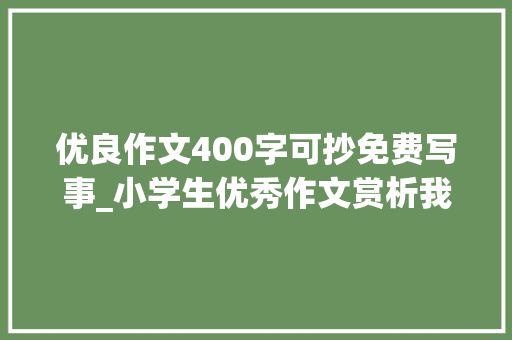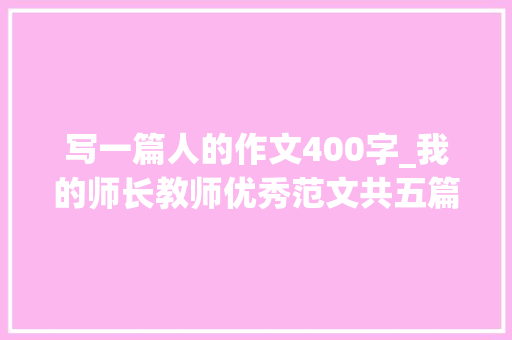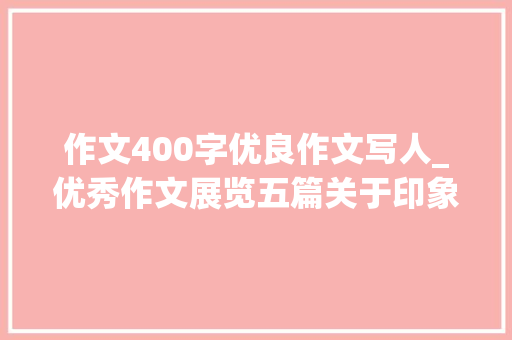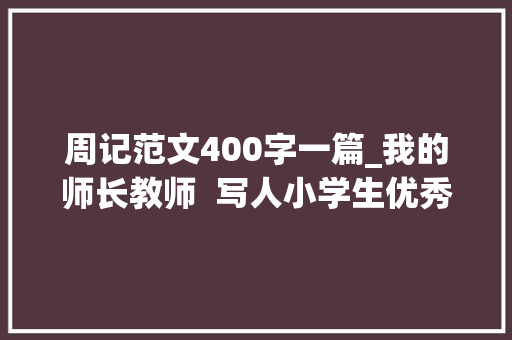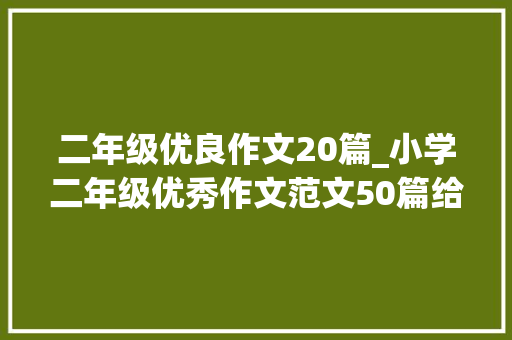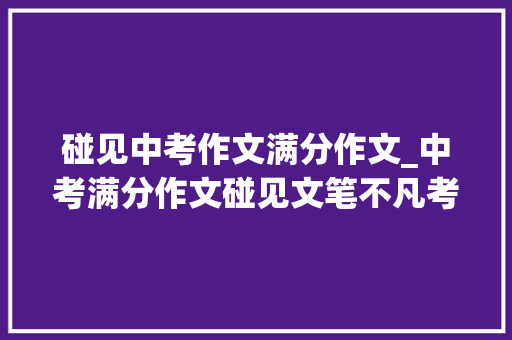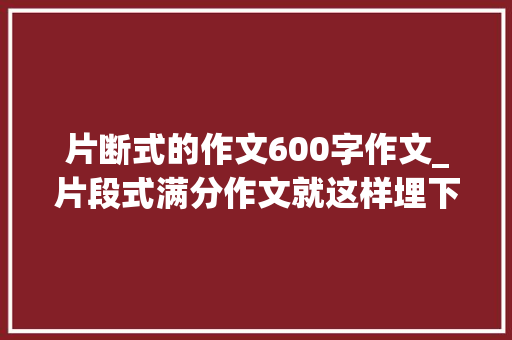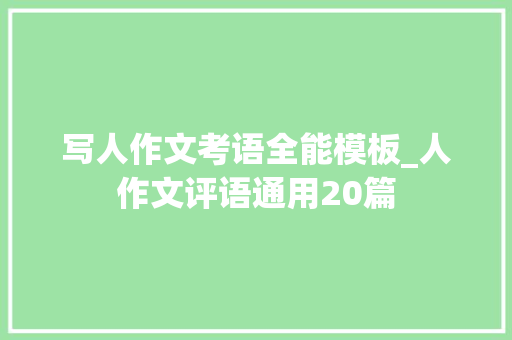老派文人见面,爱相互探听对方在读何书,而新式文人碰头,第一句每每是互问近日在写啥书。这段子出自梁实秋笔下,当然是不怀美意的调侃,是对当今文化人,读书稀疏、却“勇于著述”的一个嘲讽。
但我敬仰的当代文豪易中天师长西席,大概是足以推倒一世智勇的例外。2013年,在“六六大顺”之龄,他暂别《百家讲坛》的鼓噪,发布写作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果真,五年之间,以每年四册、近百万字的神速,皇皇20卷面世。论述范围,从先秦一起铲到了宋元,从女娲补天一贯写到改革开放,五千年变幻风云,尽在其盈盈一握之中。

这套巨著陆续出版时,我们的学界大佬们,我们的媒介报端,便是唯恐不及式的逢迎。什么“前所未有”,什么“一颗文化原子弹”,什么“可以闭幕个人史字写作”、什么“破译了中华文明密码”,彩虹屁无所不及,捧得易老师真磅礴烁烁,“如日中天”之状。
实不相瞒,等我笃信不疑,找来翻阅两三册之后,即失落望透顶:易老师的大作水准如何暂且不谈,单说我们的文化界生态就还是不免恶劣的。即便是樊树志、吴敬琏这等重量级的清流大佬,都完备将学术公器挪为了私谊相护的道具, 只有过场、背书及吹捧,没有几句实话。
马勇:易中天这么写,是回归到中国知识人的正宗上去了
各大佬们的高风、诸大贤的美意,我这般蠢笨之人自然难以领悟。只是,若说如何评价这套书,我就做躲角落里说三道四的那个小人,先匆匆笼统暗抛几块冷砖得了。
若有朋友大发慈悲施予稿费,倒是想全部买来读一遍,然后斗胆写一长篇见地书的。
易中天老师,毕竟是用过苦功的读书人,非泛泛庸籍,其笔力之健更早已传为佳话,晚辈如我素表钦敬。
以是这套书,论文笔、论质地,自然还是可以的,视角、遣辞、心态,都透着一股鲜活气息。我读来最大感想熏染便是“老到流畅”四字,老到在议论,流畅表示于行文。它真不是时下名人、大V、网红盛行套路,专搞粗编烂造、齐心专心抢夺读者花呗余额的庸书劣藉。作为大众入门级读物,自是适宜不过,求全责备似也不厚道。
但说实话,就这书,衮衮诸公拔的太高也尴尬,任何乏味的吹捧,似敬实亵。不怕冒昧,从稍高一点哀求看,总体而言,易老师的学问储备与史学功底,显然还不敷以驾驭这样一部古今中西一锅炖的通史,以至于此书在我不雅观感,是他在名收利遂之后,褪去自知之明,乃至原来“诗人意气”的暴躁之作。
从前的《读城记》,值得推举的一本散文集
学术不是面子工程。一样平常而言,读书作学问之人,是年事越大,披阅越多,胆子越小的。过去,国人共人所推尊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这干史学大宗师,年轻那会也是豪情万丈,时刻不忘要写出一部浩瀚的中国通史,到老反倒都缩手袖间不敢写了,并不算如愿。
何以故?很大略,只因中国历史与中国学问太幽远汗漫了,实际是一套通人之学,既要究察古今,又要牢笼中西,单单一柜“二十四史”都读不尽,又如何有胆子敢重新努力别辟门户,去搞出另一部更有新义的“中华五千年史”?
讲学中的钱穆
可以,储备不敷,自傲过分,已先天注定《易中天中华史》是一个仓促临蓐的早产儿。他的孱弱、娇嫩、乃至身心有障碍,都是与生俱来的病症,须要生产者不定期追踪检讨才好。
作为当代一部新通史,《易中天中华史》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在于下笔太快,弥漫着一股快餐口味。
可中国通史写作,是一桩大工程,毕竟不是美团外卖小作坊搞速食餐包那么轻巧。在我理解,其最忌讳亦是最难超过的弊端,莫过于两点:其一,是鹦鹉学舌式的陈词谰言;其二,是自我作古式的游谈无根。而易老师于此二者,都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可以说,任何追逐某种时期潮流的写作,一定短平快而无耐心打磨,就像潮男潮女追求一部新款Phone,绝非严明学者的正经活计。立意就已经暴躁,拿出来的成品,天经地义终难免位居下陈的尴尬,更难脱天桥练摊的格调。
公正地讲,易老师是一个脾气极生动、智力极发达、也身怀许多杂学技艺之人。他在通史写作方面,并非全然毛糙新手。在过去数十年书斋生涯中,他对付文学、美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等门类,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付写作思路有过很多的思考,也出过诸如《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成品,广受好评。
但以上这些,看似论史,究竟只是一鳞半爪的随笔闲谈,他实际从来没写出过一本踏实的、严明的史学著作,在史学专业研究上乏善可陈。因此,当他盲目自傲,痴痴要作当代司马迁,要为三千年国史独立自主作一盖棺论定时,他的储备、他的学识、他的见地、他的田地,险些一下子都捉襟见肘起来明晰。
可以说,这部书,论其误读、曲解及硬伤,真要挑刺,是比比皆是的。比如,该书第一卷大谈“轴心期间”,也顺俗搬来雅思贝尔斯压阵,可他似从未细想过这一套话的问题,将犹太先知也牵强附会地列入;比如,他对《论语》“三年之丧”“无后为大”等词句阐明,不丢脸出传统训诂学确实缺少演习;
再比如,他夸夸谈及唐代,率尔说唐朝是混血王朝,李唐皇室都是“异族血统”,表面上接续陈寅恪在讲,可是他似对《隋唐制度渊源论稿》这本小册子是不求甚解的,完备没有理会义宁大师后面的原话导致曲解,解释他读书不细而误解。乃至很大程度上,也显示他对外洋汉学研究是忽略的,不然何以对石见清裕这些汉学家同行的干系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只管他们早就有中译本上岸海内了。
可以说,《易中天中华史》这套书,只是粗读,即可觉察到太多问题,连各类硬伤,都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真的,我把这部书,看作是易老师由学术界大举进逼娱乐圈,由学者转型为明星后,得意忘形奋笔疾书出来的“退步集”。
萨义德有句话说,“批评常像一种寻衅找茬”。指出易老师这些“小节”,真并非故意自作高明的刁难。
的确,一部如此弘大的著作,有错或有不少错都属于人之常情,钱钟书的《管锥编》还不断被张文江、胡文辉那些后生挑刺呢,“历史”阐释更不可能就此闭幕于某一次写作,这也是它不断被重写的意义所在。
以是,我要指出的重点,在于说易老师写通史有硬伤,而在于他即便在阅读古书的点面上、理解故事的大要上,都多少存有问题,是不堪通史写作重任的。其表现,总体归纳,是要复述先哲每每不到位,想自树新义又常乏根据,导致很多篇章显得华而不实,立论多偏。
是易老师有言在先,说拜读其大作,并非纯挚学习历史知识,谆谆教诲读者不要在详细细节上纠缠对错,而哀求我们把全副关注点,都投放在他对历史的“觉得”上。易老师这番苦口婆心,确实深得海登·怀特等西方当代史学家们新理念的精髓。以60岁的年纪,尚能如此新潮,也其实是我等后生模范。
但是,我斗胆想对易老师陈说一个更为知识、堪为底线的史学不雅观念:历史的结论,是可以为“新史学”式的毫无定准,可是历史解读学与文学阐释学究竟大有不同,依然是要紧绑住文献依据的,“有一分证听说一分话”的,否则一味地“接管美学”,与天花乱坠何异?
书本部分
这便是说,任何一个史学从业者,倘要哗众取宠,显示出独树一帜的分歧凡响,并不难办;但是核心问题在于,那与众同异的东西背后,必得有一套信而有征的材料、有一个坚实的学术论证在作支撑,否则疯话是人都会扯,没什么大不了。
《易中天中华史》论学理操作上的毛病,也总体表示在这里。以是,这套巨作,诚笃说不要说能否实现易老师取代同类书、成一家之言的梦想了,连是否可当信史翻翻都是个疑问。它生动有余,严谨不敷,充斥太多作者个人的人生履历,与随意漫来的点评比附,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非纯粹史学书本。
当然,这个麻烦,也不能残酷地只归咎于易老师一人之身上。毕竟,平心而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所要面对的人事天下太过繁芜,所要攻陷的文献材料太过浩瀚,基本上任何个人的履历,都根本无法比较圆满地去阐明统统。如今的人们,早已无法像过去的中国哲人那样,可以“执一御万”了。 这种困局,也是开头所说的陈寅恪、吕思勉等大咖不敢去写通史的焦虑所在,犹如一阵阵无助的祷告,始终盘桓在每一个严明的史学家心中。
可以说, 自由过度的解读,加以轻率的自傲,一开笔就已经注定,《易中天中华史》太难熬过期光的筛选了。这不是易老师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草率下笔者的共同尴尬。
在上面,我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辞令手腕,对易老师作了略显尴尬的批评,但我的结论与用意,都不是要否定这部书。
我的个人不雅观感,假设不是太有学术洁癖,这部书作为小孩的入门书,或者成年人业余闲来读读,是足以的。此书腰封,印有一排能干的笔墨,称是“易中天开讲轻松好读的中华正史”,气概非凡,也确实达成不算太吹牛。它的生动流畅,可以给读者一种很时尚的读史体验,这是目前市情上各种通史都稀缺的品质。
以是说,只要不是大吹大擂捧称什么 “嘉惠士林的功德”之类,《易中天中华史》不失落为普通史籍领域一部好书。它的性子归属,不是《资治通鉴》式的,也不是钱穆《国史大纲》那般的,而更近似于蔡东藩。民国人在“正史”之外须要蔡东藩的“演义”,中国当代也亟需易中天此等学院中人“下海”,让普通读者在钱穆陈寅恪之外,也能兴致勃勃地读史。
因此,作为通史,这套书粗糙难免、花哨有余,史实、义理、考据方面均有较大缺憾,要“藏之名山”只怕是无望的。但它最好的秉性也在这里。乃至我以为,易老师何以要在早就成丛如林的史著中另辟门户,其良苦存心也在此守愚藏拙。可以说,要在字面上读懂《易中天中华史》很轻松,可要理解易老师及作品深意,却须要在文本外稍加揣摩。
也唯有这样,我们作为读者,为何要花费个600元巨款去买这套书,才能不摧残浪费蹂躏钞票吧。
《易中天中华史》要细论其优点,当然难以缕清,只是依照我的感想,其给人最大的欣喜,至少有二。
其一,是大气磅礴,草蛇灰线。知识面广阔,几汇聚古今中西;文笔论述上,轻松摆脱一样平常通史的呆板无味,能出之以诙谐与明锐,且擅以当下文辞去阐明古代人事,让人莫逆于心,该当是当下同类书中的俊彦。
比如,他会说,“商周时期是用眼睛看天下,春秋时期是用头脑看天下,汉唐时期是存心胸看天下,宋元有心无胸,明到了裤裆,清就到了膝盖”,写的喜逐颜开,充满兴味与激情亲切。这样的话,对错暂且不论,但是完备可以包管,司马迁不会这么说,陈寅恪也写不出来,他易中天驾轻就熟。
古人过去爱讲“学随术变”,易老师于此,可谓食髓知味。只管只为当前读者写作,只在乎一时虚誉,带来的遗憾,是常日也就与精品无缘。
其二,他的这套通史,问题意识、现实关怀、批驳理路,只管即便不显山漏水却又都是昭然若揭的。这是一种携带着极其强烈的启蒙主义态度的写法。依我揣测,这也是易老师“以是著”的最大关键点。
表面句句谈古史,却字字不忘现实,史为今用,借古喻今,这是《易中天中华史》精神独具所在,也是易老师 “学术光滑油滑”与“思想老辣”表示所在。我们都知道,眼下的学术研究也好,史学磋商也罢,日益学院化、专业化,技能化、封闭化、游戏化,与现实人间,与大的关怀连接不起来,史学的精魂这天渐在损失的。
易中天讲座中的听众
易老师在《中华史》写作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始终渗透着一种“回归史学本意”的思路,即强调史学、学术重新参与现实生活与大众社会的主要性。这也最大程度上,使得他的通史成品,不是另一个冷冰冰的、纯笔墨游戏式的知识玩耍,而是一个有厚重关怀的东西。
以是,《易中天中华史》“失落义求似”也好,“失落事求似”也罢,任何对此有非议的朋友,我想都须要把稳到这一点,好体谅到易老师的劳苦存心,也可以对这部实缺陷多多的书多些原谅。只管,作为一个浅薄且潦草的读者,我暂时只能言不及义,泛泛说及这些边角料。
我希望有余闲时,可以重新取来通读一遍,再写篇长点的议论,求教于诸位。当然,条件是得等我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