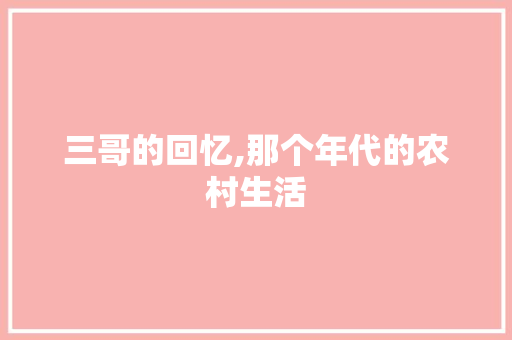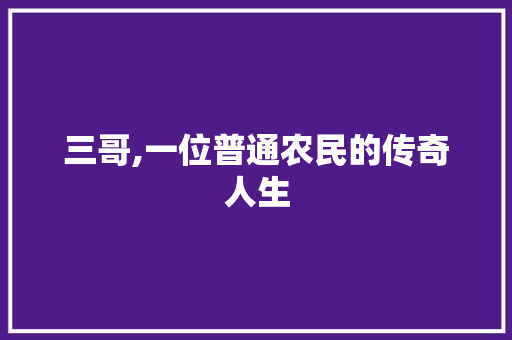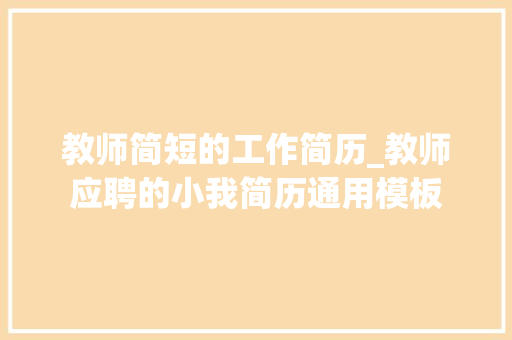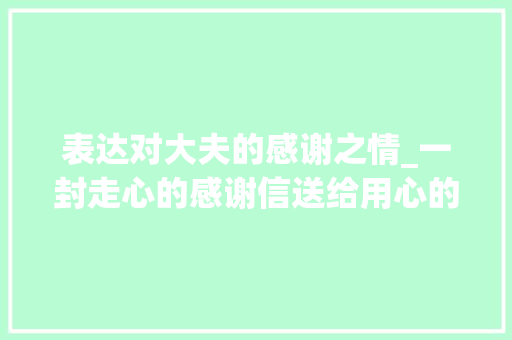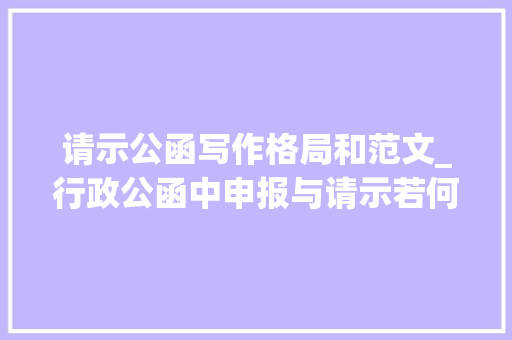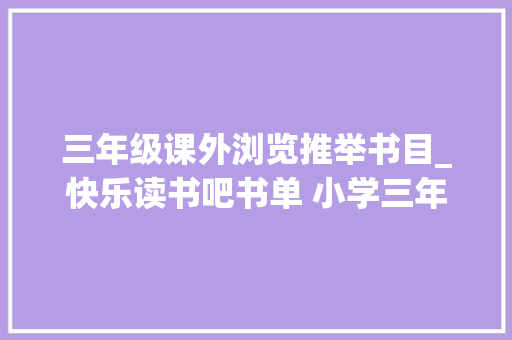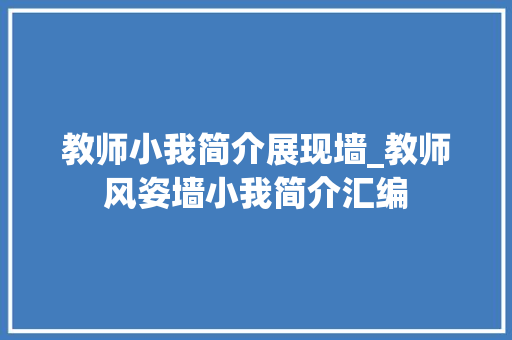震川师长西席集
此书二十年前买之于南昌,同时买到的还有一函柳文,两种书标价要五百八十四元,加上汇费五元八角四分,一共花了五百八十九元八角四分,在当时对我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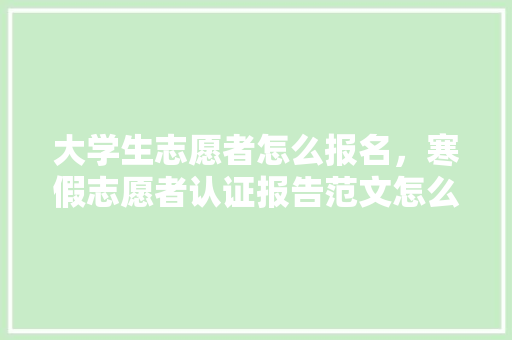
这次从中翻出了当年的汇款单和汇款收据,看字迹是母亲帮我填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钱比较多,母亲不太放心,陪我一起去的邮局。那时候买书没什么渠道,只能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信息写信去联系,索要售书目录,然后挑好想要的,并没有图片可看,只能凭简短的笔墨来想象,或者写信去问详情。末了再去邮局汇款,附言栏内写明要哪几种,这样一来一回要延误不少韶光。有时候钱汇过去,而你要的书已经售出了。卖家当然也不想把钱退回,就会其余寄一两种价格差不多的书给你,可是每每又是你不想要的。我之前吃过这样的亏,以是这次汇款的时候特殊留言注明“购柳集、震集,如无,请来信奉告,勿寄他书”。
我记得很清楚,为了凑这笔钱,我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攒的铜钱、银元托朋友帮忙卖掉了,实在数量没有多少,并无珍品,只是我从小的一种爱好,从几毛钱到一两块的铜钱,这天常平常从早点钱、零用钱节省下来买的,个中有康熙背局钱二十枚一套,我攒了十几枚,还差“福”、“台”、“漳”等几种。北宋对子钱攒了几十枚,明钱多少种,银元也有六七块,一起忍痛卖掉,换了两函旧书回来。
这套《震川集》一函十二册,共三十卷别集十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常熟刊本。卷端有“皕联山馆考藏”朱文方印,“永新刘郁文所藏”朱文长方印,当时并不知道刘郁文是谁,卖书人说是江西的一位先生长西席。后来有了百度,能查到一些平生。刘郁文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西省立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晚年有书名,惜只在网上看到零散图片,至今未见过真迹。书内有朱墨两色圈点眉批,校字是据万通书所校。批语甚精当,小字不及绿豆大,写得雅隽特立(下图)。
有两卷末端写了短跋,如卷二十二后面写了四五行,文云:
尝仰屋作企图,募得佳艇子,胜一架书,笔墨煎茶具并备,又同载得可语人,高秋好风日,浪游吴兴幽僻无人处,山水绝境中久之,复自笑此已大满意,然或所携书卷阙却归震川墓志铭一本,亦难免不免清福不敷之叹,六月大风客去后记。
细读也是一篇小品文,大有晚明人意味,大概来访的这位也非俗客。能看得出刘郁文十分在意归有光的墓志铭,前后卷中数篇都做了圈点,写了眉批,皆是有心得之语,非泛泛潦草者。如《雍里顾公权厝志》开篇批曰:
雍里郁不得志,文亦沉,勿使扬,忆少时相见苑长老,坐间论古文,长老性谐笑,每谈古今人,辄杂以花月间语,中特叹左传,而谓其有神,言文自妙,然必如震川作雍里权厝志神色,而后可以为神。
不知道刘郁文自己有没有留下什么文言著作,如今还能从这些只言片语里看出他对古文的热爱。我拿到这套书时,对归有光的理解仅仅是教室上学过的那篇《项脊轩志》,对照教材创造选用时删节了一段,刘郁文在不长的笔墨上写了几段评语,我读了读,似懂非懂,只以为和教室上老师讲的完备不一样。文章末了一句画满了墨圈,天头上写道:“能识云林子笔墨之妙则知此文。”于是我往后一看到枇杷树就想起归有光,想起这篇古文,想到倪云林画的那些树,那些石头。
中国神话故事
此徐正海姻丈三十年前所赐之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初版,袁珂著,高下两册,褐色封面,隶书题签,正面印有伏羲女娲的画像石图案,封底是朱雀瓦当纹。一起送我的还有两本白寿彝、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会我刚上小学,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是我家里没有书可看,想看也不知道哪里有,这些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
徐爹爹是我小姨夫的父亲,当时我小姨和小姨夫才认识不久,小姨夫家和我家离得很近,可以说是衡宇相望。从我家出门左拐上十几级台阶,沿着长青路的水塘向西北边走一百多米,路旁有棵巨大的法梧,梧桐树下有个幽僻的小巷子,巷子的墙根长满一种叫凤尾草的蕨类植物,巷子是去世胡同,走到头下几个台阶是个小院子,院里有一排朝南的二层楼,大概住了四五户人家,一门一户,每家都是楼上楼下,第一户便是徐爹爹家。
他家门口搭了个葡萄架,结的葡萄只有指甲盖大,颜色淡绿,核很小,去皮整吞,味道喷鼻香甜,如果吐籽的话就很酸。大概由于果实小,以是成熟得早,每年初夏就能吃到,从那时起,很长一段韶光,每年我都能得到一篮子这样的葡萄,皆拜老人所赐。他家里有一棵白兰花,我初次瞥见时摆放在门口的走廊上,险些有正门那么高,枝繁叶茂,满树着花。我们这里冬天冷,这种花木要搬到屋里,或者送到花房去寄存,等到开春再搬出来,是要细心照料的植物。我在亲友家中也见过种白兰花的,但是都不及这一棵高大,故印象极深。后来小姨成婚两家会亲,小表弟出生吃喜蛋,我随外祖家亲友来过多次,平时寒暑假或者周末和母亲闲步途经这里,只要小姨在家,我也要来这里玩一会。
这本《中国神话故事》是徐爹爹来我家时带来的,还是我去的时候给我的,已经记不清了。徐爹爹第一次来我家是某个初秋的傍晚,他听说先父有集邮的爱好,于是晚饭后夹了个邮册来拜访,相谈收藏之乐。这次还送了我一样小礼物,让我铭记终生,我小时候怕见外人,家里来客,总是躲在房里,那天恰好在做作业,索性躲着不出去。不一会母亲笑哈哈地进来,神秘地递给我一样东西,是用红毛线系着的三枚铜钱,一个康熙通宝,两个乾隆通宝。虽然只是通俗俗通的三个铜钱,市值不过一两块钱,但是我高兴极了,险些欢呼雀跃起来,这正是我心心念念想要的玩意。徐爹爹临走的时候,父母自然领着我向他道谢,我还记得他笑眯眯的样子容貌。
徐爹爹送我的这些书本,两种《中国通史》相对呆板一点,范文澜那本厚得像砖头,书脊是布包的,彷佛缺了封底,已经有些残破,内容竖排繁体,字又小,我看起来如读天书。小孩子识字有限,不大能看懂,只是随便翻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读读。神话故事就好看得多,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终年夜往后书越买越多,家里两个小书架已被堆满,直到旧屋拆迁,搬到新家,小时候看过的这些书依然摆在书架上。只是我离开家很多年,书口早就落满了灰尘。徐爹爹家的老屋子也早拆了,几年前我还乡常住,每天傍晚从徐爹爹新居楼下途经,常常能看到他和老伴牵着小狗在林荫道上闲步,有时候会打个呼唤,看着他们蹒跚地走远。
去年春天先父和徐爹爹先后逝世,相隔不过二十余日,给徐爹爹执绋归来,我在家里找出这本书,拿在手中,如遇故人,抽空在书尾写了几句话聊作纪念。东风再至,已是周年,重读此书,不禁泫然,叹岁月之不居,书在架上,忽忽三十余年矣。
楚辞集注
合肥四姊妹之一的张充和师长西席寓居外洋数十年,近二十年来逐渐为国人所知,随着各种宣布和书本的出版,渐成一文化征象。我起初看到《张充和小楷》一书,便已着迷,后来理解的多了,当然还有一层乡谊情结。最早全面先容充老和她三位姐姐的是《合肥四姊妹》这本书,封面印了她们年轻时的合影,充老小楷题写书名,下面盖了一方“楚人”印章,这方印是台湾王壮为所刻,其他作品上也见用过。我猜,大概是这里提到合肥才特意盖上的。
在先容老人平生的很多资料上有这样一段,说张充和幼年在合肥老家念学堂时,由吴昌硕弟子、精于楚器研究的考古学家朱谟钦(拜石)师长西席辅导,学习古文和书法。至于朱谟钦,彷佛很少有人提及,网上能查到的资料有限,拍卖涌现过他送给张充和的一本印谱,有署名题识,惜未遑移录。朱师长西席该当也是合肥人,别号朱楷,号拜石,曾在山东省博物馆事情,后任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部卖力人,随吴昌硕学过篆刻,有《校勘寿县出土古器物初稿》(1934年)、《安徽省立图书馆所藏寿县出土楚器简明表》等论著传世。不过当时的安徽省会在安庆,省立图书馆系在清代布政使司衙门的根本上增建而成,1934年将花厅改建成著名的寿县楚王墓(即李三孤堆)出土古物陈设室,1936年更名历史博物部。而礼聘朱师长西席在张家做塾师的李识修早在1930年已经去世,十六岁的张充和也离开合肥,回到苏州家中和姐妹们团圆。可能朱谟钦离开张家往后便到达安庆,开始图书馆的这份事情。早在春秋期间,楚国势力向东扩展。穆王四年,楚灭六、蓼,后又灭舒入巢,楚文化开始在江淮一带发展。到了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徙都寿春,这里距离合肥不过百十里地。看得出朱师长西席对楚文化有过深入研究,这一情结也深深影响了张充和。
充老晚年托白谦慎教授帮她处理身边长物,字画之类陆续让出,藏弆数十年的线装书就由我经手,放在北京拍卖。共计十三部:清嘉庆鲍氏仿宋刊本《太平御览》和清刊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是两套大部头。还有清听雨斋刊本《唐贤三昧集笺注》,清康熙刊本的《施注苏东坡诗集》《钱注杜工部集》,清咸丰十一年曼陀罗华阁本的《古谣谚》,清刊本《山海经笺疏十八卷附订伪叙录》,清康熙刊本《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清同治十一年望三益斋刊本《杜诗镜铨二十卷,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集二卷》,清乾隆刊本的《王右丞集笺注》,清乾隆鲍氏知不敷斋印本《列女传》,清光绪刊《楚辞集注》,民国刊《彊邨丛书》。
这几百册书都有充老的钤印和题签,从字迹来看,超过韶光该当不短。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上的题字,当是数十年前所写,小楷清健秀雅,一丝不苟。而《太平御览》上的则是九十岁往后所作,撇捺点画已入化境,可谓人书俱老。再如《苏东坡诗集》《山海经笺注》等,又见隶书挥洒,古雅非常。《张充和题字选集》的序文里就提过,当初孙康宜跟张充和提起耶鲁大学要为她举行“题字选集”书展时,充和师长西席半开玩笑地说:“我的那些题字啊,切实其实是小题大做了!”孙康宜听后,忽觉“小题大做”正是张充和的创作精神。她认为,张的书法之以是卓越而独具风采,乃由于她一贯本着“小题大做”的精神在努力创作:每次人家求字(哪怕只是几个字),她都一丝不苟,酝酿多时,逐步打好腹稿,然后才展纸搦笔,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写出气势,调好布局,才浓墨淡出,一挥而就,完成上佳之作。试不雅观这十多部图书的题签,谓之“小题大作”,小而弥精,不也正是一部浓缩了的小小题字选吗?
我手头的这部《楚辞集注》是个中之一,这套书一函四册,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刊本,内收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钤有“吴县利娃村落夫朱锡梁梁任印”,知为朱锡梁旧藏。书中通篇有朱笔点定文句,集注八卷据闵刻本校过。目录上有一段小楷题识,署“甲午五月”,惜题名处被浓墨涂去,不能辨其是何人手笔。据韶光推算,1954年甲午充老初到美邦,正是忙于家务的困难岁月,恐无暇顾及此类雅事。而1894年甲午充老尚未出生,朱锡梁已二十二岁,当然有校书的能力。后语六卷有几则据乐府诗集的校注,字迹与前面小楷完备不类,且夹有印着英文的纸条,倒可能是充老后来看书时随手写上的。每本书的封面有篆书题名,因从未见过充老写篆书,故而也不敢妄断。函套侧面粘一隶书题签,温文尔雅,苍劲古厚,确然是老人手笔。充老去国离乡之时没有带书,这些都是她在美国收得的,不是什么罕有善本,只是她平时的普通读物。但是书法昆曲的癖好离不开这些诗古文辞的滋养,这些书寄托的是文思?还是乡愁?我想她每次翻开这函伴随了她数十年外洋岁月的《楚辞集注》,或许更能体会到当年朱师长西席的教导和故乡的乡音乡情。
那年秋拍前我去喷鼻香港出差,在董桥师长西席府上拜不雅观了他珍藏的张充和墨宝好几件,那对有名的隶书对联,还有昆曲工尺谱,也聊到将要拍卖的这批线装书,我斗胆恳乞董师长西席为此题几句话,算是推举语,也算是广告词。桥公未加思虑满口答应。我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就接到邮件,几句口语文写的妥妥善帖,衬托着卷册缥缃一点也不突兀。几年往后,我带着这套书又到喷鼻香港,请董师长西席在卷尾用小楷题上了这段话:
冷落庭院,斜风小雨,充和师长西席险韵诗成,扶头酒醒,万千苦处都等闲。难得陪伴她大半辈子的缥缃像《潄玉词》那样无恙,随手摩挲不啻此生修来的福分,何况乞得一叶是一叶,那是江南早梅的!
晚年上娱
近几年有韶光在家里闲居,多出很多韶光和朋友们写信,我不喜好打电话,也
《晚年上娱》是我爱看的一本书信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收录了叶圣陶、俞平伯二老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五这十二年间的通信。插图有两位老人的影像、书信、诗稿等。扉页上我写了一行字:“甲申岁阑再游湖州时购于三联书店”,阁下还注了阳历日期,是二零零五年元月十六日。想起来那个冬天的旅行,放寒假前和浙江的同学约好去杭州玩玩,这是我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十岁时随父母一起来的。
这也是我第二次去湖州,上次还是头一年的暑假。定好韶光,我从家里坐汽车到合肥,拿着托母亲的同学陈姨妈帮忙买的火车票,晚上从合肥上火车,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到杭州。本来买的是硬座,附近春运,车上挤满了人,有座位坐就很不错了。上车往后我瞥见有人去找列车员补票,想想与其在这坐一夜,不如冒险试一试,于是抱着包挤到列车长那节车厢,排队等了半天,运气还不错,十点多补到一张卧铺,等我一觉睡醒,广播里说杭州城站快到了,我向窗户表面瞄了一眼,铁轨旁绿化带矮个冬青上面落满雪花,杭州居然不才雪。我之前读过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为之憧憬,没想到让我遇上了。
下了火车,同学来接我,我们沿着车站走到柳浪闻莺,然后绕行西湖爬上葛岭,站在抱朴道院眺望雪中湖景,可惜雪下得小,薄薄一层将要化尽,本想泛舟湖上一探湖心亭的心气也没有了。中午在道不雅观里每人花了两元钱,吃顿素斋,喝了两碗开水,顺带歇歇脚。下午又去孤山转一圈,傍晚我们乘车回到同学的老家湖州。第二天景象很好,同学领我去南浔,尾月里的小镇子宁静又安逸,我们去了嘉业堂、小莲庄、张石铭故居,大部分样貌还很古朴,不像现在的很多古镇景区,满是商业气息。这本书大概便是我住在湖州那两天晚上逛书店时买的,同时还买了哪些书已经记不清了。第三天我带着这本书又去了苏州,同学陪我在苏州闲逛一天,便各自散去,打道回府。我仍旧坐夜里火车先回合肥,越日天明再转车回家。这一起在车上坐了良久,六百页的书帮我消磨掉不少韶光,两位老人十二年间的你来我往像一条小溪,缓缓流淌,平白如话家常,穿插的文言也浅近。我刚刚走过的江浙一带正是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偶一提及,倍感亲切。那一趟瞻仰了俞楼,没来得及去曲园、青石弄。
此后十多年里,我给远方的朋友们写了不少信,有时候谈谈近况,互换下心得,有时候寄一张新写的字,聊聊在看的书,有时候便是零散写点,从来没有主题,没写完没尽兴的全靠电话微信办理。买此书时我以为写十二年的信会须要等待良久,没想到今日检点,一晃竟过去十七年了。
勤礼碑
《勤礼碑》是我的第一本负责临习过的字帖,是三哥送我的。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初版,一九八六年三刷,定价一元二角五分。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支配写大字,用过《小学生字帖》,记得是赵冷月题签,写完两个大楷本就停息了,从此再也没写过。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没有作业,父母给我报名上补习班,我在学校抽屉里捡到一支羊毫,拿回来乱写,从此开始了我的涂抹生涯。我家里没有人写羊毫字,也没有和这些干系的东西,当然也不知道写羊毫字还要有字帖这一说。
初二暑假,我和同学去一家裱画店玩,认识了三哥,他在家排行老三,住在鼓楼街九拐巷,和我外祖家旧宅一墙之隔,我外祖母称呼他祖母叫“邓妈”,按街坊辈他该当高我一辈,我称他三叔才对,当然这是后来熟习了相互理解才知道的。可是他为人很江湖,少年习武学书,身上有侠气,他跟我说,咱们之间不要客气,叫我三哥就好。我们之间共同的话题是从写羊毫字开始的,那时候他三十出头,刚从单位下岗,白天去裱画店帮人家看店,晚上在夜市摆地摊卖旧书。裱画店里第一次见面我瞥见他伏案写字,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就搭上话说了几句,当天晚上去书摊上一贯聊到半夜十二点,逐步熟习起来。后来他看了看我写的字,说这样瞎写可弗成,要好好临帖。我之前在旧书店买过几本字帖,像颜真卿的《多宝塔》《麻姑仙坛记》,赵孟頫的《妙严寺记》,印得很差,光是黑白分明,看不出石本的样子。三哥从摊上挑了一本《勤礼碑》给我,说这本还可以,你拿回去写写看。我那时候学习成绩很差,平时不敢在家写字,只能节假日抽空写两笔。直到高一暑假才有机会通临了一遍,看帖上记录的韶光,是从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到八月二十九日,每天吃午饭之前,我在用饭的八仙桌上写几页,家里订有一份《新安》,头天看完,第二天恰好可以用来练字,大半个暑假攒了厚厚一大摞。暑沐日间要做作业,补习作业,晚饭后的韶光才属于放松,我和三哥谈天能聊到半夜,他从没批改过我的羊毫字,拿去给他看时,总是找到优点鼓励表扬,然后天马行空地瞎聊,我仅有的一点书法知识便是这样在地摊上路灯下得到的。
有时候白天去找他玩,看他写字,他那段韶光楷书写《龙藏寺碑》,草书写《怀素小草千字文》。家里乱极了,只有书案上最整洁,我第一次认识砚台、帖架也是在这里。另日常平常干工作大大咧咧,有些不修边幅,但只要一坐在这张桌子前,就一下凝神聚气,如临大敌一样平常,充满恭敬和严明。临帖前裁好毛边纸,写楷书叠方格子,写草书叠竖行,叠好一摞放在案头,随用随取。三哥动笔必研墨,书毕必洗笔。我之前看别人写字,直接拿个碗或碟子,倒上墨汁兑点水。切切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有人用砚台磨墨。别人写完字大多直接套上笔帽,或者在笔洗里荡一荡,再在纸上掭一掭,意思一下就完了。三哥洗笔非要在水龙头下冲到笔毫发白为止,然后用废纸吸干水分,笔尖捋得直直地挂起来晾干,下次用之前用手指弹两下,笔毫疏松开像一朵花。一套流程如行云流水,看得民气境十分熨帖,十分惬意。
过了两年我去北京上学、事情,这本字帖随身带去。我开始逐渐学着他的样子每天磨墨,临帖,洗笔,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琉璃厂的书店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字帖,眼花缭乱,买了不少。又有机会上过几节书法课,老师是从美术学院来的,上课时让我们准备几本各体字帖,比如楷书选《张玄墓志》,草书选《怀素小草千字文》,隶书选《石门颂》,篆书选《毛公鼎》,巧了,这都是三哥跟我讲过的。我放假回去找他,他还在摆地摊,路边灯下接着夸夸其言地谈天。这么多年他换了很多事情,唯一没变的便是写字,他说他写字的时候很快乐。三哥最长的一份事情是在小区做物业,眼下还在做,每天处理各种杂事,帮助居民修理水电。年前他打电话找我,说单位组织给小区居民送温暖,让他约个人去写春联,我当然答应了。那天风大天冷,冻得手指头发僵,写完几百张红纸之后,三哥看看说你写了这么多年的字,气息还是憨实,结体用笔一看便是学颜体的东西,我大笑说这不都是你教的么。
作者:谭 然
编辑:安 迪、钱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