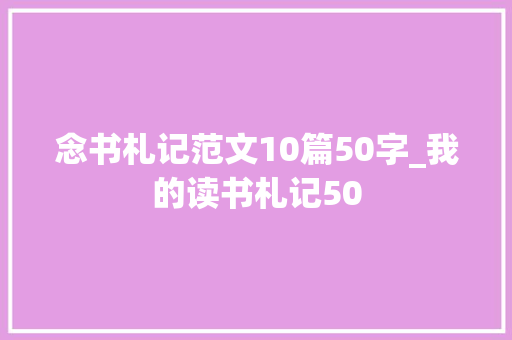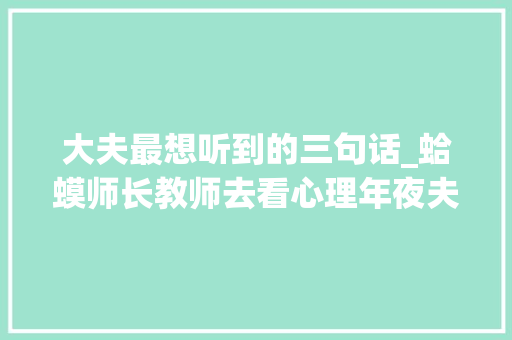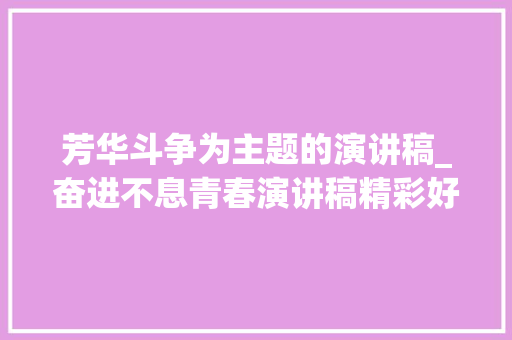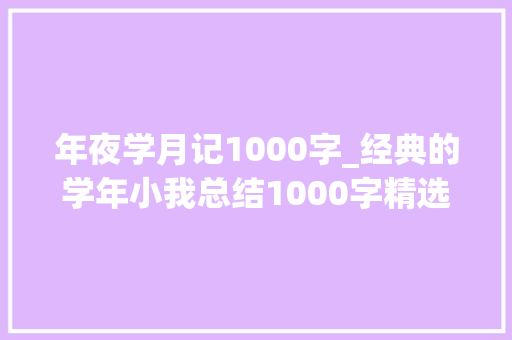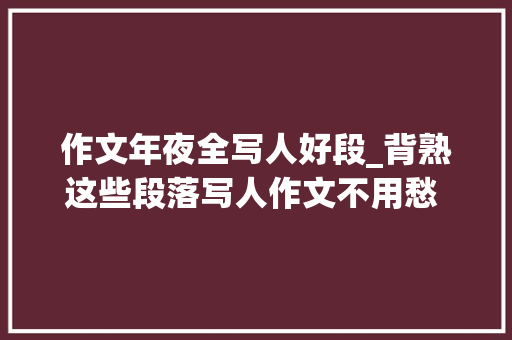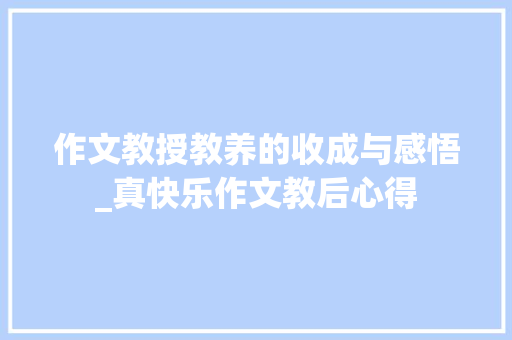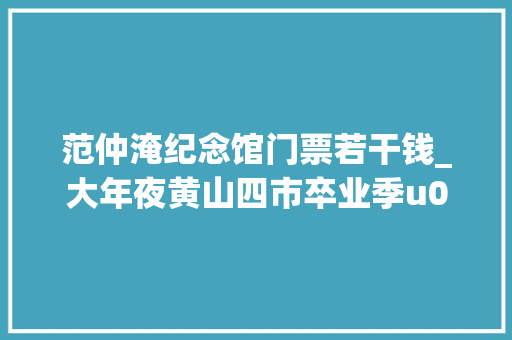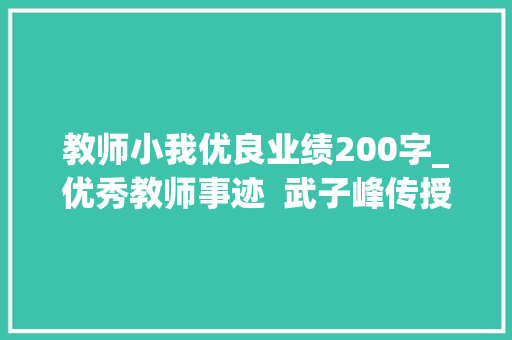话匣子便是收音机,北京人都知道。可为什么当年不叫收音机呢?我想可能跟我们国家那时还不会制造收音机有关。后来我们自己能生产收音机了,报纸刊登绝不会说国产话匣子制造成功吧,话匣子仨字太土了。随着商店有收音机卖,老百姓也逐渐改嘴管话匣子叫收音机了。
实在管收音机叫话匣子再形象不过了,一个木头匣子,里面能唱歌能说话,不便是一个说话的匣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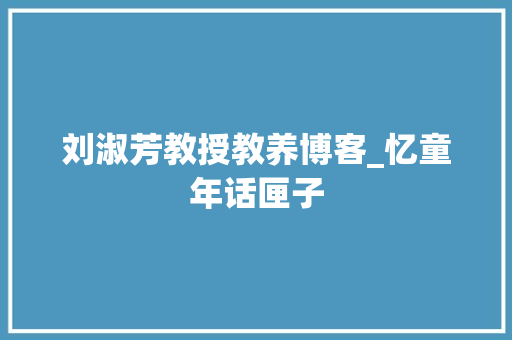
过去瞧不起乡下人,还用话匣子讽刺他们,说屯子人进城,见话匣子里面又说又唱挺热闹,心想这么个小木匣怎么能装那么多人呢?于是就把话匣子拆开了,想看个究竟。
笑话归笑话,也解释当年话匣子是奢侈品,不是大家都能听得到。那时候谁家假如有个话匣子播放节目,准有人围着听。
我小时候家里的话匣子这天本产的,黄颜色的外壳,三个旋钮,显示波段的荧光屏很小,但是声音清晰,质量还行。
后来父亲从国外带回一个“莫斯科人”牌的苏联收音机,它陪伴我一贯听到上山下乡离开北京。
有人问,你听了那么多年的话匣子,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回答说,印象最深的该当是曲艺节目。
“万人空巷”是句针言,形容轰动一时的盛况。文革结束后,刘兰芳播讲评书《岳飞传》曾涌现过这种情景。我记得每到中午快要播放的时侯,熙熙攘攘的大街急速变得人烟稀少,干活的也不干活了,开车的也不开车了,一簇簇的人聚在一起听《岳飞传》。
说实话,能让万人空巷来听评书,并不是刘兰芳说的有多么好,而是刚刚经由十年文艺囹圄的老百姓,太缺少除了样板戏以外的其它精神需求了。
评书说得好的,我首推连阔如师长西席,他说的《东汉》、《西汉》我没听过,但他说的《三国演义》我险些听完了全本。
连阔如师长西席说评书嗓亮音宽、气概伟大,尤其在形容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时,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觉得。
连师长西席是用连续不断的马蹄奔跑的声音,来表示沙场的伟大场面。他嘴里发出的“嘎嘎”声,先是断断续续,然后连成一片,真犹如千军万马向你奔来。
连阔如师长西席说完三国便偃旗息鼓了,后来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剥夺了说评书的权利。
我还听过马连登的《杨家将》,说得也好。我最爱听的一段是“杨七郎打擂”,马师长西席把杨七郎和潘豹在擂台上你来我往拳脚交加的情景说得活灵巧现,犹如亲眼所见一样平常。如果你一边听一边随着模拟,还真象那么回事。
后来跟别人去看曲艺节目,听报幕说西河大鼓的伴奏是马连登我还奇怪,心说马连登不是说评书的吗,怎么成了伴奏的了?后来才知道,马连登师长西席又能说评书又能弹三弦,还是马增芬、马增蕙姐俩儿的父亲。
提及马增芬、马增蕙,我也熟习,当然是从话匣子里熟习的。
马增芬唱西河大鼓最好,唱的最多的是《玲珑塔》,从第一层一贯唱到十三层,嗓音清脆吐字清晰,绝对是大师级的演员。
马增蕙的节目也听过,她唱的是三弦。他的儿子比她出名,如今彷佛也没什么了。
在所有的曲艺节目中,最随处颂扬的是李润杰说的快板书《劫刑车》。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象开锅”,这是《劫刑车》的第一句,在中小学里险些所有的男生都会来这么几句,《劫刑车》也成了各个联欢会的保留节目。
关学曾师长西席的北京琴书唱得好听,话匣子常常播放,记得节目有《宝玉探晴雯》,还有什么“二八的小佳人儿”。我那时年事小,对二八的小佳人儿不感兴趣,未曾负责听过,该当是后悔的事。
如果按兴趣来说,相声听的最多,侯宝林、马三立、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赵振铎、高英培等诸多的相声演员话匣子里全播过。尤其是马季和于世猷的相声,象《打电话》、《劳动号子》等节目,险些家喻户晓。
现在北京人管溜边儿走叫属黄花鱼的,还有想钓大鱼必须要烙糖饼等俏皮话,全是从相声里学的。
说了半天曲艺节目,实在孩子们最爱听的是“小喇叭”。
“小喇叭”是中心公民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最受孩子欢迎,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每天听。
至今我还记得“小喇叭”开始的第一句话:“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然后是嗒嘀嗒,嗒嘀嗒,哒嘀嘀嗒嘀”的喇叭声。
每当这个节目播放时,胡同里的孩子已经万人空巷了。
“小喇叭”里又最受欢迎的节目是孙敬修老爷爷的《西游记》。
那时你跟许多不识字的小孩谈天,他们能滔滔不绝地跟你大谈特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们知道红孩儿是牛魔王的儿子,铁扇公主是他妈。他们还知道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革和猪八戒的饕餮与无能。
这统统的统统,都归功于孙敬修老爷爷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孙敬修的故事终年夜的。
现在我偶而还听一次话匣子,如今话匣子已不叫收音机,改叫半导体了。平心而论,自从有了电视,广播电台的节目越来越没意思,大略乏味。不像过去,除了新闻和曲艺,还有电影剪辑和广播剧。
在听过的广播剧里给我印象深的是《孔雀胆》。
《孔雀胆》是根据郭沫若1944年著的话剧改编,讲述段功和阿盖公主的爱情悲剧,彷佛寓意很深。我对它印象深的缘故原由很大略,便是听了几次没听懂。这不能怪我,一个小孩子哪儿懂得故事所指和官府之间的权柄之争。
听不懂归听不懂,但演员的水平很高,通过演员对话和音响效果,连不懂剧情的我都被冲动了。
歌唱家李光曦如今年事已高,唱歌功力大不如前。但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我有幸听过他不少唱段,听得最多的是歌剧《货郎与小姐》。
“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喜悦欢畅的心情用悦耳的歌声唱出来,让你听得赏心悦目。
他的歌声风靡一时。
文革结束后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刚播出时我以为是那么熟习,但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逐步的回顾起来,五十年代中期话匣子里播送过。除了云南民歌,还播送王洛宾师长西席谱曲的许多民歌。例如《在那迢遥的地方》我很小就会随着哼,盖因听得太多的缘故。
当时除了我国的民歌,许多外国民歌也常常播放,以印尼和东南亚的歌曲为多,如《星星索》、《鸽子》等。唱得最多的是刘淑芳的《宝贝》,文革中刘淑芳为这首《宝贝》可遭了大罪。
唐朝落第秀才黄巢写过一首《咏菊》诗,里面有一句杀气腾腾的话是“我花开后百花杀”。
随着王双印的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话匣子里面播放的统统犹如“百花杀”一样,再也听不见了。
从此充斥于耳的全是红太阳和切切岁。
最可笑的是有首歌曲,从头到尾只有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是好”。整首歌把这十二个字反复地唱,来回地唱,不厌其烦地唱。
呵呵,恐怕别人说文革不好。
再今后,我离开北京,也就彻底和话匣子分开了联系。
过去话匣子里的文艺节目五花八门,内容繁花簇锦,质量很高。除了这些文艺节目最多的还是新闻,新闻又分早间新闻、晚间新闻和午间新闻。新闻是给大人们听的,孩子们不感兴趣,但是有一次我无意听到的一句新闻却给姑姑考试帮了忙。
一天中午我等着听评书《岳飞传》,播评书之前先播午间新闻,我听到一句“我国本日从朝鲜撤回万志愿军战士”。听到这句时刚好姑姑放学回家,我顺嘴对她重复了一遍,姑姑听到后答应了一声进屋用饭去了。
晚上姑姑放学回家对我母亲说,本日学校考试,问这次志愿军返国多少人,全班除了她谁也没答上。姑姑很得意,说亏了我给她重复了一句。
话匣子播送新闻不新鲜,这是政治需求,凡是各种媒体都要进行新闻播放,但是有谁听过记录新闻?
每天上午,中心公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都要在话匣子里一字一字的念新闻稿,速率很慢。我曾试着拿条记载过,只要会写字,完备能跟得上。
我想这种播送办法该当是照顾那些看不到报纸,但又要进行宣扬的偏远地区。把新闻记下来,再照着记录稿写成黑板报登载出去。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还是意犹未尽,话匣子里的回顾太多了。就跟现在离不开电脑一样,我们那时也离不开话匣子,它是各种知识的源泉,是百姓生活的精神补偿。
嫡黄花,现在除了出租车司机还在听广播,还有人听吗?有,为数不多的晨练老头。
(转悛改浪博客:马营海)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