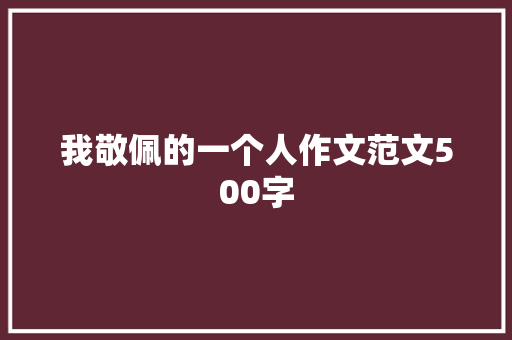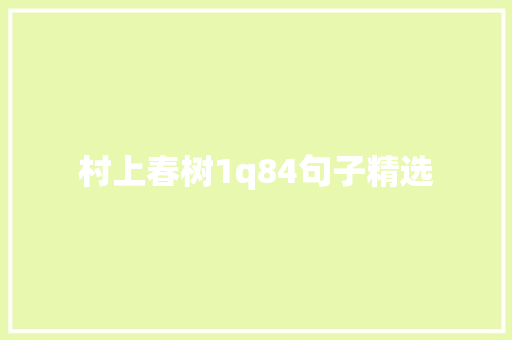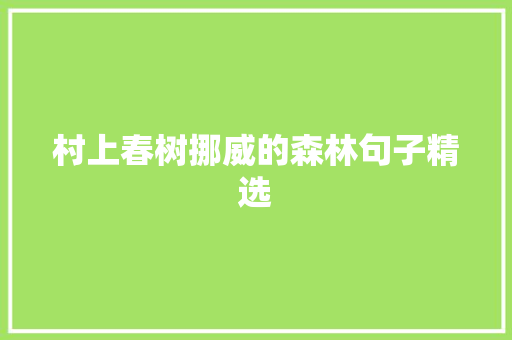名宦七人,然其宦迹皆不显,且囿于有明一朝,这里确实有些许奇怪的地方。乡贤十六人,范家洼范氏有范燧、范堤父子,新池车家有车钊、车宗汤、车朴祖孙三人,又有城关张省括、张大有父子,槐里康惠民及曾孙康乃心,皆合阳世家是也。范、车、张、康四世家之外,仅有七人。这里也有些许奇怪的地方。
无论名宦还是乡贤,我们说它们都有些奇怪的地方,那奇怪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名宦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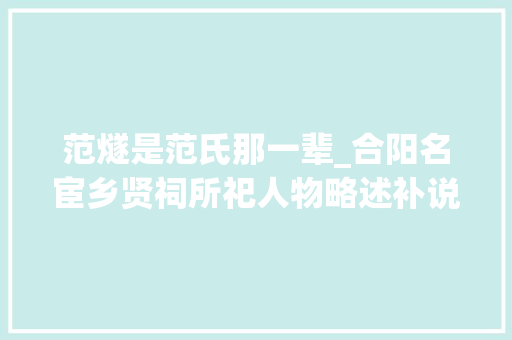
乾隆志有言:“名宦有祠矣,而士民不忘者,又别祀之,亦义也。”在名宦祠之外,合阳士民或立祠,或刊石,记其功而祀之者,“明邑丞龙塘叶公祠在东门外”,“三仁君祠在县治北,康熙五十八年,邑丞赵嗣隆为明邑令范君志懋、守府李君国政及国朝西安司李君秦镜保全合民建也。……先是,康太乙孝廉祀三仁君于北城谯楼,请诸当事,附春秋戊祭之例。今祠仍其旧名。”嘉靖时,宋奎、张道“二令者,合人皆勒石颂之”,“李豸,有去思碑,碑文韩尚书撰也”,顺治时,彭有义,“合人为建生祠祀之”,康熙时,傅瑞,“士民刊石记焉”,乾隆时,梁善长,“合阳名流为木主祀于华云叶公祠侧”。据此,名宦祠所祀者七人之外,又有宋奎、张道、李豸、叶弄璋、彭有义、傅瑞、梁善长等七人亦各有祠祀。
在这里,尤其须要把稳的是范志懋。范志懋既入名宦祠,又入三仁君祠,而其入祠之缘起则略异。据乾隆志,范志懋以怀来参议殉难,合民即于名宦祠祀之,等到清初,康乃心则初创三仁君祠。三仁君祠之创设,透出某种诡异,范志懋、李国政皆明末人,其所谓保全合民者,都是抵抗李自成之大顺军,而李秦镜则是从清军的暴虐中拯救合民。看到这种敬拜格局,不由人不想到雨果的一句话:“在绝瞄准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瞄准确的人性主义”。但是,康乃心肯定不是雨果,因此,这种敬拜格局显然隐含着其他的安排。
所有的敬拜都具有唤醒影象的功能,乃至便是一种可见的影象形式。康乃心创设三仁君祠自然也是期望唤醒某种影象的,因此,我总以为,他拉来李秦镜实在是做反衬的,在这种反衬浸染之下,范志懋与李国政的形象会更突出,而康乃心的吊念亡明之意也就昭然若揭。
据康乃心传记,三仁君祠的创设该当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往后,不会晚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也便是说在康乃心临去世之前的几年韶光里。在这段韶光里,他感慨先哲逸事湮废,为之立石作传,竟无虚日。
康乃心晚年的转变有些溘然,也奇怪。的确,明清之际,康乃心和顾炎武、李颙、李因笃、王弘撰等遗民来往密切,但后来就一贯在变,在适应新朝。为什么在生平的末了时候彷佛又回到了从前?我想,这极有可能与他的科第生涯有关系。有一个细节极故意味,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乃心参加会试,而同乡的张大有则分校礼闱,也便是做考官的。康乃心的会试不举,至少解释他完备没有受到同乡张大有的任何一点照顾。
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回过分来说合阳名宦乡贤祠所祀者令人奇怪的地方。名宦七人,如前所述,叶弄璋创设其祠所祀者仅六人,范志懋在其外。就这六个人看,除过前面所说宦迹不显之外,彷佛其仕宦经历都有些挫折,都是所谓穷而愁者,而叶弄璋表彰他们彷佛就显然有某种惺惺相惜的意思。如果不考虑叶弄璋贬谪生涯中无意识的动机,那么合阳名宦祠局限于有明一朝彷佛就可以理解,恐怕很少有人乐意和一群晦气鬼混在一起。当然,到了清朝,入祀名宦祠进而成为朝廷主导的祀典之一部分,也须要有相称繁琐的手续,合阳名宦祠的衰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名宦祠最初所祀仅六人,我以为,乡贤祠最初该当也是六人的,旁边厢该当是对称的。叶弄璋提到的七个人恐怕就会少一人,少的这个人或许岳崧。虽然叶弄璋称岳崧高节独行之士,然此前就有刘应卜的“赤帜录隐士岳景山于乡贤”,大概叶氏之前的表彰先贤便是用刘应卜的这种办法吧。
叶弄璋提到的七个人是岳崧、褚锦、王化、赵孟春、车宗汤、范燧、任守成,到了顺治期间,方志里提到的则是岳崧、范燧、车钊、车宗汤、王化、康惠民、范堤,这也便是说车钊、康惠民、范堤该当都是明末清初才入祀乡贤祠的。果真如此,乾隆志所称十六人中,车朴、张省括、李穆、张大有、王又旦、康乃心,就都是乾隆期间逐步入祀的。
总之,合阳乡贤祠所祀十六人中,其先后顺序可以排列出四个批次:第一批即刘应卜“赤帜录隐士岳景山于乡贤”,第二批是叶弄璋创设乡贤祠所祀者,即褚锦、王化、赵孟春、车宗汤、范燧、任守成,第三批是顺治朝或之前就已经入祀者,即车钊、康惠民、范堤,第四批是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入祀者,即车朴、张省括、李穆、张大有、王又旦、康乃心。
这里尤其须要把稳的是清朝入祀的两批,从中可以看出合阳士绅阶层的变革。大略地说,明末清初,范氏、车氏、康氏三族的影响极大,同时也可以说遗民群体在合阳地方影响极大,但是,康熙之后,张氏作为地方新贵则尤其刺目耀眼。就个人来说,王又旦不单因此科名更因此文假名誉入祀,康乃心和李穆则是由于保护地方文献而入祀。
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大概只有深入到范氏、车氏、康氏和张氏等世家的家族史里才能挖掘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