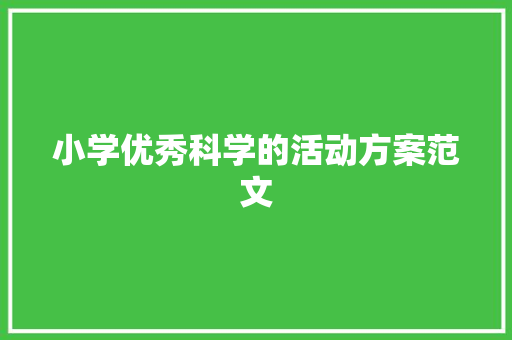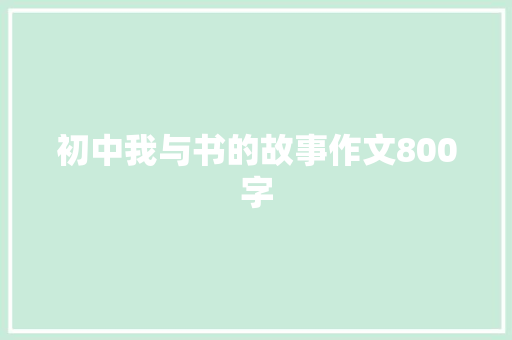前三部小说均为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末一篇的原作者为美国科幻作家斯特朗(Louise J. Strong)。《月界旅行》(1865)原题为De la Terre à la Lune(从地球到月球),英译本题作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in Ninety-seven Hours and Twenty Minutes(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从地球到月球)。日译本题为《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天下旅行》,井上勤1880年译出,分十册由大阪二书楼出版,后于1886年8月由三木佐助以合订本办法重版。《地底旅行》(1864)原题为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英译本不详。日译本题为《拍案惊奇•地底旅行》,三木爱华、高须墨浦1885年译出,九春堂出版。(山田敬三)《北极旅行记》原题为Les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英译本不详。日译本题为《北极旅行》,福田铁研(直彦)译。(工藤贵正)【1】 <造人术>原题为 “An Unscientific Story”(一个非科学故事),日译本题为<造人术>,原抱一庵1903年译出,收入《(小说)泰西奇闻》,知新馆当年出版。(神田一三 2001)
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由于外语能力以及知识不敷,鲁迅有不少误译。另一方面,鲁迅自己也没有虔诚原作的想法,不仅采取了意译的办法,还有很多为所欲为的增删。故翻译时“随阅随译,速率惊人”(沈瓞民 46),而每每与原作出入甚大。如《月界旅行》的日译本共28章,与原著相埒,而鲁迅“移多补少,得十四回”,又将“其说话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全集》,卷十,164),略去井上勤译本中多处先容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地底旅行》改动更大,凡尔纳原作由45章构成,日译本为17回,鲁迅更只取其骨架,改编为12回。《地底旅行》前半为故事,后半则是对有关科学知识的讲授,鲁迅未译后半部分。开头引人入胜的“解谜”情节被略去,第九回又插入底本没有的论述“胜天说”的百余笔墨(山田敬三 30-33)。鲁迅晚年回顾起这样的翻译时,承认“虽说译,实在乃是改作”(《全集》,卷十三,93),不无懊恼之意:“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忆起来真是悔之已晚。”(《全集》,卷十三,99)不过,鲁迅的翻译策略很快发生了变革。《北极探险记》已佚,无从查考;<造人术>的译文除了一处人名改动、另一处添加一句外,连转业、符号等也与日译本相差无几,是虔诚于原文的中文翻译。(神田一三 2001 : 38-39)虽然<造人术>只是一篇千余字的微型小说,但至迟在1905年,已经可以在鲁迅的翻译实践中创造“直译”的取向【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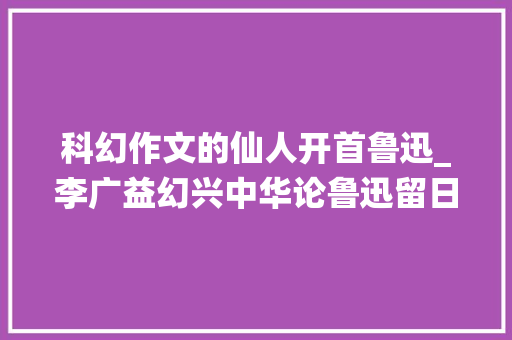
不过,也正是由于不受翻译底本拘牵,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等作品时行文流畅生动,激情旷达而又不失落幽美,使译作具有相称好的可读性,至今读来仍觉意兴盎然。如《月界旅行》第三回“巴比堪列炬游诸市 不雅观象台寄简论天文”述及众人欢呼情景:
此時ニ當テヤ大月恰モ人ノ天下ノ事ニ付キ叫呼喧嘩數千雑沓スルヲ解スルカ如ク雲氣四散中天ニ懸カリ光輝閃々朗明畫ニ同シク數千ノ松明為メニ賽雑セラレ其光ヲ失落シテ無キカ如キノミ就テ説ク數千ノ米人ハ尽ク頭ヲ擡ケテ蒼穹ニ向ヒ彼ノ燦熳タル月華ノ圆体ヲ觀テ……已ニ半夜ニ至ルモ猶熱心動揺ノ勢些少モ减スルノ色ナク其囂熱遂ニ市街ノ公民ニ波及シ學者モ巨商モ書生モ貧商モ車夫モ擔夫モ何トナク各處ニ衆合シ此回ノ大事業ニ熱心スルノ勢ナリ全市街上トナク下トナク或ハ埠頭ニ集テ酒觞ヲ飛ハシ或ハ湊腹ニ泊スル百般ノ船舶ハ船長ヨリ水夫ニ至ルマテ幾種ノ酒ヲ傾ケ空壺ヲ積累シ歡呼笑叫ノ聲ハ恰モ楚歌ノ如ク四面ニ絶へス或ハ空談ヲ為し或ハ論議ヲ發シ或ハ吻争ヲ起シ或ハ賛美ヲ稱シ人皆醉倒足皆蹣跚實ニ古來未曾有ノ景况ナリキ
加之天又凑趣,长空一碧,星斗灿然,当中悬着一轮明月,光辉闪闪照着社长,格外分明。众人仰看这残酷圆满的月华,愈觉精神百倍,……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热闹,扰扰攘攘,引动了街市公民,不论是学者,是巨商,是学生;下至车夫担夫,个个踊跃万分,惊叹这震铄古今的奇迹。凡是住在岸上的,则在埠头;住在船上的,则在船坞;都举杯欢饮,空罐如山。那欢笑声音,宛如八面受敌,嚣嚣不歇。
法文原文 【3】:
Précisément, comme si elle eût compris qu’il s’agissait d’elle, la Lune brillait alors avec une sereine magnificence, élicpsant de son intense irradiation les feux environnants. Tous les Yankees dirigeaient leurs yeux vers son disque étincelant; les uns la saluaient de la main, les autres l’appelaient des plus doux noms; ceux-ci la mesuraient du regard, ceux-là la menaçaient du poing; ……Minuit venait de sonner, et l’enthousiasme ne baissait pas; il se maintenait à dose égale dans toutes les classes de la population; le magistrat, le savant, le négociant, le marchand, le portefaix, les hommes intelligents aussi bien que les gens «vert», se sentaient remués dans leur fibre la plus délicate; il s’agissait là d’une entreprise nationale; aussi la ville haute, la ville basse, les quais baignés par les eaux du Patapsco, les navires emprisonnés dans leurs bassins regorgeaient d’une foule ivre de joie, de gin et de whisky; chacun conversait, pérorait, discutait, disputait, approuvait, applaudissait, depuis le gentleman nonchalamment étendu sur le canapé des bar-rooms devant sa chope de sherry-cobbler, jusqu’au waterman qui se grisait de «casse-poitrine» dans les sombres tavernes du Felles-Point.
较为虔诚的中译文:
彷佛玉轮也知道这与自己有关,它宁静大方地闪耀着,比周围的任何灯火都更加通亮。所有的美国人都望着通亮的月盘,有的人向它挥手存问,有的人甜蜜地呼唤它,有的人目测它,有的人挥拳威胁它。……时钟刚刚敲过午夜,可激情亲切仍旧没有消褪,它在公民的各阶层中都一样。法官、学者、贩子、小贩、脚夫,聪明人和无知的人一样以为被触动了最奇妙的神经,这是全体国家的奇迹。因此上城、下城,巴台斯科河边的码头和停泊在港口的船上,都挤满了沉醉在欢快、金酒和威士忌中的人群。名流们躺在酒吧的长沙发上,拿着雪利酒,水手们在波音特岗的惨淡酒馆里,喝“烧心”酒喝得半醉,每个人都在辩论、谈论、鼓掌、庆贺。
四段笔墨比照之下,我们不难创造,日译本较凡尔纳原文增删颇大,且多了些即兴发挥,如“欢呼笑叫之声恰如楚歌,四面不绝”(声ハ恰モ楚歌ノ如ク四面ニ絶へス)、“实在是自古未有的情状”(实ニ古来未曾有ノ景况ナリキ)。虽然不能打消英译本影响的可能性,但“楚歌”这样的中国文化典故被用到译文中,自然是井上勤不拘译格。汉文调的日译本已经相称生动,而由鲁迅信笔译来,文采飞扬的四字词持续赓续,而“云气四散”(雲氣四散)变成“加之天又湊趣,長空一碧,星斗燦然”,“空壺堆積” (空壺ヲ積累シ)形象化为“空罐如山”,凡尔纳原来平实的描写越来越华美,井上勤和鲁迅这两位“豪杰译者”真可谓“俱怀逸兴壮思飞”!
鲁迅之“意译”,虽不准确,但却很能表示其个性和发达朝气,“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清新雄浑,在当时译书界已经独树一帜了”(沈瓞民 46)。
其余,鲁迅对小讨情势的改造,也值得把稳。在鲁迅的译笔之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态。章回小说保存了宋元话本中开头引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系统编制,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每每在情节开展的存亡关头煞尾,用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中间又多引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袁行霈等,卷四,13)两部译作的每一章前,都有鲁迅自撰的对仗回目,如“新实验勇士服气 大创造巨鉴窥天”(《月》十二回),“拼生命奋身入火口 择中道联步向地心”(《地》第四回)【4】 。《月界旅行》每回末,都有鲁迅自撰的散场诗,如第五回回末:
正是:
啾啾蟪蛄,宁知春秋!
惟大哲士,乃逍遥游。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地底旅行》虽然没有散场诗,但和《月界旅行》一样,多择紧要处煞笔,大有“话本”之风。如“天文上的疑问,都已阐明;那东西却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说。”(《月》第三回末)“不知何时,忽闻有弹窗以呼者曰:‘亚蓠士!
亚蓠士君!
’亚蓠士心中一跳,跃然而起。”(《地》第一回末)
文中偶有穿插诗文,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即兴发挥。如《月界旅行》第一回:
晋人陶渊明师长西席有诗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
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像是说这会社同社员的精神一样。
第五回:
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妒忌,某诗说什么,“高峰突出诸山妒”【5】 ,这是在在皆是的。
至于翻译的措辞,《月界旅行》“初拟译以俚语,稍逸读者之思虑,然纯用俚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全集》,卷十,164),《地底旅行》也是如此操作。《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口语”(《全集》,卷十三,99)。<造人术>则纯是古朴拗口之文言,但又有简洁、明快的特点。
受“小说界革命”启示而进行的翻译,意在引介新文类,但译作又表示出一派古典小说的艺术意见意义,阐述语体也杂糅混乱,这种抵牾是晚清作家普遍面对的困境(陈平原12);详细地说,《月界旅行》等小说的翻译,受《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影响甚大【6】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造人术>尚直译,言古拙,这又反响了鲁迅翻译策略的调度。究其缘故原由,可能有二。一是《北极探险记》托蒋智由先容到商务印书馆时,竟被编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全集》,卷十三,99)。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快意增删,用语也为所欲为,而且并不以为自己的译法有什么欠妥,《月界旅行》出版后欣然寄给周作人一阅(周作人 1996:401),乃至在《地底旅行》篇末开了一个颇为得意的玩笑【7】 ,翻译《北极探险记》则连续翻新花样,“叙事用文言,对话用口语”,多少有些顽皮。商务印书馆这位编辑确当头一棒,显然给他不小的打击,也迫使他反省自己从前的“译法”。而翻译语体由“俗”转“文”的缘故原由,在于鲁迅深层思想的变动。袁盛勇指出,鲁迅的复古方向与其民族主义思想有密切关联,当鲁迅超越留学生的普遍水平而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文化民族主义的高度,“才在更高的意义上真正开始了独特的文化建构活动,他所由此而具有的‘复古方向’也才真正显现了自身的积极浸染”(2000a:6)。【8】 正好是在仙台,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项义华认为,鲁迅在东京时,生活在留学生社群中,“可以在思想上做一个异类,但毕竟在现实中还是同类”,而他虽不乏爱国情怀,但对当时的激进革命势力还是有所保留的,因此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离开漩涡中央东京,来到偏僻的仙台。在仙台,鲁迅是伶仃的中国人,变成了“现实中的异类”,民族意识强化,民族情绪也不断加深。(项义华 Chap. 6)另一方面,当时日俄战役正在中国东北激烈展开,鲁迅也非常关注。早在东京,日本人对清政府在战役中“发布中立”便大加嘲讽,鲁迅还曾因此与当地人发生过冲突(周建人 67);此刻仙台市民多次举行庆祝日军攻占中国东北城市的大会、游行(《鲁迅年谱》,卷一, 142),势必给鲁迅更为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感情下,鲁迅得到《黑奴吁天录》后一口气读完,随即在写给朋友蒋抑巵的信中,感叹黑奴悲惨命运,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傲心和自傲心:
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近数白天,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走运动,则彼辈为长。以乐不雅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全集》,卷十一,329)
而要光大“黄帝之灵”,重铸国魂,时人多认为应求诸中原民族悠久残酷的历史文化。(郑师渠 263-66)以是鲁迅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表现出复古方向——既要以小说“新民”,又要让这种文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说鲁迅返回东京后所撰写的几篇极为主要的文辞吐文是“文学复古”蔚为大不雅观的表现,则译作<造人术>可称为“文学复古”之先声;而用如此古拙的言辞表现以科技创造生命这一极具当代色彩的抱负,在中国科幻小说史和天下科幻文坛上都是罕见的奇不雅观。
二
鲁迅为自己的译作《月界旅行》写有一篇<辨言>。从这篇<辨言>中,不仅可以看到鲁迅留日早期的翻译方法,把握鲁迅的翻译意图,更可以从中发掘鲁迅此刻的科学不雅观念和文艺思想。而随意马虎被人忽略的是,鲁迅在文中对“科学小说”的阐述,是晚清期间相对最完全的一篇科幻理论磋商,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具有主要的地位。因此,欲理解和评价鲁迅早期思想和文学活动,当细读<月界旅行•辨言>。
工藤贵正指出,<月界旅行•辨言>第一段从交通角度追溯人类文明发展史,因此日译本片冈彻所作序为根本写成。(39-40)但片冈彻的序仅表现了对科学伟力的推崇,而鲁迅在回顾了文明之进步后,笔锋一转,“然造化不仁,限定是乐,山水之险,虽失落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缚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于是不少人不思进取,“沉沦黑狱,耳窒目朦,夔以相欺,日颂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羞者矣”。但人类又是“有希望进步之生物”,“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而此部小说,则“实以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
在鲁迅眼中,科学固然为征服自然之利器,但自然并不是可以轻易降服的,“虽失落其力,复有引力空气,束缚群生”。在这种情形下,态度成为关键。“至德”一语,源出<论语•泰伯>:“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正象征着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批驳“日颂至德”,可以理解为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守旧势力的鞭笞。而小说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以“尚武之精神”,写“希望之进化”,弘扬了追求进步的精神,也是进化史不雅观的表现。
其后鲁迅畅想未来,“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一定夷然视之,习不以为诧”。但于此乐不雅观奇想之外,鲁迅又言:“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小说中并未有此“星球大战”的抱负,是鲁迅自发之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虽崇尚科学,认为可促进“希望之进化”,但也明白,秉“尚武之精神”,则战役终无止境。因此过去并无“至德”之社会,未来也未必是和安然康的“黄金天下”。因此他感慨道,月界旅行乃“据理以推,有固然也”,而“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抱负”,今日“沉沦黑狱”,将来即便“地球大同”,而“星球战祸”又起,可供和乐隐居的“福地”“乐园”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样,鲁迅就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指出了进步的必要性,并对国民发出了号召,“冥冥黄族,可以兴矣”。这样,进化、进步的不雅观念,就和民族壮大的空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月界旅行•辨言>二、三两段,是鲁迅结合文本对《月界旅行》和“科学小说”的评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科学小说”要以科学知识为根本展开想象,“比事属词,必恰学理”。
2.“科学小说”乃“托之说部”,“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是一种文学形式。如《月界旅行》,其构建离不开人间生活,“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交融人间情绪,“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个中”,亦可讽世,“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
3.《月界旅行》虽富于科学,也并不是处处精准。“觥觥大谈之际,或不免微露遁辞”,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智有涯,天则甚奥,无如何也”。
4.《月界旅行》具有独特的美感。“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月界旅行》则不落窠臼,“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5.“科学小说”既“析理谭玄”又不失落文学意见意义,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功用甚大。“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虑,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而中国小说中恰罕见“科学小说”这一门类,该当大力提倡,“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
纵不雅观<月界旅行•辨言>,有两点值得把稳:
其一,鲁迅对“科学小说”的理解靠近于当代的科幻小说观点。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浪潮中,“科学小说”成为引介的一个主要门类,时人认为中国小说中没有政治小说、侦查小说、科学小说,“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 (饮冰等 83)。但晚清新小说家们虽普遍认为“科学小说”有主要功用,但在这种小说门类的观点上,却莫衷一是。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论及《新小说》杂志上准备登载的小说类型时,专门列出一类“哲理科学小说”,指出这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新小说报社 45),此外并无深入剖析。晚清报刊在刊登“科学小说”时,也胡贴标签,如<光绪万年>标注为“空想科学寓言讥讽诙谐小说”(吴趼人 1908),《新石头记》标示为“社会小说”(吴趼人 1905),而作者自认为“兼空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吴趼人 1989:359)。晚清所谓“科学小说”者,既有以科学为跳板跃入抱负天空的作品,也有用小讨情势罗陈科学知识的科普小说。鲁迅比较把稳“科学小说”中的抱负成分,不仅嘉许《月界旅行》作者“默揣天下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自己也有“星球之战祸又起”的抱负。因而,“科学”“抱负”“小说”这三个要素同时存在于他的论述语境中。此外,他还敏锐地把稳到这种小说的一些特色。如“遁辞”,牵扯到当代科幻批评多有提及的“硬伤问题”;其余,言及“科学小说”不“借女性之魔力”而有“光怪陆离”的独到之美,也提出了科幻美学的命题。他的“科学小说”不雅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代科幻小说家对科幻小说的理解若合符节(叶永烈 92-93; 黄海)。
其二,鲁迅提倡“科学小说”,意在遍及科学;而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他将“科学小说”视为科普工具,这固然是受“科学救国”的时期思潮之影响,而对“科学小说”寄予“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厚望,也高估了文学于改造社会之功用。但鲁迅所提“智识”是否仅指详细的科学知识,是否如有的论者认为,仅仅是希望“将呆板乏味的科学知识‘点石成金’”(吴岩),则该当结合鲁迅的翻译实践考虑。工藤贵正认为,将日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凡例>和<月界旅行•辨言>对照,可以创造其翻译目的是同等的,即“为了引进‘补助文明’的西方文化,防止‘智识荒隘’,有必要进行科学知识的遍及” (42)。另一位日本学者山田敬三比拟《月界旅行》日译本和鲁迅译本后,却创造日译本中详细记述宇宙天生和月球学说的第五回、记录人类曩昔积累的有关月球知识集大成的第六回,以及磋商将火箭发射地点定在佛罗里达过程的第十一回,在鲁迅译本中均被略去。《地底旅行》更有大删刈之处,这个文本前半是故事,后半是对有关科学知识的讲授(从《地球的出身及沿革》到《说创世时期的动物》),日译本完全译出,而鲁迅则没有译后半部分(32-3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底旅行》日译本译者正好在<凡例>中声明:“至末段觉系学术上最有益者,乃详细译出。”“后段地质学与动植物学,似宾实主,作者取笔题此书曰旅行,而其意即在后段。”综上,宇宙、月球、地球、动植物等诸般学说,正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知识”,为何却被鲁迅删去呢?至少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是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的阐明:“其说话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这表明,鲁迅在翻译时,遍及科学的哀求并不凌驾于译作的意见意义性、可读性之上,以是他对那些读之无味的大段科学知识陈述予以删节;另一方面,“一斑之智识”也不应片面理解为详细的科学知识,而该当包括渗透在文本中、更为宏阔的科学理念、科学天下不雅观,尤其是对鲁迅早、前期思想具有辅导意义的进化论,正如伊藤虎丸在比较福泽谕吉和鲁迅对近代科学的理解时指出的那样,“他们彷佛都没把近代科学只是当成个别知识,而是把它们当做新思想或新伦理来接管的” (61)。鲁迅言,“若培伦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正是点睛之笔。
三
以对鲁迅科幻小说翻译实践及其“科学小说”不雅观为根本,可以上溯鲁迅从前的发展经历,进而概括出匆匆使他在留日期间激情亲切洋溢地译介科幻小说的几个紧张成分。
第一,少年时期博览群书打下的根基。少年鲁迅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阅读极广。他受过较为完全的传统教诲,“险些读过十三经”(《全集》,卷三,138),但不是去世读经书的呆子,课下常兴致勃勃地抄杂书,描绣像,种花草等。纵然在教室上,他也常常“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寿洙邻 4)。知足求知希望并在无形中培养文艺意见意义的“业余爱好”得到了家中长辈的宽容,如父亲并不责备兄弟几个私购《海仙画谱》(周作人 1999b:796-97),而祖父对小说的提倡更使鲁迅“理直气壮”地大看小说,“介孚公的确喜好《西游记》,平时主见小孩该当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随意马虎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周作人 1999a:964)。祖父科场舞弊案事发后,鲁迅兄弟二人被送到大舅父家避难,后又到其前妻内弟秦少渔处,即娱园。秦少渔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的“说部”,他险些都买了,看过便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由鲁迅自由取阅。于是鲁迅在家中那“两三箱褴褛书”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等小说外,又读到了“各类《红楼梦》,各类侠义,各类别的东西”(周作人 1999a:936),“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根本”(周作人 1999b:795)。鲁迅日后翻译和创作小说,以及编辑《古小说钩沉》、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都受到从前阅读的影响。
而与科幻小说翻译有着密切关系而值得强调的,是抱负文学对少年鲁迅的影响。家中女佣长妈妈为鲁迅买来绘图的《山海经》,使他大喜过望,对长妈妈“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备消灭了”。数十年后的回顾,仍可见到鲁迅当时的激动,“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样子容貌,到现在还在面前”。(《全集》,卷二,255)《山海经》保存了不少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千百年来一贯是人们奇思遐想的源泉,至今仍为抱负文学的作者们供应着丰富的素材。鲁迅从中也获益匪浅,“第一是这引开了他买书的门,第二是使他理解神话传说,扎下创作的根”(周作人 1999a:951),更主要的是,《山海经》造就了他恣肆汪洋的想象力:“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疆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旷达丰富的想象来呀。”(周作人 1999b:794)他读过的书中还有《西游记》《镜花缘》《封神榜》《聊斋志异》等抱负文学,至于《绿野仙踪》《池北偶谈》《酉阳杂俎》《阅微草堂条记》等广涉怪诞、灵异的作品,更是不一而足。它们都勾引着少年鲁迅神游天外。科幻小说为抱负文学一脉,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引《山海经》《镜花缘》为例,大概其潜意识中以为这些作品中的奇山异水、神秘鸟兽和《月界旅行》中“光怪陆离”的抱负不无契合之处。此外,据周作人回顾,有段韶光鲁迅看了《十洲》《洞冥》中的神话,奇想大发,于是“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去世复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玄门的封建气,完备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空想乡,每晚连续的讲,颇极细微”(1999a:944)。翻译本便是二度创作,而译《月界旅行》时鲁迅的日文水平尚不是很高,又采取意译,兴致勃勃地在底本上多加发挥,就更有“创作”的意味了。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认为是他从前“口头抱负文学创作”的延续吧。
第二,学习自然科学的影响。鲁迅自陈:“我由于向学科学,以是喜好科学小说。”(《全集》,卷十三,99)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从前喜读《花镜》并动手栽造就物(周建人 2),不过真正受到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诲,是在南京求学的时候。鲁迅于1898年5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0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创办这所学堂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折中说:“江南办理矿务甫有端倪,……拟即挑选学生,调派教习,于陆师学堂内添设矿路学一斋,分习重力汽化地质等学,以备专门学堂异日之取材。”(《鲁迅年谱》,卷一,60)鲁迅自己也说“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全集》,卷三,436),算是个“工科学生”。在矿路学堂里,鲁迅习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多门当代科学 ,兼阅《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学著作(《全集》,卷一,438),从而具备了较好的自然科学素养。留日初期,在弘文书院的学习也增加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积累。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仙台习医”。
科幻小说对读者的哀求是比较高的,除了对生活的理解,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较好地欣赏科幻小说。由于科幻小说常常以某种科学技能的抱负为基本的情节推动力,而在阐述中又渗透着科学知识乃至科学的理念和向度,其审美代价和思想内蕴与这些特点有着密切关系。鲁迅钟爱科幻小说,亦与自身科学素养有密切关系。他学矿出身,对地质学和矿物学有浓厚的兴趣,缮写过《地学浅说》,采集了不少矿石标本,有下矿洞的经历,后又作<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而《地底旅行》正是一部以地质学和矿物学为基本知识背景的科幻小说,其主人公列曼和亚蓠士都是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自然让鲁迅倍感亲切,而大地深处的景象,也能唤起他对矿洞的实感。此外,熔炼学与测算学之于《月界旅行》,地质学、地理学之于《北极探险记》,医学之于<造人术>,都有显而易见的联系。
而在理念上影响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的,则是进化论。严复编译《天演论》,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对晚清思想文化界有重大影响。鲁迅在南京时读到《天演论》,深受吸引,即便后来受到长辈的批评,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依旧大看《天演论》(《全集》,卷二,306),并向二弟周作人推举(周作人 1996:278),又购读加藤弘之的《物竞论》(《鲁迅年谱》,卷一,79)。去日本后,鲁迅还常与许寿裳谈论《天演论》,乃至能背诵个中的<察变>等篇章(许寿裳 217)。他对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理解,明显有进化论的印迹,而且是经由严复改造之后的进化论。严复虽然在译作中加入了斯宾塞的不雅观点,把进化法则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强调了国际关系中“良好劣败,适者生存”的法则,但又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说”,赞许赫胥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的意旨,希望国人奋起自强,救亡图存。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认为这部小说“写此希望之进化”,并高呼“冥冥黄族,可以兴矣”,表示了他基于进化论的不雅观念对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理解和发挥。《地底旅行》在第九回插入底本所无的“胜天说”,显然也是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事实上,所有这四部小说的主旋律都是依赖人的聪慧、美德、毅力和科学的力量降服自然,乃至成为新的造物主,如<造人术>。
第三,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在南京求学时,鲁迅便读到《天演论》等新书报,但“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打仗,乃是壬寅(一九〇二)年仲春到了日本往后的事情”(周作人 1999b:843)。《知新报》《时务报》等维新报刊数年前便激起了鲁迅忧国忧民情怀,此刻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激情洋溢的宣扬更让贰心潮难平。鲁迅受维新救亡思潮影响,参加了一些新派组织,继而剪辫,作<自题小像>,意气颇为昂扬。如果说留日学界的政治氛围匆匆使鲁迅爱国激情亲切飞腾,那么他在文学方面的作为——翻译<哀尘><斯巴达之魂>和几篇科幻小说,则更多地表示了“小说界革命”的影响。鲁迅回顾从前读过的文学作品时,说: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瞥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瞥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全集》,卷四,472)
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中也回顾道,当时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梁启超、凡尔纳和林纾(1999b:843-44)。兄弟二人举出的这三位作家,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也恰从三个方面影响了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梁启超是晚清思想文化领袖,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创办《新小说》杂志,为“新小说”的创作和理论磋商供应了主要阵地,又着<新中国未来记>,译《十五小豪杰》(与罗普互助)等,引领着文学变革的潮流。“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付小说的性子与种类后来见地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周作人 1999b:897)可以说,梁启超所鼓吹的以小说“改良群治”“新民救亡”的理念,在这个期间直接规定了鲁迅对小说的取向。凡尔纳是晚清期间作品被译介第三多的外国作家(陈平原 1989:52),其《海底旅行》和《十五小豪杰》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周作人 1999b:844),起到了示范的浸染,让鲁迅大开眼界,领略了科幻小说之魅力。而鲁迅最早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便有林纾最负盛名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周作人 1996:276),从此成为林纾的虔诚读者,林译随出随买(周作人 1999b:887)。受到类似报酬的是严复,相应地,“桐城美文”的笔法也在纯用文言的<造人术>中依稀可见;至于《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在删节原作之后复而“这里补充一下,那里修饰一下”(钱钟书 85)的译笔,和字里行间的勃勃兴致,则颇有林译的味道。
四
在晚清文学文化语境中评析鲁迅留日期间的科幻小说翻译,可有如下之结论:
首先,这是化身为“小说救国”的“科学救国”。鸦片战役以来,有识之士痛感外人“船坚炮利”,进而认识到外人不仅有此利器,更主要的是“制器精也”,而“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李善兰 12),根本上在于科学的领先。甲午惨败震荡中国高下,学习西方、变革图强遂成为朝野共识,“科学救国”成为时期大潮中的强音。严复指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救中国之亡须学习西方,“而欲关照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线人,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也。”(严复 1986:43, 46)有研究者认为,世纪迁移转变期间维新人士遍及科学的实际行动可以概括为四点:创办科学研究的各种团体和机构;广设译学馆,翻译西书;创办报刊,宣扬科学;推动科技教诲系统编制化。(吴献雅)梁启超在这四个方面都有贡献,是“科学救国”的积极支持者。既然他认为“欲新学艺,必新小说”(33),则他把“科学救国”与“小说界革命”搭中计,鼓吹“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而成的“科学小说”,自是天经地义。受其影响、又具有相称科学素养的鲁迅作<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篇章,译科幻小说,这些行为都带着深深的时期印记。
其次,作为“科学者”和“文学者”的鲁迅,在翻译科幻小说这样的活动中,都得到了表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凡尔纳是常日意义上的“硬科幻”作家,其学识的丰富和创作态度的严谨使他的作品不同于后世某些科幻小说的“皮以科学,实以言情”,而真正做到了“经以科学,纬以人情”。因此,对付鲁迅而言,自然科学教诲形成的知识背景和在对东西方文明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在对译本的选择和改造中也得以表示。即便在弃医从文之后,他对科学的思考也没有终止,<科学史教篇>(1908)中对科学的批驳理解和接管便是明证。另一方面,弘扬科学的出发点部分地落实到翻译科幻小说上,又表示了一个文学者的特色。归根到底,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门类,笼统地称为“自然科学和进化论的先容和论文”和“文学批评或文明批评”之间的“过渡形态”(伊藤虎丸 59)并不得当。鲁迅自己说,在受到“幻灯片事宜”刺激之后,思想发生转变,认为“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长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全集》,卷一,439)。但是,笃信文艺能够“新民”,提倡文艺运动,难道不是从激情亲切洋溢地译介科幻小说就开始了吗?多年后鲁迅仍旧说作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全集》,卷四,525),可谓“吾道一以贯之”;溯洄从之,这种思想最初的表现就在于科幻小说的翻译。以此为出发点,鲁迅的“科学者”和“文学者”的品质都在延伸,并整合在政治哀求之中,完成于他对异质的西方文化从整体和实质上——而不是割裂成“科学”、“文学”、“政治”等诸多板块——的把握(伊藤虎丸 83-84)。
第三,在翻译这几篇科幻小说的过程中,鲁迅的翻译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翻译手腕从意译到直译,利用的语体也从俚语为主,“参用文言”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口语”再到古朴文言。因而,虽然迟至1909年周氏兄弟才在<域外小说集•媒介>中明确表示“特收录至谨严,迻译亦期弗失落文情”,并在译作中全面贯彻虔诚原文并“词致朴讷”的翻译原则,但这种原则早在五年前鲁迅翻译的<造人术>中就得到了表示。其深层动因,如前所述,是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一样平常意义上的反清反帝向文化民族主义的转变。由于鲁迅自觉地以政管理念辅导自己的文学文化活动,以是翻译策略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能性的操作,更反响了他思想的变革。
末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核阅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还可得出两个故意思的命题。碍于篇幅,本文不能进行深入磋商,但笔者不揣浅陋,试进行初步的勾勒:
科幻小说在东亚的接管。晚清中国能掀起“新小说”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在大量的翻译小说中,若以译者所据底本语种统计,译自日文的小说应是第一位(陈平原 71)。就科幻小说这一文类而言,更是直接管到日本科幻小说热潮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为了掀起科学技能启蒙的高潮,推动自然科学即“实学”的发展,也涌现了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的高潮。川岛忠之助1878年翻译了《八旬日地球一周》,揭开了凡尔纳作品日译的第一页,此后“科学小说”在日本非常盛行,凡尔纳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他讲述的各类故事引发了人们对梦想的追求。在鲁迅留学日本之前几年,以押川春浪的《海底兵舰》为出发点,日本又涌起了第二次“科学小说”的热潮(程麻 64; 山田敬三 28-29)。基本可以剖断,梁启超主理的《新小说》创刊号上涌现的“科学小说”这个名词,源自日语。尔后,梁启超、鲁迅、徐念慈、包天笑等多位科幻译者均依据日文科幻小说进行翻译,凡尔纳和押川春浪也双双跻身晚清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最多的五大外国小说家之列(陈平原 52)。伊藤虎丸认为,鲁迅翻译科幻小说,是鲁迅与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同时期性”的表现之一,而与其说鲁迅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在“西欧冲击”的某一阶段共同的时期思潮或教养当中自身所面临的选取什么和怎么样去选取的问题(12);那么,也可以说,科幻小说这一结合了科学与人文、富于当代性的文类在东亚两个文化附近、渊源颇深的国家相继兴起,两国文学文化界对这一新兴文类的接管既有相似(如以科学启蒙为基本目的;科幻多蕴含政治主题;原创在译本的持续影响下涌现等),相似中又有差异(如科幻译作涌现二十年后押川春浪才创作了第一部日本原创科幻小说,而在中国,仅仅相隔四年;明治时期的科幻热潮之后,日本科幻小说或与政治小说结合,或变身为面向少男少女的科学冒险小说延续下去,并经梦野久作、海野十三等人的努力而不断壮大,中国科幻小说则在晚清之后陷入永劫光的沉寂),本色上反响了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冲击之下所面临的选取什么和怎么样去选取的问题,以及两个国家不同的回答。个中蕴含的丰硕文化意蕴,值得深入磋商。
《月界旅行》及其他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问题。在19世纪,凡尔纳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一经问世很快便被译成英文,继而被翻译成更多的笔墨,得到各国读者的喜好。《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出版,旋即被译介到英美;井上勤在日译本《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天下旅行》的<凡例>中解释,他所据的底本是由美国“芝加哥”府“顿内利 咯义德”商会发行的(山田敬三 29);继而鲁迅再将日译本译成中文。《月界旅行》由法国到中国,也险些“环游地球”,不过耗时为三十八年。这一超过四种措辞文化的抱负之旅,无疑是“艰险重重”的:英、日、汉的译者统统是“豪杰译”的妙手,凡尔纳的作品抵达中文时已经面孔全非。米勒(Walter James Miller)在《详注版月天下旅行》(1978)的媒介<儒勒•凡尔纳的多面天下>中对19世纪的英译本批评道:“(译者)大量删削原文的结果,使得凡尔纳的科学、性情造型、诙谐,及其欲传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声音都遭消解。”(qtd. 山田敬三 33)井上勤和鲁迅也不乏自作主见的发挥。此外,不同译者译介凡尔纳小说的出发点也不一致,更可追溯到不同的时期背景乃至民族性情。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科学技能日月牙异的时期,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奇思妙想和寄寓个中的深刻思考无疑拓展了人类的肚量胸襟,而不断“接力”的翻译则组成了不同文化碰撞交汇的历史画卷。这幅画卷,仍旧等待着环球化时期的天下公民来打开 !
【10】
注释:
【1】 工藤氏并未提及《北极旅行》所依据的原来,笔者据日译者在媒介中对小说内容的先容和中译本(《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刘晖译,西宁:青海公民,1998)内容确定。
【2】 据熊融、戈宝权等研究者查证,《哀尘》译文和雨果的法文原文甚为吻合,应为直译(<关于鲁迅译述《哀尘》、《造人术》的考说>,《文学评论》(1963.3);<关于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文学评论》(1963.4);两文收入陈弄璋《<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鲁迅佚文佚事考释》,1-16,17-19);而据工藤贵正论述,鲁迅译文中的“译者曰”是对日译者森田思轩所撰序文的改造。
【3】 作为中介的英译本,因井上勤给出的信息不尽不实,难以确定。
【4】 据山田敬三称,《月界旅行》日译本的回目与原作完备同等,而《地底旅行》日译本已经模拟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回目分两行对句,回末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可见,文化背景附近的东方译者在改造西方文本时,在翻译策略上显示出某种同构型。
【5】 语出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之一),全诗为:“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庭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
陆沉预为中原叹,异日应思鲁二生。”据马自毅选注《康有为诗文选》。
【6】 拜会卜立德<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他>。
【7】 第十二回:“德意志人,也从此都把两颗眼球,移上额角。说什么惟我德人,是环游地底的开山祖师!
荣光赫赫,环球皆知!
把索士译着的微劳,磁针变向的奇事,都瞒下不说。”按,鲁迅译此书时署笔名“之江索士”,故此处“索士”乃其自况也。卜立德用戏谑的口吻评论道:“索士是鲁迅译此书时用的笔名,也便是说他在抱怨1863年德国人胆敢向1903年才动笔翻译的鲁迅掠美!
一样平常人只知道1920年代在巴黎有超现实主义派,不知道东方已有个鲁迅抢先。”(<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33)
【8】 木山英雄也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文学复古”的深层动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哀求:“周氏兄弟共通的反功利主义,是遵照庄子式的‘无用之用’的逻辑,希图依赖文学的力量使同胞纯粹无垢的灵魂觉醒,从而使衰弱的古老文明保有再生的希望: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反功利主义是为远大的功利做事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224)
【9】 据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的毕业执照,《鲁迅年谱》,卷一,66。
【10】 目前各国研究者从跨措辞文化角度对《月界旅行》以及凡尔纳科幻小说的翻译已有一些研究,如Arthur B. Evans, Jules Verne’s English Translations, Science Fiction Study 95 (2005.3), 80-104;卜立德的<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他>;以及上面引用的几篇日本学者的论文。但这些研究多局限在两种措辞之间,卜立德虽然勉强做到了参照四种措辞的文本,但其磋商中存在不少问题:所看的日译本仅为一小部分;对日译和汉译辨析能力较弱;从文化背景差异角度进行的剖析还不足深入;等等。个中有一些想当然的论断,不足严谨,如“英美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国作者大同小异,情趣约摸同等,因而艺术上的鉴赏大概也差不多”(<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29),又如卜立德只看了《月界旅行》一小段日译,《地底旅行》和《造人术》日译未曾得见,在好几处颇为武断地认为某些改动是鲁迅所为。真正能够深入把握四种措辞的文本,超过多种文化进行透彻剖析的研究,尚付诸阙如——无疑,这样的命题是对研究者学养的极大寻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