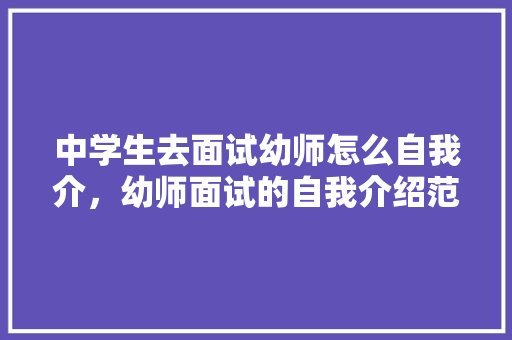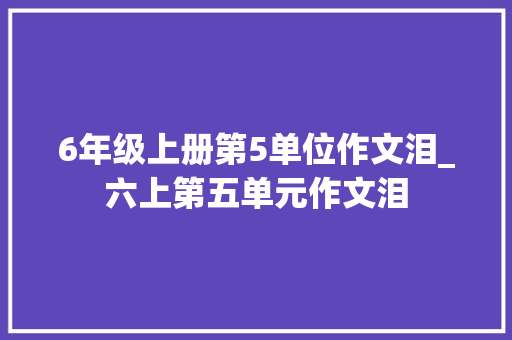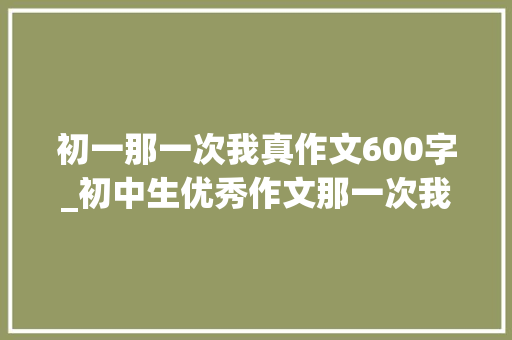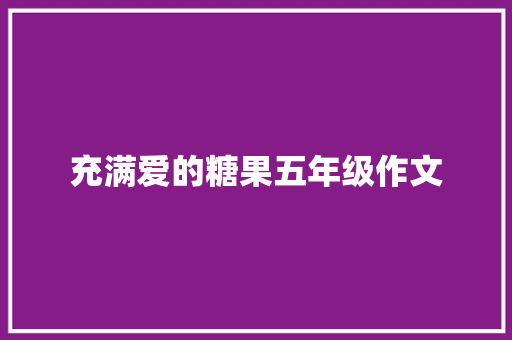那天我回去看她,穿过新建好的林立的摩天大楼,绕过新刷了漆傲气地立着的一排小高楼,艰难地找到了夹在它们之间一幢岌岌可危低矮的小楼。敲门的声音惊动了老人,她谨慎地把屋门推开一条细缝,看见是我,便露出一个惊讶而慈祥的微笑,拉开门栓迎我进来,按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蹒跚地走进厨房,端她刚蒸好的包子。
姥姥真的老了。她走进厨房的背影佝偻而拖沓,拖鞋松垮地趿着,与粗糙不平的水泥地面摩擦着,发出平缓而滞涩的响声。已是傍晚,屋里却没有开灯,室内的光线昏暗地打在赭红的地板上,散发出一片陈旧而腐朽的暗色。姥姥围着深棕色的围裙,劣质的染发剂把她的银发染成灰色,一双枯槁而消瘦的手搭在髀间,骨骼的轮廓清晰可辨,一张松弛的棕色皮肤搭在上面,青筋毕露熏染了油烟。我不记得这双手纤细光滑的样子,我只记得在我还在朦胧的阳光里终日酣眠时,就是这双粗糙的手为我掖上被单;在我肆意玩闹不知忧虑的时光,就是这双沧桑的手擦干净我身上的泥和尘土,捋顺我凌乱的头发,或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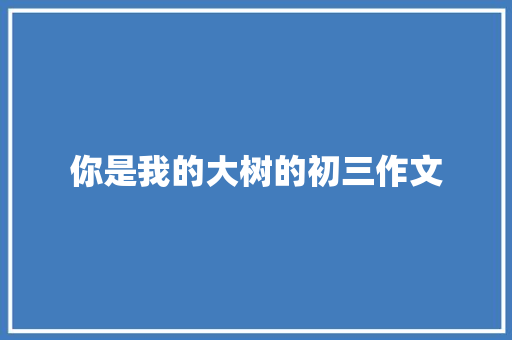
那时候家门口有一颗大树,挺拔油绿泛着明亮的光泽,我以只到那树干一半的身高痴想着树上泛着青绿的果子,便央了姥姥来帮我。姥姥从劳碌里抽开身,搬来一把椅子靠在树旁。我站在树下看着,姥姥站在椅子上伸长双手努力够着那颗果子,阳光重重洒下,覆了她一身碎汞。她的双手张开,脚尖踮起,像那棵挺拔油绿的大树,她的影子笼罩着我,像一个温暖的怀抱。
然后我一点一点长大,长过姥姥的肩,姥姥的眉毛,长得比那树干的一半还高,比最低的枝杈还高。姥姥老了,抬头含笑地望着我,我的影子盖住她的,在地面上缓缓拉长,像一个拥抱。
姥姥,你是我的大树,你的双手像大树的枝桠,你的拥抱像重重荫蔽。你没有挺拔的身躯,但你有挺拔的灵魂,像一棵不会枯萎的树,用生命的光亮庇佑了我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