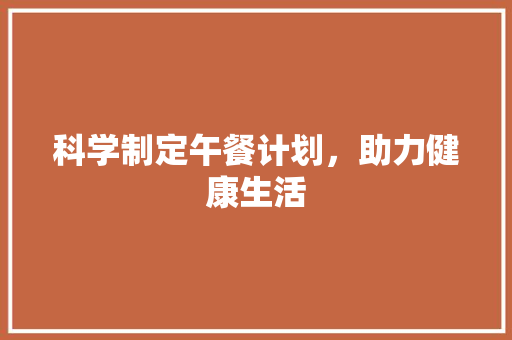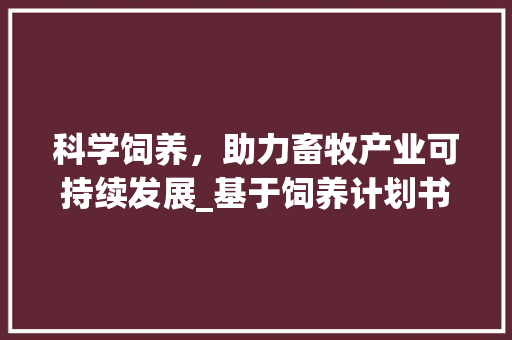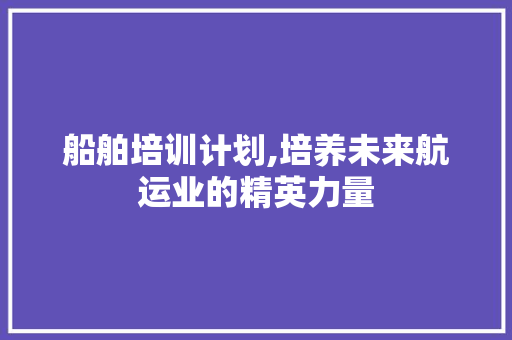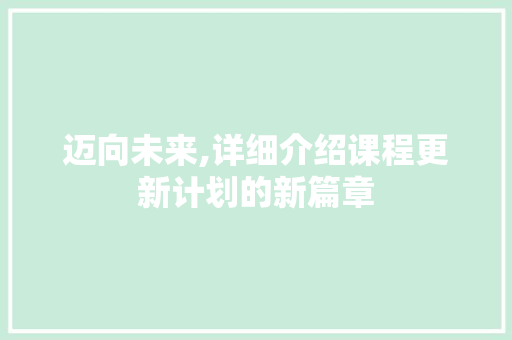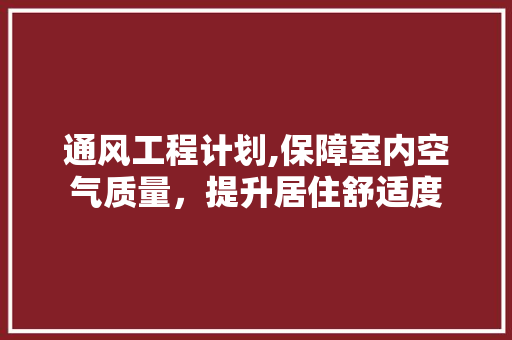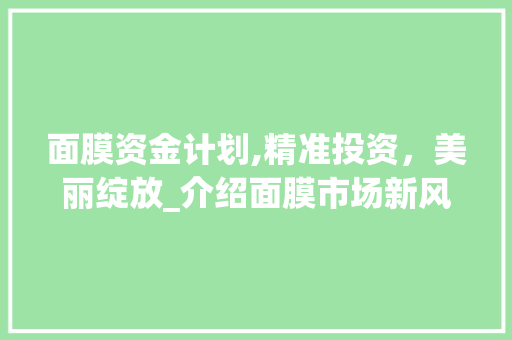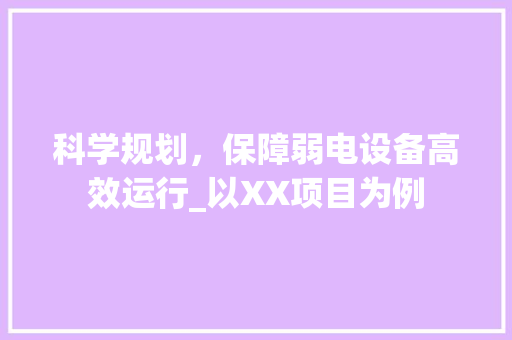宋代儒医与医学的巨变
儒医是对中古时期“士人”与“医者”“鬻技”与“医学爱好”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宋代儒医秉承唐后期士人阶层对医学的爱好,但打破了鬻技的生理障碍,从而带来了医人阶层乃至医学的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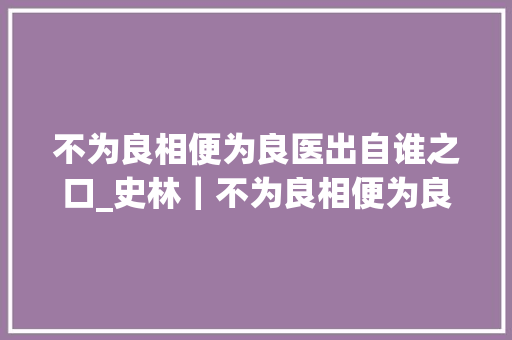
宋代儒医阶层的涌现是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尚医”行为的延续和升华,而这种行为的表示便是士大夫们之间医学文本的交流。士大夫以交流“信方”的办法公开磋商医理,并进一步塑造起以文本为根本的“更高”等级的医学研讨模式。阅读并且传承医学文本,原来便是医者的空想,是多种医学知识传授办法中最高真个,唐人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序文中将自己的著述初衷表达如下:“余缅寻贤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大家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
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多为欺诒,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他希望通过《千金方》的撰写,改变知识分子只习阅经学和文学书本的风气,以求大家通达医术。
中古期间医学知识的流传中,自学、家学、师徒相授都是主要的渠道。“关于春秋以迄于隋唐这段时空长河中的医学知识节制者,个人基本上因此‘知识人’这个词汇来概括他们。这里说的‘知识人’,在意义上实在是很笼统的,一个人只要在能读会写之外,再具备对传统中国医学知识思辨体系的理解能力,大概便能够纳入此一范畴”。
但是毫无疑问,最少在“知识人”的认知中,拥有阅读书本、解读书籍的本领才是一个医者鹤立鸡群的必要条件,例如许翰《修职郎宋侯墓志铭》:“宋侯讳道方,字义叔,世河东人。父曰可德,有隐操,好五行三式、星历丹经神奇奥衍之学,从方外士客游梁宋间,遂家襄陵。义叔年十五,念贫无以为养,则辍其所学诗书而学为医,取神农、帝喾以来方术旧闻,昼夜伏而读之,二年曰:可矣!
始出刀圭以治人病,每每愈,益自傲……义叔非有世业资借,专用古法以治人,邃张仲景,尊孙思邈。初以年少后起,邑中老医俗学者皆意轻之窃笑,已而见其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据依不妄,稍复畏而忌之。久而靡然屈从以定,遂为医宗,名号闻四方,缙绅大夫道过邑者必求见之。”在许翰的表述中,宋义叔卓然于众医者的缘故原由是“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从而使那些庸俗医者折服,使“缙绅大夫”无不视其为同类。
与欧洲古代的状况相似,宋代从事所谓“外科”和牙科治疗的一样平常都被视之为赳赳莽夫,“一见文繁,即便厌弃”,这势必便会招来时人尤其是儒者的鄙视,以是能否读书、能否通达文理是衡量医者水平的主要标准,最少在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文籍中是如此。
图为《苏沈良方》
儒医的特点
“儒医”的关键就在于儒,众所周知,宋代儒医的涌现与宋代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考试失落意儒者的增多密切干系,儒医的特点是在节制医疗技能的同时,行为合乎儒家行事的标准,这样的人便可以被时人称为“儒医”,在人们的眼中,儒医才是高明的年夜夫,而且其身份地位也由于近“儒”而有所提高。而且儒医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一句口号,那便是《能改斋漫录》所记载的出自范仲淹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口号奥妙地将“医”与儒祖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空想结合起来,使得儒而从医者可以摆脱生理上的耻辱感,安心于岐黄之术。
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有:“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遍及,医学知识随文本流传之势,益不可挡,其他各种依赖心传口授的技能却有渐被排挤的征象。”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儒医’如医之资来自研读医学文本,或流传宣传节制了医学经典的精髓。他们强调文本知识的主要,并边缘化了其他不依赖文本的医疗传统。而在商业出版较前代遍及的情形下,‘儒医’无法垄断文本知识,其他的医者和文人亦能节制文本知识而自称儒医,甚或有文人自认研读医学文籍的能力高于医者,反以自己的文本知识与医者颉抗。文本知识因此成为双面刃,一方面使儒医能隔离其他医者,却也使文人学士永久得以渗透其边界,寻衅其威信,儒医因而无法打消其他医者,垄断医疗市场;社会上亦无任何标准能确认儒医成员的身份。”
也便是说,儒医与世俗医之间有一道学术竹篱,便是文本,能通达文本者就能得到儒医的认同。“当时的年夜夫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履历,以及师徒相授的知识和履历来写作和传播医书。医学知识是一种成本,而且儒医则方向于把医书视为具有独占或排他性的传承办法。”
古代医术的传播办法是多种多样、纷繁繁芜的,绝不可一概而论,目前学界对付所谓“文本”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到了史料话语权的影响。历史上的文本的撰写者、受众、传承者当然会强调笔墨的主要性,也会在光阴流逝中逐渐以笔墨固有的上风凸显在历史影象中,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表达并不是务虚的,它终极一定会影响到后世的历史不雅观和代价不雅观,在历史影象中像大浪淘沙一样平常淘去其他模式,凸显自己,使得后世——尤其是像宋代这样高度崇尚文化的时期——更加认同文本所构建的代价不雅观,使得“文本”成为衡量医者水平、通报知识的象征物,进一步发展则成为全体医学的象征。不仅仅是医学,很多知识领域都存在类似征象。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