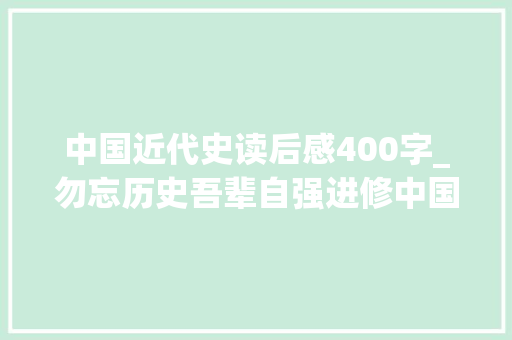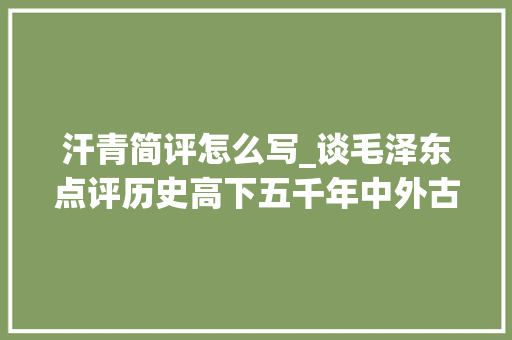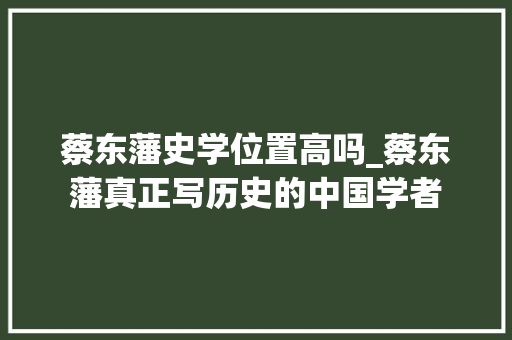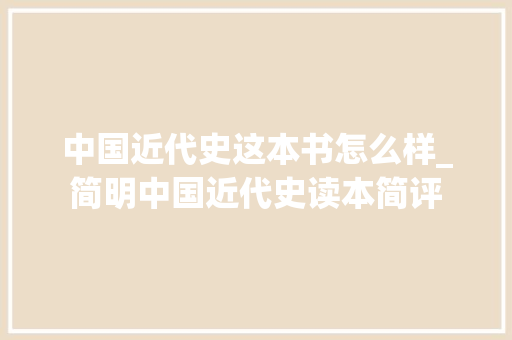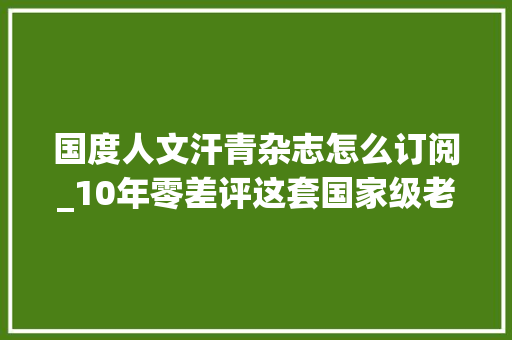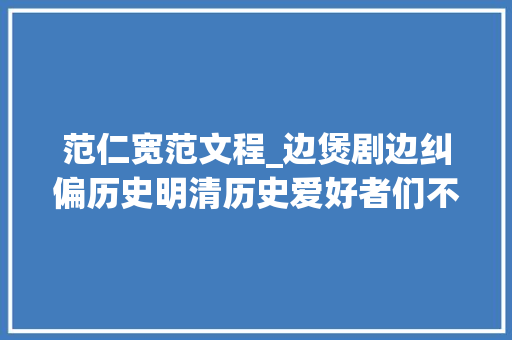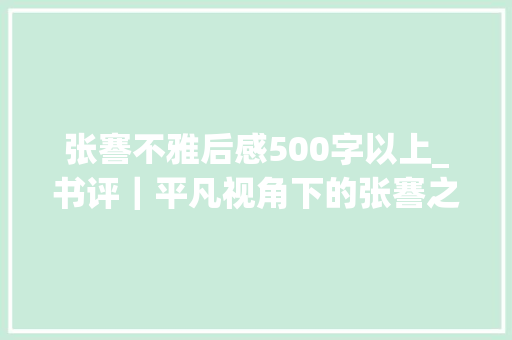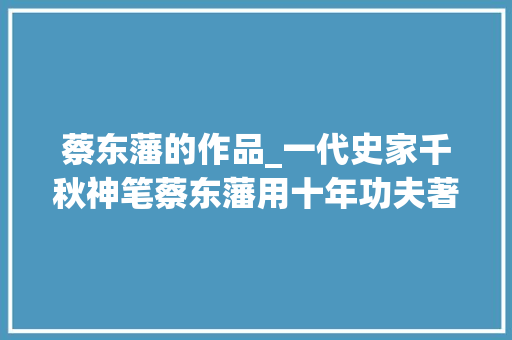作者简介:江湄,都城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引论:“历史条记”与历史影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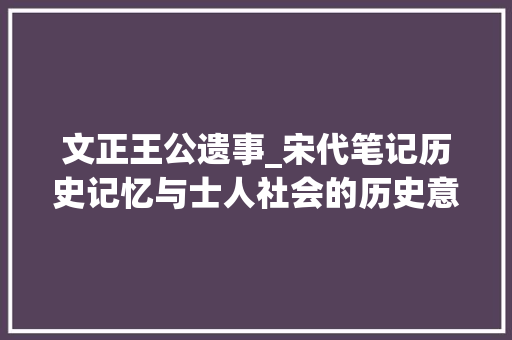
中唐期间,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为紧张内容的“小说家者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幼年说的作者自觉地以严明的态度记录有历史代价的见闻、经历,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供史氏搜集采取的撰述意识①。最有代表性确当属李肇《唐国史补》,其序载: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迷惑,示劝戒,采风尚,助谈笑,则书之。②
这就把条记体的“小说”中关乎史实的“野史”和故意虚构的“传奇”明确地加以区分,并规定了这类具有写史意识、史料代价的条记应有的范围和内容。两宋期间,这种“野史”条记加上有史学代价的考据、辨证类条记③,或可统称为“历史条记”,得到了突飞年夜进的发展。明人编《五朝小说》的媒介对宋代条记特点的论述十分中肯:“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骚,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④。
经宋、元、明三朝的发展,历史条记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要撰述门类和传统,而与正史、家史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明朝史家王世贞曾将史籍概括为三大门类,即“国史”、“野史”和“家史”。他指出,相对付“国史人恣而善蔽”,“家史人谀而善溢真”,“野史”虽然“人臆而善失落真”,但在“征是非,削讳忌”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浸染⑤。至编修《四库全书》之时,四库馆臣已明确将“稗官野记”和“正史”对立并举:“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⑥。
谢国桢曾给“野史条记”下过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凡不是官修的史乘,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条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⑦。历史条记作为历史书写形式,其特点在于:(1)相对付国史、正史的整全式视角,它以个人视角记述亲自见闻、经历;(2)与正史、国史力争站在一个全体的、后设的、客不雅观的态度上不同,历史条记反而刻意不分开主不雅观履历性,保留作为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主不雅观情绪和态度;(3)没有严整的编纂体例,即见即录,随忆随记,保留其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本来面貌。在西方文艺复兴的16世纪,包括日记、回顾录、书信集等在内的“个人的书面历史影象”呈现出来,“还是在这个世纪,史学涌现了,个人观点也涌现了”⑧。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个人的书面历史影象”的历史条记于中唐涌现,至两宋期间繁荣昌盛,蔚为大不雅观,这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条记的繁荣发展,是这些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科举入仕的士人们对付自身与家国历史之关系的一种自觉强调,是其以匹夫而任天下之忧的主体意识的深刻反响。从史学的角度而言,正是由于士人们自觉地参与建构本朝的历史影象,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促进了历史条记的兴起和繁荣,从而使保存下来的文献具有足够多样的态度和角度,留存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意见、多种声音,使历史的繁芜性在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正是随着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的深化和扩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征象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和内容,有关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才不断增多。以是说,历史条记既是宋代史学的主要特点和造诣,更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征象。本文将宋代历史条记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考试测验磋商其时代特点和紧张趋势,以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扩展的线索⑨。
一、北宋前期:五代旧臣的故国之思
自宋朝建立以来,尤其是宋太宗登基之后,大兴文治,大开科举,厚待文臣,彻底旋转了五代以来政权盘据的局势,确立和完善了中心集权的官僚制度。作为提倡文治的重大方法,太祖、太宗、真宗朝都进行了重大的图书编纂工程,尤其是号称“四大部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精髓》、《册府元龟》的编纂,以五代旧臣中著名的文人学者担当编修,一方面给予这些有影响力的旧臣崇高地位以安其心,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优待他们提倡尚文的社会风气⑩。在北宋前期的六七十年间,这些在五代就已经出名的文臣霸占着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宋初的文学、学术和文化也仍旧沿袭着晚唐五代的遗风。
北宋前期的历史条记也承接晚唐五代之余绪,紧张是五代旧臣及其后代记述有关故国的历史见闻。如,南平高氏政权重臣孙光宪所撰《北梦琐言》,在南唐即以文学有名的陈彭年所撰《江南别录》,以父荫入仕南唐的郑文宝所撰《南唐近事》,吴越王钱镠的曾孙钱易所撰《南部新书》,后蜀的句延庆所撰《锦里耆旧传》,后蜀的画家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南楚的周羽翀所撰《三楚新录》,等等。作为五代旧臣,这些作者大多怀有故国之思,抱着为亡国存信史的诉求,强调自己严明的撰述态度和求真意识。郑文宝在《南唐近事》序中痛惜“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乘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11),遂立志为南唐写国史。孙光宪多年来留神搜求唐末五代史事,他“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墨”。《北梦琐言》的不少条款都解释出处,有的还注明传说的歧异,以示有征和严谨(12)。
在他们看来,故国亡于大宋既是天意也是时势,并无怨尤,但是,他们对故国的历史持一种相对正面的态度,认为很多嘉言善行、明主贤臣不应被埋没,其衰亡也令人寻思和怨嗟。《锦里耆旧传》对后蜀主多所称美,四库馆臣遂据此认为作者句延庆很可能便是后蜀孟昶时校书郎句中正的后人(13)。黄休复《茅亭客话》第一至五条皆记蜀国归宋、天下一统的征兆,而紧张内容则是蜀中“高贤雅士、逸夫野人”,“可以为后世景仰儆戒者昭昭然”(14)。在五代诸国中,有关南唐的野史条记是最多的,这解释号称接续唐朝正统、崇尚文治的南唐,其士人有着较强的国家意识。据载,“南唐自显德五年(958)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不雅观中,碑多不题年号,后但书甲子而已”(15)。《钓矶立谈》在这方面很具代表性。其作者应是南唐校书史虚白之子,史虚白因与权臣政见不合而退隐,其子亦隐居不仕。该书序文写道,虽生逢“大同之庆”,但“私自弗郁,如有怀旧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以是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16),遂记录南唐一百二十余条史事成《钓矶立谈》,皆有关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作者盛赞南唐烈祖李昪的国策:把南楚、吴越、闽三国当作自己的樊篱,不开边衅,致力于内政,等待有利机遇完成统一大业。他认为,南唐的衰亡正是由于元宗听信佞臣,用兵闽、荆,甚至国削民乏。对此,作者以“叟曰”的形式言之再三,将憾恨惋惜之情表达得十分强烈。
这样的情绪和态度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大不一样的。欧阳修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撰成《新五代史》,时距《旧五代史》的成书已近百年,作为儒道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把五代十国的历史描述成一个阴郁的浊世,“有贬无褒”,通盘否定,其意是彻底划清“我宋”与“五代”的历史界线,以树立新的社会、政治和人格空想。为此,吴越王钱镠的后裔钱世昭在《钱氏私志》中说,欧阳修年轻时担当西京留守推官,“有才无行”,主座钱惟演曾讽劝之,欧阳修“不惟不恤,翻以为怨”,所往后来在《五代史》中痛毁吴越,不及其善(17)。
二、北宋中后期:变革、党争与条记撰写蔚然成风
仁宗庆历往后,古文运动、儒道复兴运动大势渐成,带动了全体社会、政治、文化风尚的更新,一批宋朝自己培养的新兴士人阶层的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孙复、石介、胡瑗,等等,他们提出新的社会政治空想、新的学术思想主见,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树立起新的人格典范和生活办法。思想的变革随即落实到了政治上,仁宗时,范仲淹等发动“庆历改造”;神宗期间,又有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在此期间,士大夫们根据自身利益、学术思想和政治主见的不同,结成党派,环绕“国是”之制订,彼此展开殊死斗争。就在党争激烈、“国是”屡更的过程中,宋朝走向衰败,亡于新兴的女真政权。
庆历往后呈现的宋朝文化、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所谓“绅士”、“名臣”者,纷纭撰写条记,蔚然成风。他们对付自身所处的时期和历史地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如苏辙自叙其撰写《龙川别志》的旨趣:“所见朝廷遗老……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之周旋,听其所请说,后世有不闻者矣。贡父尝与予对直紫微阁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去世,序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18)。他们知道自己是本朝历史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故意识地以历史人物的身份留下威信性的历史记录,为此,他们强调要自觉继续和发展中唐以来兴起的历史条记传统。欧阳修致仕前撰写《归田录》,表示要以李肇《唐国史补》为法,“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迷惑,示劝诫,采风尚,助谈笑,则书之”(19)。范镇致仕后作《东斋记事》,其《自序》云:“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20)。宋敏求与其父宋绶相继预修国史,自述道:“每退朝,不雅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21)。其所写《春明退朝录》多记朝廷典章制度和掌故,其后踵者相继,形成了典制掌故类的专门条记系列。王得臣的《麈史》尤其值得一提,他自从学于京师就养成了随笔记录见闻的习气,在其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线人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22)。王得臣致仕后重加刊定,以事类相从,别为四十四门,标以名目,内容涉及国政、典制、名公事迹、学术、风尚以至博弈、谐谑。这种见闻条记撰述态度之严明、体例之严整、内容之代价、记载之精核,已足以当一部史著。而这种史著的分外之处,在于个人的经历与家国历史水乳交融,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考求史料,更名贵的是从中得见身处当时历史时期之中的生动详细的个体情绪、态度和判断。
名臣名公之子弟也重视撰写条记,并形成一种传统,在两宋条记中霸占相称分量。这些人大多并不通显,但他们由于家世的缘故,亲炙当朝绅士重臣,熟习当朝掌故,理解黑幕,所见所闻每每具有很高的史料代价。如,宰相庞籍之子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宰相王旦之孙、工部尚书王素之子王巩的《闻见旧录》、《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三书,宰相吕公著之子吕希哲的《吕氏杂记》,曾以直龙图阁知广州的朱服之子朱彧的《萍洲可谈》,等等。这一期间还涌现了不少后世子孙记录先人言行业绩的外传、祖传类条记,如王素为其父王旦撰《文正王公遗事》,王钦臣记录其父王洙辞吐辑成《王氏谈录》,程颐记《家世往事》,苏籀陪侍祖父苏辙记《栾城师长西席遗言》,苏象先记其祖苏颂言行教诲撰成《丞相魏公谭训》,反响了北宋著名士大夫的“士族”意识,他们看重以先祖言行作为规范,形成门风,教诲后世。
地位不高的地方官、未入仕的布衣乃至僧人也热衷于撰著条记,所记多为与名流交游之所闻见,往往事关朝政、士风。僧人文莹曾自叙其撰写《玉壶清话》之旨意:“古之以是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23)不足闻达的有志有才之士之以是撰写历史条记也正是为了“传”,试图凭借书写历史争取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这些中下层士人对自身见闻之历史代价的器重,对本朝史籍写的积极参与,尤能反响当时士人社会历史意识的深化。王辟之及其《渑水燕谈录》是一个范例。王辟之是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仕不出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是宋朝一名普通的士人官僚,但他“从仕以来,每于燕闲得一嘉话,辄录之。凡数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噱,虽若噜苏,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24)。他以这样一种严明的态度来撰写《渑水燕谈录》,可见其以“一命之士”怀天下之忧的心志和风范。其书史料代价很高,元朝修三史时,袁桷在《修辽金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曾开列之。
北宋中后期日趋繁芜激烈的党争直接匆匆动了野史条记的发展(25)。有关庆历党争,就有托名梅圣俞的《碧云騢》、田况的《儒林公议》。王安石变法以来,党派斗争日趋白热化,熙宁、元丰期间,有新、旧党争;在哲宗元祐期间,旧党执政,但内部又涌现了洛、朔、蜀党之争;哲宗绍圣年间,重新上台的新党对旧党展开残酷的打击报复;徽宗崇宁年间,树“元祐奸党碑”,党争蜕变成大规模的政治伤害,为宋徽宗、蔡京集团极度阴郁腐烂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自熙宁年间之后,野史条记的撰写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党争之中。正如四库馆臣所说:“考私史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个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26)这样一来,历史影象和撰写就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关系繁芜且密切的斗争场域,并形成了多元的历史叙事和代价态度。
不同期间的一些主政大臣也撰写日记、条记。据南宋人记载:“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27)这实在是故意识地为日后国史编纂留下第一手材料,为自身的政治主见和作为留下证据,其本身便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元祐年间修《神宗实录》,多取材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到了绍圣年间,则被指为谤史,重修时用朱笔把原来记述抹去,而根据王安石《日录》进行删修,被称为“朱、墨本”(28)。司马光所撰《涑水记闻》不但史料代价高,而且著述态度严谨,每条皆注所述之人或出处,是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所作的资料准备,生前未曾整理编次,至高宗绍兴六年(1136),范冲奉诏将手稿整理成十册呈进。绍兴十五年(1145),由于秦桧严禁“野史”,其曾孙司马伋畏罪,上奏以为非司马光所作,诏毁版禁绝。司马光还记有《温公日录》,载录熙宁二年八月至三年十月事,紧张涉及这一期间的朝政大事(29)。王安石当政期间也记有《日录》,今虽不存,但仍留有不少遗文(30)。曾布是哲宗期间主持规复新法的主要人物,后扶立徽宗,在建中靖国年间主政,被蔡京排挤去位。他自绍圣元年起就开始记《日录》,今存世的曾布《日录》名为《曾公遗录》,自哲宗元符二年(1099)三月至元符三年(1100)七月,篇幅很大,其代价自不待言。苏辙于绍圣初被贬谪,元符元年(1098)复谪循州,“乃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记所梦”,撰成《龙川略志》。四库馆臣一方面认为“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另一方面又夸奖:“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于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
”(31)
党争之激烈匆匆使一些人从各自主场出发记述本朝历史见闻,为本党派的人物、政见、思想进行辩解,攻击反对派。不同党派上台,不但要重定“国是”,国史也要随之改易,最著名的便是从元祐到绍兴年间《神宗实录》的不断修正。在这种情形下,失落利的党派就要利用历史条记的撰述为自己说话,争取在历史上的公道地位,在有关党争的历史条记中,对历史书写权力的争夺是非常自觉、明确和激烈的。孙升是元祐重臣,绍圣年间遭贬谪后,由刘延世笔录成《孙公谈圃》,对元祐党人的言行记述颇多,其贬斥王安石自不待言,而对苏轼、程颐也时有微词。王巩是宰相刘挚的姻亲,元祐党人,生平屡遭贬逐,所记《闻见近录》、《甲申杂记》,多涉及“朝廷大事”、“贤奸进退”,党派态度明显。再如《道山清话》,其作者不详,但久居馆阁,熟知朝野士大夫遗闻,记北宋杂事至崇宁五年止,“书中颇诋王安石之奸,于伊川程子及刘挚亦不甚满。惟记苏、黄、晁、张交际议论特详,其为蜀党中人,固灼然可见矣”(32)。陈师道与苏轼、曾巩关系密切,是蜀党中人,其《后山谈丛》对党争各派人物褒贬分明,“笔力高简”。“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所撰《师友谈记》,于元祐党人尽遭贬黜之时记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不雅观、晁说之、张耒辞吐业绩,对王学“排斥笑谑之语,不肯少逊”(33)。魏泰是曾布之妻弟,未能登第入仕,元祐中记其交游所闻成《东轩笔录》,自称:“呜呼!
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存问于其间。”(34)他对新党人物及其内部斗争的记述颇详。朱彧的《萍洲可谈》记事止于宣和,其父朱服是新党中人,《萍洲可谈》“遂不得不尊绍圣之政,而薄元祐之人”(35)。此外,徽宗时人高晦叟的《珍席放谈》所记自太祖至哲宗,“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于安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36)。
三、北宋末南宋初:亡国影象与历史反思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序中悲叹:“呜呼!
靖康之祸,古未有也。戎狄为中国患久矣!
……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也。”靖康元年(1126),金军两度南下,于十一月攻陷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北上,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戏剧性的惨烈亡国,极大地刺激了士人的历史意识,关于汴京围城、北宋亡国、二帝被掳的过程,亲历者的记述数量可不雅观。徐梦莘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之记录者,无虑数百家。”(37)王明清说:“靖康之变,士大夫记录,排日编缀者多矣!
”(38)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古未有也”。这些记述大都逐日记录,乃至准确到“时”,细节丰富,令人身临其境。这些记录者正在经历和见证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和视角留下了一份亡国大难的实录,他们要把自己身受的巨大苦难、耻辱和仇恨通报给后人,这些记述成为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痛楚影象(39)。
高宗期间,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激烈,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条记极能引发人们的历史情绪,引发人们对秦桧及其求和政策的痛恨和贬斥,有的还揭破秦桧亡国后失落节的历史污点,这尤其为秦桧以及当权者所切齿。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秦桧“乞禁野史”,尤其针对“靖康以来私记”,绍兴二十年(1150)他又制造了针对前参知政事李光的“《小史》案”。但在南宋仍不断有人汇编刊刻上述条记,对亡国的惨痛历史影象加以强化、重申,这对南宋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情绪的引发和动员,“靖康之难”、“靖康之耻”可以说成了郁积于南宋民气中的一个情结。汪藻是高宗朝名臣,也是著名的史家、墨客,他曾汇编靖康时的六种见闻录、日记,包括《金人背盟录》、《围城杂记》、《避戎夜话》、《金国行程》、《南归录》、《朝野佥言》(40)。孝宗隆兴二年(1164),市价隆兴北伐第二年,确庵编《同愤录》,收录《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等五书。度宗咸淳三年(1267),南宋即将亡于蒙古,耐庵编《靖康稗史》,以原《同愤录》五书为下秩,又补录《甕中人语》和《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为上秩(41)。
高宗一朝,宋金和战是历史的主题。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制定条约,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大举攻宋,兵败被杀,世宗登基;次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自此,宋金两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和平,高宗朝一样平常被称为“复兴”期间。关于这一期间的主要历史事宜,皆有当事人及时记录,撰写条记,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广征博引此类条记著述,因而具有很高的史学代价(42)。
在亡国惨祸的刺激下,南宋朝野沉痛反思历史,深究亡国之祸的根源。高宗期间,朝野基本达成一种共识,将北宋亡国的根源深究至王安石变法,彻底为元祐旧党翻案,也全面否定了哲宗、徽宗的绍述之政。各类情势,不但促进了私修本朝史的繁盛,干系的历史条记也层出不穷。绍兴年间对野史私记的查禁,并无法压制当时士人社会飞腾的历史意识以及借史议政的激情亲切,尤其是那些亲自经历北宋亡国的士人,追忆前朝往事,撰写历史条记,多聚焦于与北宋国运密切干系的变法和党争,个中不乏深刻的见地,也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料。邵雍之子邵伯温在仍处于战乱之中的建炎、绍兴初年撰成《邵氏闻见录》,“于王安石新法始末以及一时同异之论,载之尤详。其论洛、蜀、朔党相攻,授小人以间,引程子之言,以为变法由于激成,皆平心之论”(43)。朱弁身经靖康之难,于建炎元年(1127)奉使金国,被扣十七载,于留金期间作《曲洧旧闻》,“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44)。两宋间著名理学家罗从彦撰《尊尧录》,以明靖康之祸,源自变法。方勺著《泊宅编》,记事最晚至绍兴十二年(1142),载元祐迄政和间朝野往事,他鞭笞新法新党的态度与当时“公论”同等,个中记述方腊事始末,最为世所重。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记事迄于绍兴年间。他亲历靖康之变,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尤为详确,对北宋末年弊政也多有记载。陈长方所著《步里客谈》篇幅虽小,但“所记多嘉祐以来名臣言行,而于熙宁、元丰之间邪正是非,尤三存问”(45)。北宋后期一贯行绍述之政,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长期以来是科举考试的标准,新学新政的影响不可能肃清于一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站在元祐旧党的态度上否定新法。如叶梦得著有《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岩下放言》、《玉涧杂书》,是南宋初历史条记的大家,他是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为蔡京门客,“不免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贡解绍圣”(46)。其人学术渊博,于朝章国典夙所究心,其《石林燕语》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并列为记载北宋典制掌故最主要的条记撰述。张邦基,平生不详,然家世显赫,其伯父张康国、张康伯皆徽宗朝名臣,所著《墨庄漫录》供应了有关北宋时政、党争的主要材料,他自称“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容心焉”(47)。
两宋间不少旧族世家子弟撰写条记追述前朝往事,抒发黍离之悲,寄托沧桑今昔之感。个中比较主要的,如王萃之子王铚的《默记》,曾公亮四世孙曾慥的《高斋漫录》,吴中复之孙、吴则礼之子吴坰的《五总志》,吴越王钱镠后裔钱世昭的《钱氏私志》,蔡京之子蔡絛的《铁围山丛谈》,等等。个中尤为主要的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在他笔下,故都盛景犹如梦境,对逝去繁华的追忆更映衬出身经亡国的怅恨。这类条记在南宋人的历史影象和情绪中有着分外的主要性,正如陆游为《岁时杂记》(吕原明著,已佚)作跋说:“太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尚,大家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余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则当如《梦华录》之韵”(48)。
四、南宋中后期:条记书写达至全盛
之以是说南宋中后期是宋代条记写作的全盛期,不但是从数量上看,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不仅名臣绅士撰写大量条记,而且地方人士、地方官、被放废的士人、未入仕的士人均纷纭撰写历史条记,其数量远超北宋。南宋以来,社会发展涌现了明显的地方化趋势,立足于地方的士绅家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理学之以是逐渐在士人社会中霸占主流地位,与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的发展大有关系。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不但表示于地方志的兴盛,也反响于中下层士人所撰历史条记的激增,而这些人所撰写的历史条记更多地反响了地方社会、民间社会的状况。如龚明之出身于苏州昆山的王谢,未能考中进士,他所撰《中吴纪闻》专门记述吴中(今苏州、昆山一带)地方官员和文人绅士的逸闻轶事、名胜古迹、民风习俗。明朝杨子器曾为之作序,颇为肯定这类条记之于朝政国史的主要代价:“若《纪闻》之类不雅观之,于国史之阙遗讹谬,于是乎补正;政治之得失落淳漓,于是乎征验;郡邑之废置沿革,于是乎考证;古今名迹、士夫出处、贤才经济、闺房贞秀,又皆于是乎总萃”(49)。廉布所撰《清尊录》多记载两宋期间的街巷轶闻,作为社会史材料有较高代价。庄绰在建炎年间做过知州,他学问广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撰《鸡肋编》内容驳杂,多反响当时社会风尚。张世南尝任闽中的地方官,所撰《游宦纪闻》多记闽中永福县事,而无一语及于时政,但四库馆臣夸奖其史料代价颇高,乃“宋末说部之佳本也”(50)。
这些人所撰写的条记,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便是内容上的丛杂,朝政、典制、轶事、辞吐、风尚、物产、考证、义理、诗话、文论,每每无所不有。正因如此,这类条记反响和记录了社会、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也为后世留存了更多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如,沈作喆于放废之后所撰《寓简》,曾为桐乡丞的李如篪所撰《东园丛说》,国子监免解进士费袞所撰《梁谿漫志》,未曾入仕的王楙所撰《野客丛书》,绍述余党之子孙陈善所撰《扪虱新语》,曾为丽水丞的宗室子弟赵与时所撰《宾退录》,辗转各地佐幕的宗室子弟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出身世家但终生未仕的周辉所撰《清波杂志》、《清波别志》,因不满史弥远当国而归乡不仕的韩淲所撰《涧泉日记》,因上书言事而开罪的张端义所撰《贵耳集》,官至抚州推官的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曾任义乌令而入元不仕的周密所撰《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等。这些居于士人社会之中下层的作者,非常看重自己的条记撰述,他们不但自己作序,还要请名人和当地官员作序,对撰述之旨、平生志业进行充分的表述,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也是历史任务感,无疑大大提升了这一类条记的精神品质和历史代价。
从种类上说,这一期间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专门条记,当时发生的历史事宜、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的个人经历,皆有条记进行记录,深刻反响了南宋期间的历史特点。在重视“文治”的宋朝,翰林院及其干系制度是极其主要的,翰林之职既是进入中枢的捷径,同时也是士大夫的极大声誉。这一期间关于翰苑制度和掌故的条记成为系列,如程俱《麟台故事》、洪遵《翰苑遗事》、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此外洪遵还编著了《翰苑群书》,收录唐宋干系著述十一种。这一期间还涌现了有关典制掌故的集成式条记,最主要确当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均一代记载之林”。
在南宋,理学一开始并不是官学,紧张靠盛行于士人社会而渐成大势,在野士人撰写的干系条记构成了理学史的主要材料。如施德操,学宗二程,与张九成、杨子平合称“三师长西席”。他所撰《北窗炙輠录》紧张记载了二程再传弟子的言行业绩,全祖望修《宋元学案》多从中取材(51)。理学的兴盛引起当时权臣的猜忌压制,秦桧当权就排挤理学人士,宁宗韩侂胄当政期间又有“庆元党禁”,遂涌现了署名“樵州樵叟”的《庆元党禁》、“湘山樵夫”的《绍兴正论》、楼昉的《绍兴正论小传》、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记录道学党禁始末甚详。宋代士人撰写条记以补国史之阙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佛教界,佛教人士也以条记的形式记录空门见闻、禅宗公案、与士大夫往来,为撰写佛教史供应史料,如释晓莹所撰《罗湖野录》、《云卧纪谈》。
北宋已有不少旅行日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在南宋写旅行日记形成一种风气,多出名家之手,如范成大的《骖鸾录》、《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周必大的《乾道庚寅奏事录》,记述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名胜古迹,历史和文学代价都很高。这一类行记、游记的大量涌现,与南宋士人的地域意识、“中国”意识是大有关系的。北宋时,出使契丹的青鸟使都要写行程录上呈朝廷,个中虽不乏主要史料,但作为例行公函一样平常不收入文集。到了南宋,则涌现了很多作为私人条记的出使行记,打破了官样文章的限定,容纳了更多、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个人思想。如洪皓的《松漠纪闻》、范成大的《揽辔录》、楼钥的《北行日录》、周辉的《北辕录》、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赵珙的《蒙鞑备录》。
南宋与金划淮为界,只有半壁江山,遂致力于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开拓,任官于这些地区的士人撰写了不少记述当地人文风尚、地理、民族、物产、交通等各方面状况的条记,反响了当时士人社会对这些地区和民族的重视和认知,也反响了南宋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有效统治的历史进程,如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录》、田渭的《辰州风土记》、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朱辅的《溪蛮丛笑》。此外,赵汝适的《诸蕃志》根据见闻记载了与南宋通商的“海国之事”,其代价不言而喻。
南宋中后期涌现了不少接续《东京梦华录》的都邑条记。南宋虽然武力不竞,但其经济生产、商业贸易、学术和科技的发展却远超金朝,在当时天下居于领先地位。经济和商业的发达,为都邑文化的繁盛、平民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是南宋历史的一大亮点,在这些以记述杭州及其生活为主的条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响。如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繁胜录》、周密的《武林往事》,和《东京梦华录》一样,这些条记在尽述繁华的同时,深深渗透着黍离麦秀的历史兴亡感。
这一期间的历史大事,也多有亲历者以条记加以记述。如开禧北伐期间,四川吴曦于开禧三年(1207)正月向金朝正式屈膝降服佩服,宣告受封于金朝为蜀王。仲春末,以李好义、杨巨源为首的军民策动叛逆,杀去世吴曦,平定叛乱,但功劳却被吴曦的心腹安丙窃夺,甚至李好义被鸩杀。关于这次事宜,很多亲历者撰写条记为杨巨源、李好义鸣冤。李心传尽采时人著述编成《西陲泰定录》九十卷,可惜佚失落,但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中罗列了二十余种。
南宋中后期涌现了宋代最主要的历史条记作家,他们把历史条记的撰写真正提升到“史学”的层次,成了当代史撰述的一种形式。首先该当提到确当然是李心传,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表里,被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52)。他还撰著《旧闻证误》,对宋人所作私史、小说四十余种进行考辨、驳正。其次,当属王明清,他出身于著名世家,其祖王萃学于欧阳修,其父王铚是曾布的孙半子,于建炎初任枢密院编修官,曾撰述《七朝国史》,因绍兴史禁而被焚毁,仅有《默记》传世。王明清生平紧张致力于史学,他“怆念父祖以来平生存心”(53),纂集闻见、访求父祖师友,撰成《挥麈录》,紧张记述北宋以及两宋之间的人物、事宜和典制。之后,他又陆续写成《挥麈后录》、《挥麈第三录》、《玉照新志》、《挥麈录余话》,皆记述两宋史事。王明清的《挥麈录》及其续编并非仅杂记见闻,而是通过广泛访求搜集史料,其间搜集、考据、归纳之功甚深,堪称研究,而绝非史料的大略汇编。他自言:“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书。”(54)《挥麈录》及其续编的史学代价在当时就得到很高的评价。宁宗庆元初,就在《挥麈第三录》成书不久,实录院即敕令抄录其书,作为纂修《高宗实录》的基本史料。其余,叶绍翁及其《四朝闻见录》也堪称条记体的本朝史撰述。叶绍翁平生不详,只知崇奉理学,与真德秀、危稹都有交往,在宁宗嘉定年间同为朝官。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详确赅备,但仅止于高宗一朝,叶绍翁则扩充二书的范围,对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朝政、典制、史事、人物加以记述,每条都有条款。后人评价说:“南渡往后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者,惟李心传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为精核,次则绍翁是书。”(55)岳飞之孙岳珂也是南宋主要的条记作家,所撰《桯史》按条款记载两宋史事、人物,“在宋人说部中,亦王明清之亚也”(56)。这一期间,考据、辨证兼记事的学术型条记也涌现了大家之作,最有名确当属洪迈的《容斋随笔》系列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它们标志着宋代考据学的最高水平,在宋代乃至全体中国学术史上都霸占主要地位。
结语:历史条记撰述的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历史条记的撰述得到了长足发展,已蔚为大不雅观,这使得学者们开始磋商和论述这一类条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在史学上的代价,这是对历史条记发展的理论总结,反响了历史条记在发展之中得到的自觉意识(57)。这一点,在条记的序跋中有充分的表示,也属于两宋历史条记撰述的主要成果。
两宋间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的跋语中,将唐以来“小说家流”分为两大类,个中有一类,“怪诞茫昧,肆为诡诞,如《玄怪录》、《河东记》、《会昌解颐录》、《纂异》之类,盖才士寓言以逞词,皆亡是公、乌有师长西席之比,无足取焉”。而“小说家”的主流是供“后史官采摭者”,他列举了“晚世诸公所记,可不雅观而传者”三十六种,都是北宋著名的历史条记。这是明确地把“小说家”中虚构性的志怪传奇和纪实性的历史条记区分开来,从而使历史条记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撰述门类。他还指出,这一类“小说家”有一个值得把稳的问题,便是“著述者于褒贬去取,或有未公,皆出于好恶之不同耳”(58)。但对付我们来说,条记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个中强烈的感情性、倾向性、主不雅观性同样也是主要的历史信息。
杨万里在给曾敏行《独醒杂志》所作的序中指出,历史的影象和传承有两种形式和路子:一种是“言”,“未必垂之策书,口传焉而已矣”;一种则是“策书”。书可焚禁,但却不能封住人们的口耳,但口传之言毕竟须要以书册的形式才能传之久远,以是说“书与言其交相存欤!
”条记这一类撰述形式便是要将口传之言书写下来,以书存言,如曾敏行所记“皆晚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这一类撰述,记载的内容广泛、丛杂乃至微不足道,但却可以寄托、寓含主要的思想:“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爱好笑,可骇可悲,咸在焉”(59)。赵师侠为《东京梦华录》作跋,他把“史册”和“传记小说”对立并举,以为缺一不可:“礼乐刑政,史册俱在,不有传记小说,则一时风尚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焉”(60)。如果说,“史册”是政治史,那么,“传记小说”就有些社会史、文化史的意味了。
给周辉《清波杂志》作跋的徐似道认识到,条记撰述供应了多种历史记录和证据,使得后世研史者有了更多的凭据,可以相互参照,以得其真:“大抵记载事实之书,各随所见,收书者不厌其博也。异日谈论一事,适然针芥相投,车辙相合,方知此书之效”(61)。对付这一点,周密在《齐东野语》的自序中论述得更加详细。他“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某事与国史之论异”,其父拿出“其曾祖及祖手泽十大帙”以及“其外祖日录及诸老杂书”,参照之后,给出解答,并见告他:“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定哀多微词,有所避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议论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62)。这就准确指出了“国史”和“私记”作为史料存在的毛病,以及诸家条记撰述在史学上的主要代价。
这些理论性的论述,对促进历史条记的发展、对历史条记之撰述传统的形成,都有很大的浸染。中唐兴起两宋形成的这一历史条记的撰述传统,在“正史”、“国史”之外,展现了一个更有社会性、抗争性、多元性的历史书写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而这一撰述传统也是两宋相比拟较自由、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注释:
①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361页。
②李肇:《唐国史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③刘叶秋将条记分为三大类,即小说故事类条记,历史鳞爪类条记和考据、辨证类条记。拜会刘叶秋《历代条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佚名编:《五朝小说》第一册卷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⑤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弁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序,河北公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8页。
⑦谢国桢:《明清野史条记概述》,载《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⑧勒高夫:《历史与影象》,方仁杰、倪复活译,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⑨关于宋代条记的研究,拜会宫云维《20世纪以来宋人条记研究述论》,《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郑继猛《近年来宋代条记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宋馥喷鼻香《两宋历史条记的编纂特点》(《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丁海燕《宋人史料条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条记的评价谈起》(《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郭凌云《历史鳞爪条记题材在北宋的变迁》(《河南教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都研究和论述了宋代以来历史条记的迅速发展及其特点。张晖《宋代条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傅林辉、吴凤雏《宋代条记概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宋代条记,但也都指出并论述了宋代条记的纪实特性和代价。
⑩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太宗收用旧臣处之编修以役其心”条,载《全宋条记》第六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11)郑文宝:《南唐近事》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12)孙光宪:《北梦琐言》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4页。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史部》“载记类”,第1790页。
(14)黄休复:《茅亭客话》石京后序,载《全宋条记》第二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15)马永卿:《
(16)佚名:《钓矶立谈》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四册,第215页。
(17)钱世昭:《钱氏私志》,载《全宋条记》第二编第七册,第65~66页。
(18)苏辙:《龙川别志》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九册,第313页。
(19)欧阳修:《归田录》自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五册,第236页。
(20)范镇:《东斋记事》自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六册,第194页。
(21)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六册,第253页。
(22)王得臣:《麈史》自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十册,第5页。
(23)文莹:《玉壶清话》序,载《全宋条记》第一编第六册,第86页。
(2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满中行题语,载《全宋条记》第二编第四册,第6页。
(25)拜会郭凌云《北宋党争影响下的历史鳞爪条记创作》,《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总叙》,第1228页。
(27)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元祐诸公日记”条,载《全宋条记》第五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28)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载《全宋条记》第六编第二册,第126页。
(29)司马光:《温公日录》,载《宋代日记丛编》第一册,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30)王安石:《熙宁日录》,载《宋代日记丛编》第一册,第94页。
(3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子部》“小说家类一”,第3587页。
(3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597页。
(3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子部》“杂家类四”,第3110页。
(34)魏泰:《东轩笔录》序,载《全宋条记》第二编第八册,第4页。
(3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602页。
(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594页。
(3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38)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载《全宋条记》第六编第一册,第137页。
(39)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对这类条记包罗备尽,亦可拜会燕永成《有关北宋亡国的私家紧张著述一览表》,载《南宋史学研究》,甘肃公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40)拜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41)崔文印:《靖康稗史笺证》序言,载耐庵、确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崔文印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42)拜会燕永成《有关南宋初建的私家紧张著述一览表》,载《南宋史学研究》,第29~30页。
(4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606页。
(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子部》“杂家类五”,第3114页。
(4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609页。
(4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子部》“杂家类五”,第3118页。
(47)张邦基:《墨庄漫录》自序,载《全宋条记》第三编第九册,第5页。
(4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子部》“杂家类四”,第3111页。
(49)龚明之:《中吴纪闻》杨子器序,载《全宋条记》第三编第七册,第165页。
(5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子部》“杂家类五”,第3129页。
(51)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全祖望跋,载《全宋条记》第三编第八册,第218页。
(5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七《经籍考二十四》“史部传记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92页。
(53)王明清:《挥麈录》自跋,载《全宋条记》第六编第一册,第54页。
(54)王明清:《挥麈后录》自跋、《挥麈第三录》自跋,载《全宋条记》第六编第一册,第234、282页。
(5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613页。
(5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3610页。
(57)拜会瞿林东《宋人条记的史学意识》,《文史知识》2014年第10期;郭凌云《北宋历史鳞爪条记不雅观念简论》,《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58)张邦基:《墨庄漫录》自跋,载《全宋条记》第三编第九册,第138页。
(59)曾敏行:《独醒杂志》杨万里序,载《全宋条记》第四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18页。
(6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赵师侠跋,载《全宋条记》第五编第一册,第190页。
(61)周辉:《清波杂志》徐似道原跋,载《全宋条记》第五编第九册,第135页。
(62)周密:《齐东野语》自序,载《宋元条记小说大不雅观》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431页。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