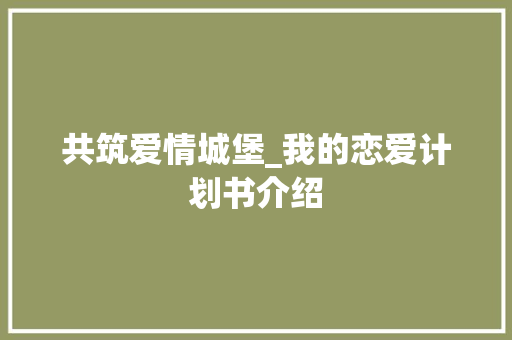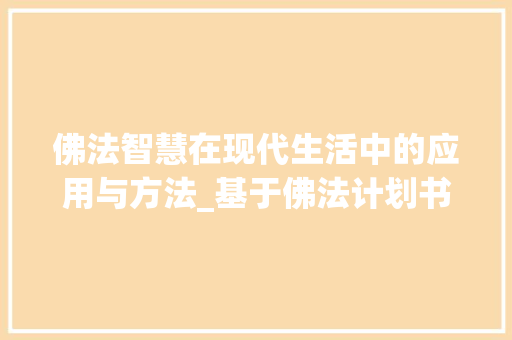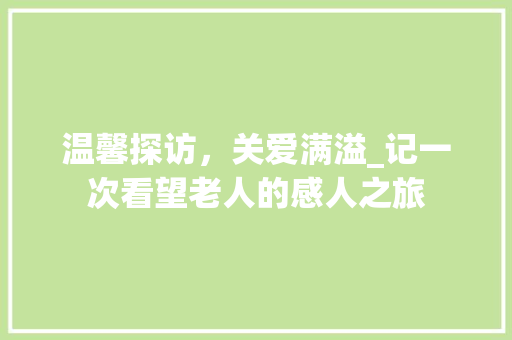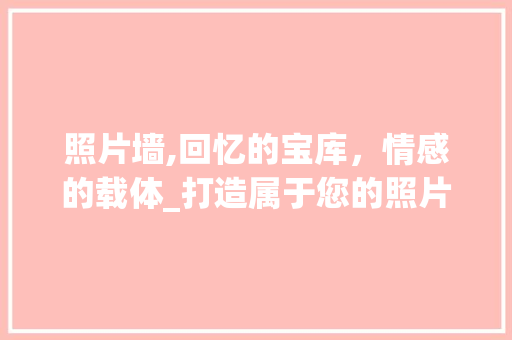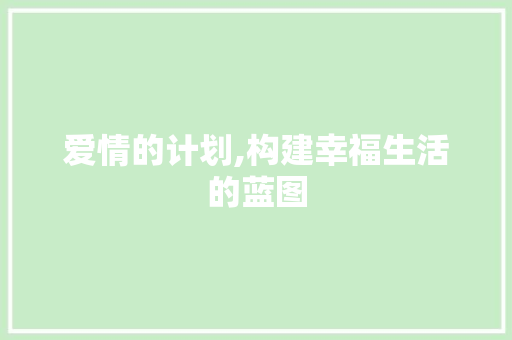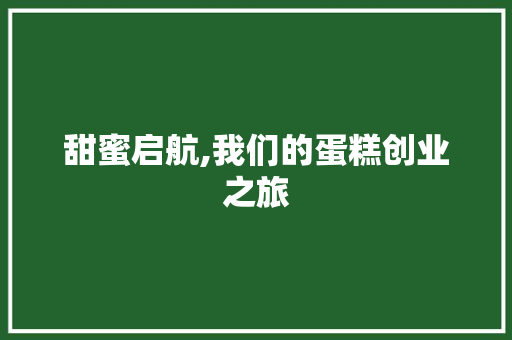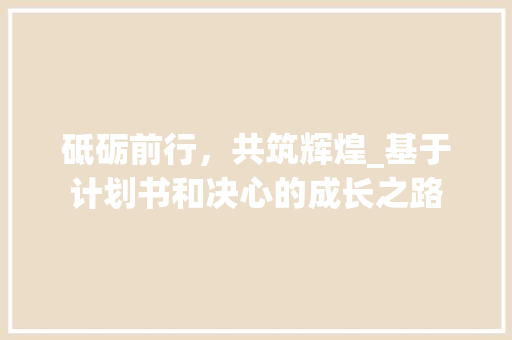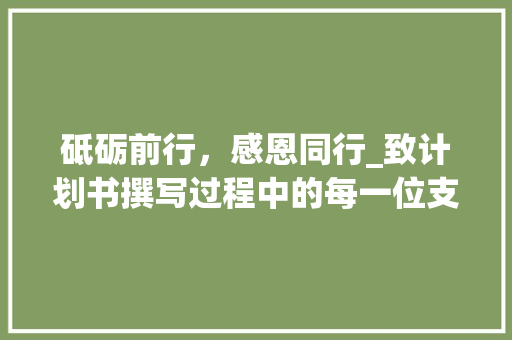作者:沈玉印
这几天景象极好,空气纯净,天蓝云白,阳光残酷。此时,已是中秋,虽然路旁的梧桐树叶依旧泛着绿,但却在叶的裙边已经逐渐地染上了一丝黄色,就象画家手里的彩笔,每落下一笔,秋就逐渐地入了人的眼帘。而在这样纯净而美好的时令里,也总是能忆起一些美好的人生片断来,让自己回味,也让自己的生活在金色的秋日里也充满着无限的冲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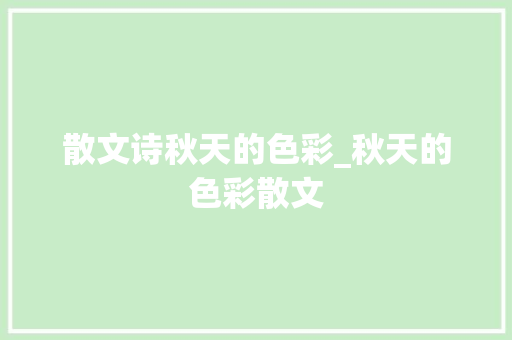
或许到我这个年纪,可能很多人都喜好回顾过去的一些生活片断,由于曾经会有很多让自己觉得美的东西会时时的呯击人的精神情绪。我自然也难以脱俗,由于有时一个闪念,还真是能觉得到曾经被自己忽略的东西,现在回忆起来,竟然还是一个很美的场景。
我的高中是在溧阳的上兴中学读完的,对屯子的孩子来说,当时最大的欲望便是能考上一所大学,哪怕是能考上一个中专,也是一个莫大的幸福,由于那时的城乡差别还是极大,若能考上中专不但户口可以转成城镇户口,而且毕业后还都有国家分配事情。但遗憾的是,那一年我所在的那个中学竟然没有一个学子如愿,也就在那一年的秋日,我去了另一所中学去复读。
我是在溧阳的竹箦中学复读的,中学离我所在的村落庄有十公里的样子,那时同村落还有一个女孩,比我大一岁,记得那年,我是十八岁,她该当是十九岁吧。女孩属于那种微胖的形态,戴着一付金丝眼镜,皮肤非常的白净,喜好扎一根又黑又亮的辫子清闲地搭在肩后。女孩喜好穿白色的小翻领衬衫,表面再穿着一件军绿色的秋衣,显得大方而白净。由于间隔远,那时我们都住校,但是每到周末,我们都要回家,一是取点米,菜之类,另一个,过了一周也要回家看看,也好让家人放心一些。
女孩那时在文科班,我在理科班,每到周末,她临走时都要去宿舍喊我,然后我们就结随同行。那时,我们回家常日都是步辇儿,极少坐车,由于若坐汽车的话,不仅中途要换车,还须要绕很大的一个弯子,以是我们都是尽可能的步辇儿回家,那样不仅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可以挑最近的直线走。
步辇儿回家,大约须要二个小时旁边,现在想来,那二个小时实在也是极美的。周末放学依旧会早一点,那时太阳还高高地悬挂在西边的天上,也从那一刻起,夕阳就开始随着我们的步伐逐步地西沉,从最初的发着刺目耀眼的光芒再逐步地变成橘赤色,再逐步地隐入西边小山村落后,而在西边的天上留下一片残酷的云彩。那时我们险些不带书包,但手上会拎二个空的铝饭盒,用一个丝网袋装着,其余我们还都会带着一根短小的毛竹扁担,透着淡淡的绿色,而那网袋有时会被我们挂在各自的扁担上,有时她会叫我把饭盒给她,她把饭盒放在一根扁担上,就那样挑着。而若那样我则喜好握着我的扁担,若刀若枪般在我手里一直地转换着角色。女孩话不多,有时默默地跟在我的后面,有时也跟我说一些她们班里的事,而回家走哪条路,她则完备地听我的,由于为了寻求一种新鲜感,我们时常也会走一些大方向不变但却是不同的路。那时已是秋季,正和现在的时令差不多,放眼一望野外里的空气好象都显得特殊的透明而纯净。从中学出来,我们要经由很多的村落落和野外,还有一片茶园。茶园建在一片山坡地上,一行行的茶树,正泛着绿,象在山坡上流淌着绿色河流,在秋阳里离我们逐步远去。而野外里稻穗已经开始发黄,就连稻子的叶子,在金色的秋阳下,也显得逐渐地金黄起来。稻田是成片相连的,一片一片的,一贯延伸到一个小村落的边缘,而每一个陌生的小村落,则又是一种色彩,小村落依旧笼罩在绿色的树丛中,从远处看,那些绿色依旧是那么的富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让稻子的金黄和小村落的绿色形成光鲜的色彩比拟。脚下的小道边上,也会有一些淡紫色的马兰花,象一元硬币大小,悄悄地开在田埂边的野草里。野外里很静,有时连个人都不见,只有我们二人的话在微风中逐步地飘散开来。
那时回家的路上,上腰村落是必经之路,然后我们会超越104国道,穿过几个不有名的小村落。印象中,在不到堰下村落的路上,还有一个水库,我们要从坝顶上途经,路上还有一个水泥浇铸的水闸,水闸的缝隙处,上游的水涌了出来,在闸边上形成一条小溪潺潺地流向一条水渠。过了水库,就会到曾经的堰下村落,那村落由于1979溧阳上兴那场六级地震,堰下村落的房屋大部被毁,全体村落就全迁了,留下了一片村落的旧址。竹林、大树、茅草、旧屋、断壁,在斜阳下,竟然还有一份很苍凉的美。但村落前还留着一个小青石桥,桥墩是用乱的麻石垒成,而桥面则是二条约一米宽的青石担在二边。桥下是一条小溪,溪水不大,但水很清很透。
过了堰下村落,我们有时会从陶村落走,有时会从七木桥的山岗上走,有时也会沿着稻田的小路一贯向西。记得有天我走的热了,便脱下了脚上的鞋子拎在手里,赤着脚走在乡野的泥地上,那天女孩还笑我变成了“赤脚大仙”。不过,不管走哪条路,女孩好象都没有反对过,她只是跟在我的后面,隔着三五步的间隔。一起上小村落很多,狗大概多,一旦碰到这种情形,我手里的扁担就会真正地发挥了浸染,我会掩护女孩快速地通过是非地,而我则会舞着扁担朝狗佯冲去,然后再快速撤退,有时兴致来了见居家没人,就捡起村落边的石头把狗砸的落荒而逃。
女孩戴着眼镜,看上去弱弱的很文静的样子,有次我好奇,把她的眼镜要过来试戴了一下,结果我竟若一个醉汉般迈不了几步路,还是赶紧把眼镜还给了她。还有一次女孩放学后去宿舍找我,我恰好不在,同学说我可能走了。她以为我没有等她先走了,就只能失落落地去坐汽车,我后来赶到车站时,车刚要起动,见到我她便急急地冲了下来,还一脸的委曲和紧张。
从学校到村落口时,已近薄暮,二个小时,好象觉得并不漫长。但本日想来,这统统竟然已是近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不免让人唏虚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