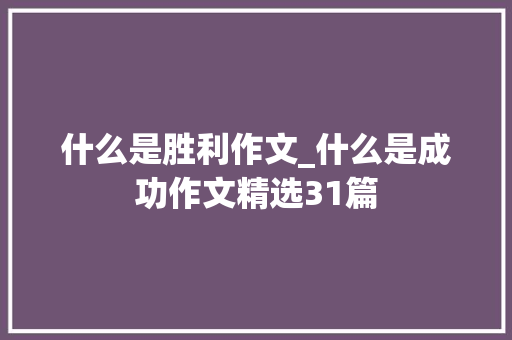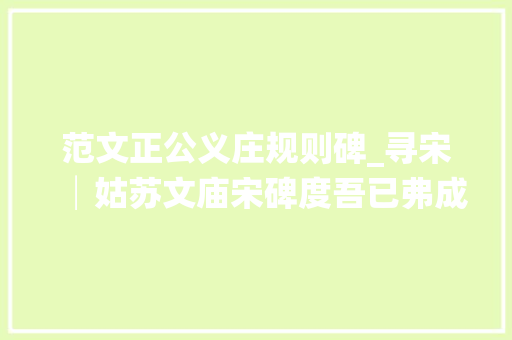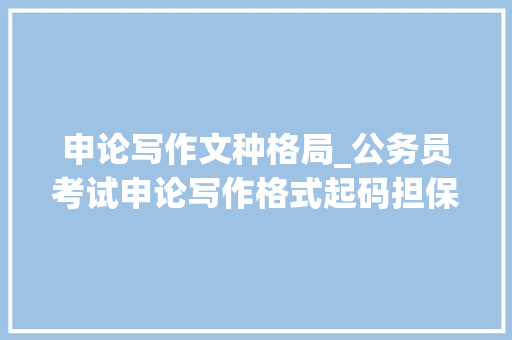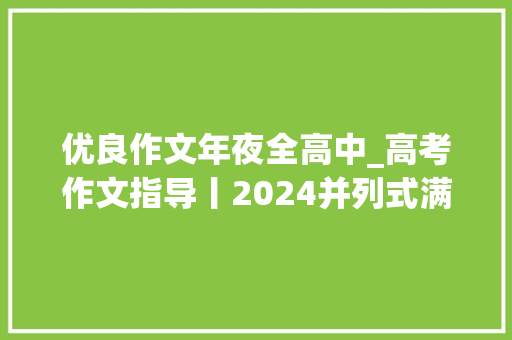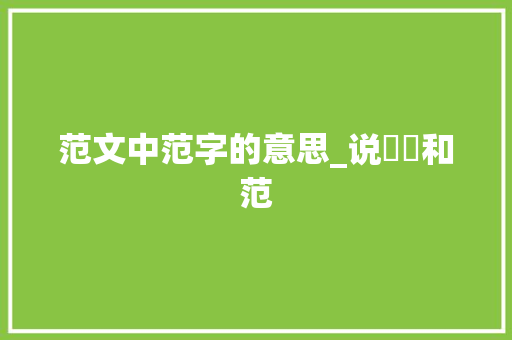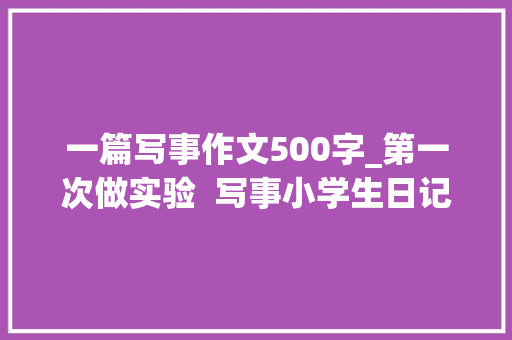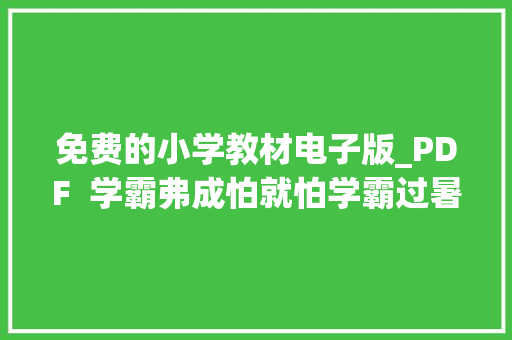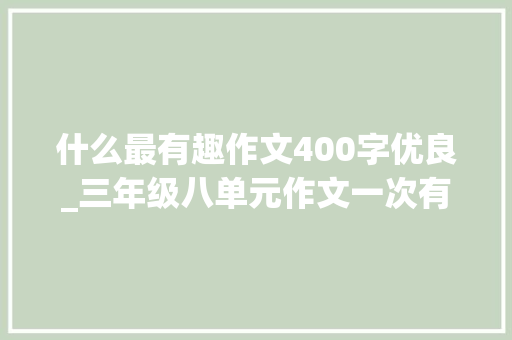11月23日,95岁的杨宪益病故于北京;此前的7月31日,86岁的大卫·霍克思(DavidHawkes)在牛津去世。短短5个月内,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红楼梦》英译者先后亡故。
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GladysMargaretTaylor)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致巨大声誉。后人或会猜测杨家与霍教授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当年必如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高手对决,非要分出个雄雌。然而这并非事实:杨霍分居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又因冷战隔绝,故而各译各的,对对方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竞争的压力或发奋的动力。相反,霍克思与杨宪益英雄相惜,两家人日后亦结下厚谊。杨宪益先生晚年在海外出版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Tiger),即是由霍克思的女婿、接续译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汉学家闵福德(JohnMinford)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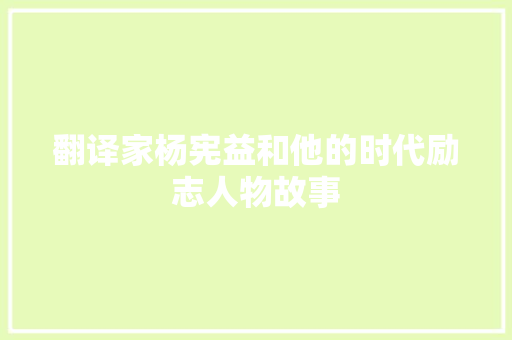
两本《红楼梦》译本,两种情境
但杨译与霍译并非不可对照甚至对比。事实上,30年来,述及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事关翻译技巧,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亦多有论及。
有人说杨宪益采直译,霍克思取意译。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当然都是直译,只是意趣不同。概括地讲,杨译简练,但略显苍白,文采不足。霍译虽饱满、耐读,却也有落口罗嗦与过度之嫌,有时甚至自由发挥、添枝加叶。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张南峰在所著《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举《红楼梦》焦大发酒疯一段,将两译对照,指出,杨译过于整齐,有些字眼太“严肃”,“令焦大显得像正气凛然的英雄,而不大像口吐狂言的酒鬼”,霍译有些段落虽“在字面上离原文较远,但这种俚俗的语言和人物性格相当配合”。霍甚至煞费苦心,将中式度量单位转换成英制,为此不惜调整数字,亦别出心裁,在字体和字号上多变花样。
张南峰大概不知,按当时的标准解读,焦大是劳动人民,属正面人物,发酒疯也是批判腐朽没落阶级,自然该正气凛凛。
张引原著例句:“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曹雪芹没有写明焦大被拖走时脸朝上还是朝下,霍克思却在此处加了半句:“andthrowinghimfacedownwardontheground”(脸朝下掀翻在地)。张南峰认为:“这个姿势会令焦大痛苦不堪,却令看热闹的读者乐不可支。”
不过,一触及书中的性事或亵语,杨宪益便不那么忠于原文,不仅能省则省,能略即略,甚至多有洁净,至原著粗俗难耐处,宁可多落个一句半句也不可惜。霍克思则全不避讳,予以充分还原,在处理薛蟠的著名春诗时,还额外给句中的性器加了一个“big”。
关于杨霍两译所呈现的两种面貌,张南峰解释说,实因两国翻译理念不同所致。英国讲究可接受性,而中国的翻译规范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倾向于充分性;另一层原因,则因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更何况这部作品是最高领导人评价很高的”。1980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座谈会上,戴乃迭说,她觉得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像力,而他们钦佩的霍克思则有丰富得多的创造性。
霍克思个人喜好译书,他本人也以向读者传达阅读乐趣为己任,因而更重译文之可读性。而杨宪益夫妇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从事翻译。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出版其译本的外文出版社也是非常官方的,然而该社的产品其实很难进入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其翻译出版工作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是由来源系统发起的,主要是给来源文化中的读者看的。所以,译文没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却很有必要遵守来源系统的各种规范。”张分析说。
然而说到底,杨宪益从不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比起霍克思来,生活中的他更喜笑谑,由于嗜酒,朋友们赠以别号“酒仙”。1968年4月他因“帝国主义特务”罪名被捕时,还与戴乃迭整晚在家中喝酒,太太喝过就睡了,杨先生继续,孰料喝到一半就被带走。入监时,同号的犯人闻见他身上的酒气,以为这老头子喝多了在外面闹事,才被抓来。坐了四年大牢,经历了无数次提审和信以为真的假枪毙,杨宪益终于被释放回家,4年前喝剩下的半瓶泸州大曲还在桌上,却早已发黄而不能续饮。
特殊时代下的翻译人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1936年入读牛津大学,1940年携英国女友戴乃迭回国,在贵阳、成都等地短暂任教后,入国立编译馆,受主事的梁实秋委派,着手英译《资治通鉴》,从此以汉语经典英译为终身事业。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润色校改,夫妇合作无间,获得举世称许。“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闵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写道,“若无他俩及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
解放后,杨戴夫妇来到北京,任职外文局,疯狂投入工作,译出《儒林外史》、四卷本《鲁迅选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等众多汉语文学名著。大跃进时,两人主动响应,废寝忘食,力争工作量翻番,只用10天就译完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杨宪益阔少爷出身,性格中颇多闲散,然而工作中不能自主的地方实在太多,审查无处不在,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并一度自称“受雇的翻译匠”。而且夫妇两人的大量时间,都用于翻译无数的最高指示和领导讲话。杨宪益当年遭批判的一条罪状是:中文里明明有六个“毛主席”,译文只出现两次,其他的都用“he”代替。戴乃迭亦曾奉命翻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愤怒之余,竟在译稿上批注: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对外宣传中非常愚蠢云云。此举事后亦成她一大罪状。
《白虎星照命》的英文颇明快,即便述及个人至痛至悲处,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或揶揄,或自嘲。讲到自己在外文局食堂被批斗,被迫站到3张桌子摞起来的最高层,颈挂大他一倍的木头黑板时,杨宪益还特意在行文中采用英制单位:“因为我离地十英尺,当时惟一的恐惧是他们会发飙,开始踹我,或在怒火中把我从高处推落。那我就要腿断臂折了。”
他写到自己在挨批时精神濒于崩溃,时刻觉得同事欲行加害,竟要戴乃迭写信给党的统战部派人来救他;他还觉得有坏人藏在出版社,操纵一台邪恶的发报机,不停向他一人发送信息。他还幻听,坐在家里,听见毛主席在隔壁屋里说话:杨宪益不是坏人。
看到这里,读者多半是要苦得落泪的。
杨宪益的翻译生涯大部分不能自主。事实上他并不喜欢《红楼梦》,尤其对书中无尽的宴饮感到厌烦。戴乃迭则始终无法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不带着林妹妹私奔,两人照例是奉命翻译。相反,霍克思全凭对此书满腔热爱,才全身心投入其中,并很快就把翻译《红楼梦》当成全职工作,为此辞去了牛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教席。他乐在其中,翻译过程中自绘大观园地图,标明各个人物住房的方位,以求直观理解原著。对书中人名、地名、餐具、食谱的中英转换,亦乐此不疲。如丫鬟名全采意译,戏子名法语化,僧尼和道士则统统译作拉丁语。而或许世风使然,或许本人忌红,霍克思不仅将书名由《红楼梦》改回《石头记》,亦改红为绿,将“怡红院”(HappyRedCourt)译作“翠喜堂”(HouseofGreenDelight)。
霍克思不为国家雇佣,翻译《红楼梦》亦非效命于外宣,在严谨的学术态度下,尽可以自由为之,并以此为乐。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若英语读者能从中得到他读此书时乐趣的百分之一,作为译者,他也便知足。
也许我们永远不该轻谈霍杨之译孰优孰劣。当我们多少了解了一些译者的命运时,就更不该妄加评判。
至少有一次,杨宪益是率性而译的。那是他24岁在牛津读书时,出于闲情(forfun),而以仿冒的英雄体(mock-heroic)译出了《离骚》。采用这种过时的诗体多少带些嘲弄的意味,因为他一直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几百年后汉代的淮南王刘安。许多年以后,霍克思看到杨宪益译的《离骚》,大为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