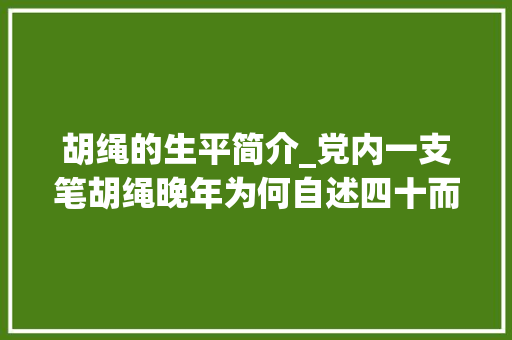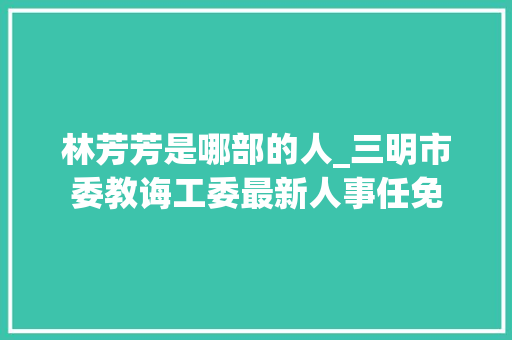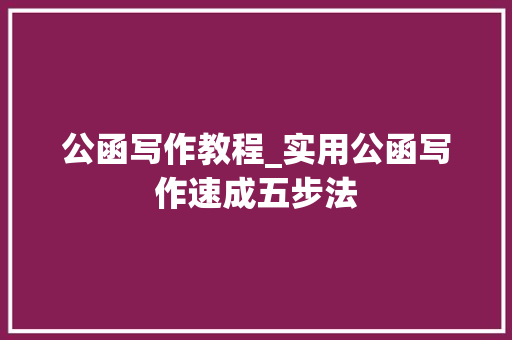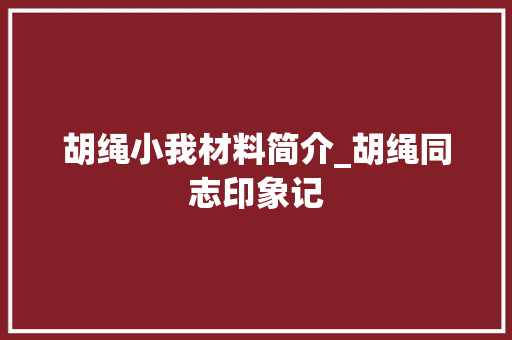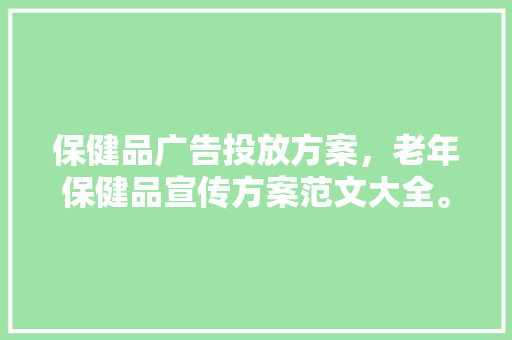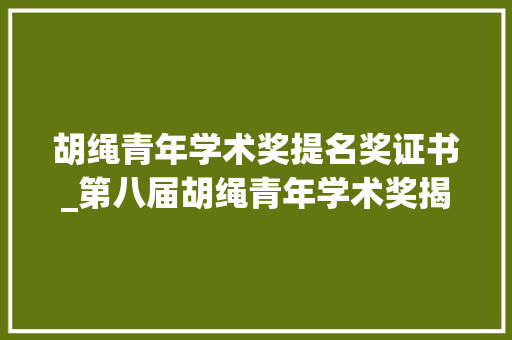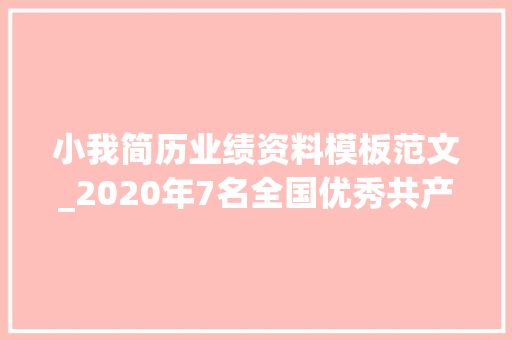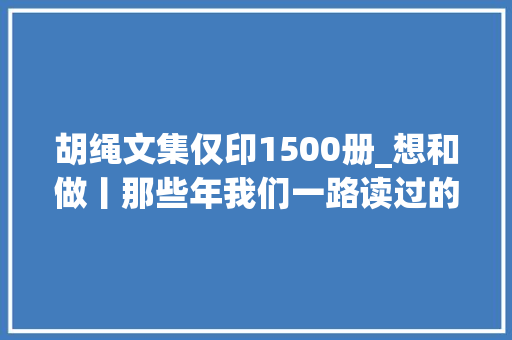范用(1923—2010年),公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本文写于2001年5月。
我十六七岁就读胡绳的著作《新哲学人生不雅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那时正醉心于追求新思想,学习新思想,迫在眉睫。这两本普通哲学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深入浅出,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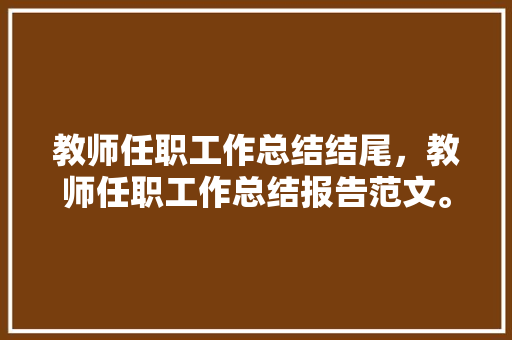
胡绳写这两本书时,不过十八岁二十岁,就足以担当青年导师了。
范用同道(摄于1993年)
初见胡绳同道,是1939年在重庆,他在学田湾生活书店事情,我在武库街读书生活出版社,难得见到。当时我刚入党,有一天陈楚云同道带我到七星岗某处听讲,到的人只有五六个,个中有赵冬垠,他也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在座的还有侯外庐,想来他也是党员。听谁讲,凯丰,那时他在八路军办事处。讲的内容便是后来揭橥于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季刊上的《论知识分子》,后来印成了书,在解放区脱销一时,在国统区则成为禁书。
我不知道这一次胡绳对我这个十几岁未脱稚气的孩子留下什么印象。往后,又见过几面,没有深谈,但他对我十分和蔼,民平易近。
胡绳同道
再次见面,是1946年在上海。我离开重庆时,组织关系在何其芳处,他见告我到上海后由胡绳同我联系,但是过了几个月都不见他来。有一天,我在四川路底乘一起电车,在车上见到胡绳,十分高兴,但胡绳立即以目暗示彼此不识,不能交谈。往后得到关照,关系转到冯乃超处,但也未接上。直到1948年方学武来,说关系又转到吴克坚处了,这才又过上组织生活。
解放往后,胡绳在出版总署任办公室主任,公民出版社重修,他兼任社长,我在他领导下了,但他并不管出版社的日常事情,由王子野、华应申主持。开会时他来做过几次报告。出版总署和公民出版社同在一处,常常碰到他。
上世纪60年代初,公民出版社出版他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枣下论丛》,打仗就多了。他住在史家胡同,与公民出版社及我住处很近,我也就常常去他家走动,请教出书和编辑事情中的问题,得益良多。他爱饮酒,常以茅台酒飨我。那时一瓶茅台八块钱,二锅头才几角钱一斤。他的爱人吴全衡同道在重庆时就认识,一贯把我看做小弟弟,还曾经动员我到生活书店去事情,我们叙起旧来,十分高兴。
后来他做的“官”越来越大,我不便轻易去打扰他了。当然,去找他是不会遭到谢绝的。
范用同道
1999年秋日,胡绳住院,王仿子约我去看他,他精神很好,谈兴甚浓,将近一个小时谈了许多往事。回来我见告老伴,我又见到当年的胡绳了。
我还带去1939年、1940年胡绳用“雍蒲足”笔名写的一组读书随笔《夜读散记》。胡绳看了在上面题字:“范用同道出示五十余年前从我主编的《读书月报》上一些小文章剪集在一起的本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居然尚存,实属不易。”
没有多久,胡绳寄来一笺《八十自述》。诗中说“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四十岁是1958年,三十载是到1989年,我们过来人都知道其间政治风浪是怎么翻滚的,当时,有谁能说得清楚?心惊肉跳过日子,哪里谈得上理解。不少人直到丧生都“惑而不解”。而在胡绳,困惑正是觉醒的开始。
胡绳同道在1996年写的《胡绳全书》第二卷弁言中有一段肺腑之言:
从1957年往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碰着过的抵牾。彷佛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以为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抵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辅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辅导思想。正由于我不理解它,以是陷入越深的抵牾。
这一段反思解释,晚年胡绳同道终于由惑而悟而明了,十分可喜,值得赞颂。
1998年12月,胡绳到长沙,参加一个“毛泽东、邓小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作了发言,随后将发言写成近两万字的专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揭橥,竟遭到某些人的求全谴责和攻击。这是胡绳同道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末了的贡献。我希望对这一问题有兴趣者都能一读此文(后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胡绳逝世后,吴江在其吊唁文章中对胡绳有如下的评价,我以为全面中肯,适可而止:
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亦将以近代史著作传于世。但他同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教化,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所知。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胡绳是长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色。
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期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期前面发言立论,而不知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期,在历次批驳运动中,胡绳属宽厚派、温和派,只管即便不说过分话,诚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所论常“未能尽意”,即持相称保留态度之意。这是颇难能名贵的。
但胡绳还有其另一方面,即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候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定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情形到了他的晚年特殊是末了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这有他逝世后一个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为证。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今胡绳同道对成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课题作进一步的磋商,又有新的成果,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因此,我们深深怀念胡绳同道这位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近读李普《悼胡绳》一文,他认为胡绳生平也有“从前实现自我,中年失落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与吴江所说是一个意思。
另一篇《忆胡绳》的文章叹曰:“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胡绳作为一个八十岁老人,不随意马虎啊!
我怀念胡绳,更景仰其为人。
【本文来源于公民出版社出版的《公民出版社往事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