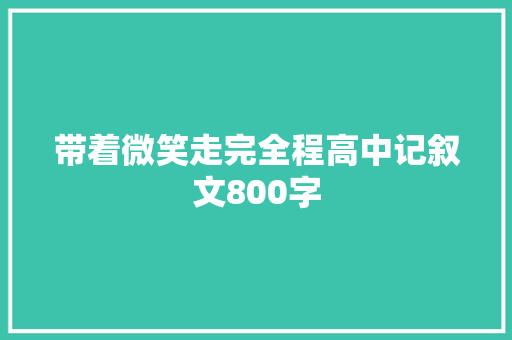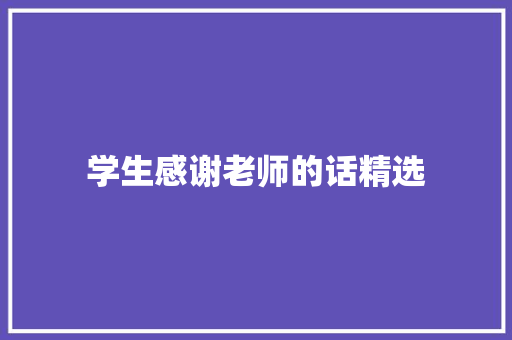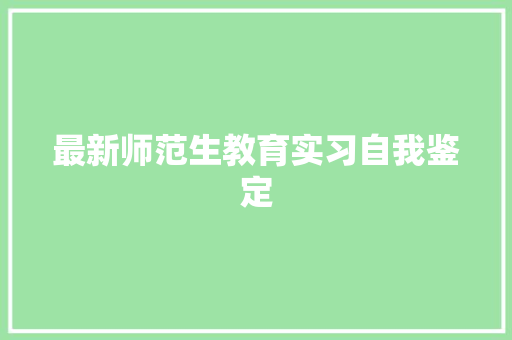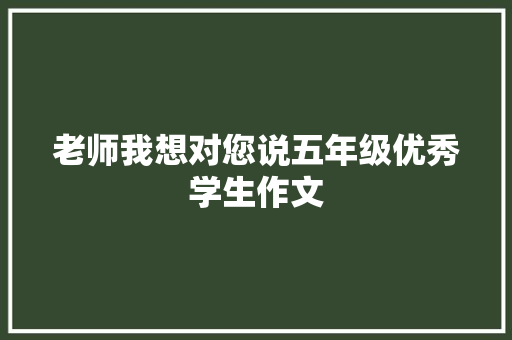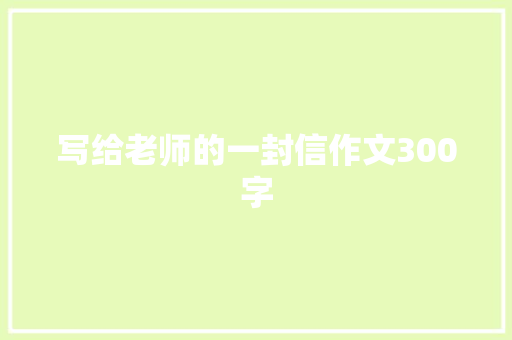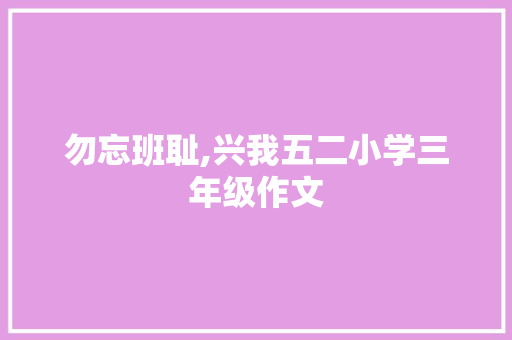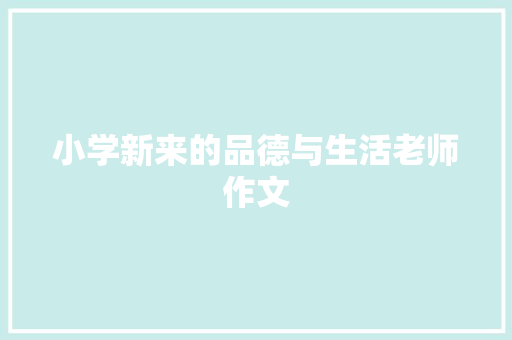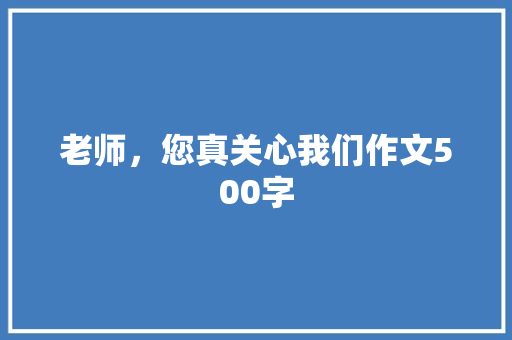我的家乡在西藏。1953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大门外传来“折嘎”的说唱声。刚穿上新衣的我,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白发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着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着木碗。“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相传古时候,在西藏碰着战役胜利,农牧丰收,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颂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每当藏历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户人家门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唱一番动听的赞颂话,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多是即兴创作、自由表达:共和国出身,解放西藏,汉藏联络……西藏刚得到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
通往那曲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四百公里路,是畜生踏出的小路和行人双脚踩出的土路。我白天骑马赶路,夜晚睡在路旁。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一起的烦躁寂寞,艰费力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思念、顾虑,百味杂陈咽进肚里。再从那曲镇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两千公里,全是灰尘翻滚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等十二座大山,要超过楚玛河、通天河、拉多河等二十五条江河。经由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历时二十五天,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三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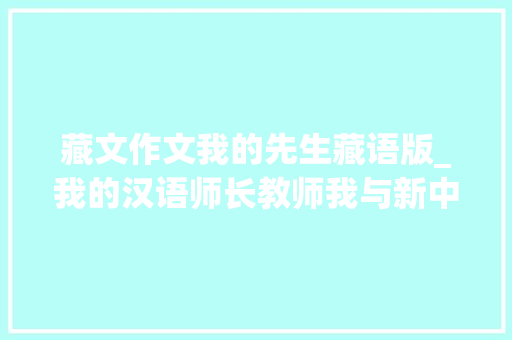
千亩校院,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用藏汉两种笔墨书写着校名“西藏公学”。我们在敲锣打鼓的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畅的水泥路探求宿舍。繁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洁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十来个平方米,摆着四张高下双层床,住着八个学生。五层高的传授教化楼,显得威武高大,墙壁是砖边石心,屋顶是灰色大瓦,楼脊上有透窿的瓦做装饰,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塑有一个鸽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解释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迢遥的西藏飞到咸阳俏丽的校园。上课第一天,在通亮的教室里,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先容汉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我数学很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心神专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第一印象,仪表堂堂,体格平均,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黄色衣裤明显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负责真,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更惊异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起辛劳了,这学校你们喜好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间隔,贴近了民族情绪,更让我产生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话是“老师,你好”及“你用饭了没有”;教的前三个汉字是“你、我、他”。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位好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平,以是一句“老师,你好”值得终生铭记。
咸阳这座安静的新城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学生。三千多逻辑学生,不论出身,学校等量齐观,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中学,学生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十三岁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党校,只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还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只管西席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小学教材。
教诲能改变人的命运。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六十年的进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培植培养了八万余名专业技能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豪杰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学习汉语特殊存心。汉语老师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字词,音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着两种措辞的发音办法。教汉语,没有教材只有提要,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边整理自己的传授教化条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我们在五年多的韶光里读完了初中以下的汉语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三千多个单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殊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当作文写作的课代表,老师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教室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先发的是写得不好的,末了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韶光宣读和讲评好的、差的作文。
教室前面墙上是黑板,只有老师拿粉笔书写。后面墙上是报栏,长方形的木框内贴满精良作文和好人好事表扬信,我的作文常常贴在最前面。我为了写好作文,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想读《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图书馆的老师说:“你才学了五年汉语,有点……”这些书当时被视为“闲书”。我于是跑到咸阳街头一个旧书出租屋费钱去租,有空就读,还常常在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动手电筒来读。有一天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俏丽的校院》,可以描写不同时令的风景,抒发对老师的情绪,还可以写同学之间的交情。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赞颂学校的长诗。我交完作业心里忐忑不定,总以为作文既离题,又离谱,不知老师怎么想。没想到产生发火文的时候,还是“压轴”,这就吃了定心丸。但这次老师没有念给我的批语,我翻开作文簿一看,红笔写的“诗写得很好,但把稳不能好高骛远”映入眼帘。对前一句话有点志得意满,后一句不便是批评我还不会走就想跑吗?
有一年学校组织全校汉语普通话比赛,在三千逻辑学生中我得了第三名,缘故原由是朗诵中卷舌发音不标准,老师有些失落望。不久又进行全校汉语作文大赛,我得到第二名。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门市部,取出一斤粮票,买了一斤糕点,把一半分给我吃。在六十年代初,那算是最大的褒奖。老师的一举一动鼓起了我的写作激情,就像鼓满船帆的风,勉励着我不断远航。
十多年前,我专程前去咸阳看望我的老师们,将我出版的散文集和专著送给他们,还见告他们,中篇小说《江贡》获奖,部分散文集翻译成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匈牙利文。老师们的恩情我常藏在心底,师恩是报答不尽的,只能作为内心的纪念。我最高兴的是老师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风姿如故,威严如故。
去年,我去咸阳看望我的汉语老师陈钦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陈老师见证西藏和平解放,存心培养藏族学生。他对我的无私付出改变了我的命运,就像新中国无数的教诲事情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样。
(作者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 公民日报 》( 2019年05月27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