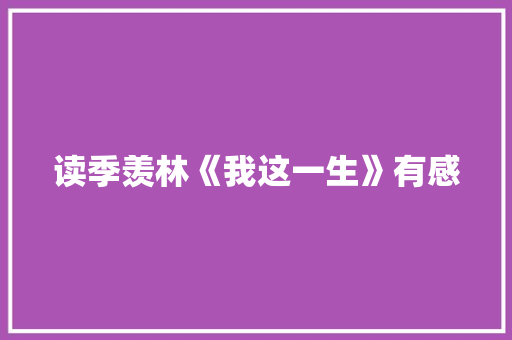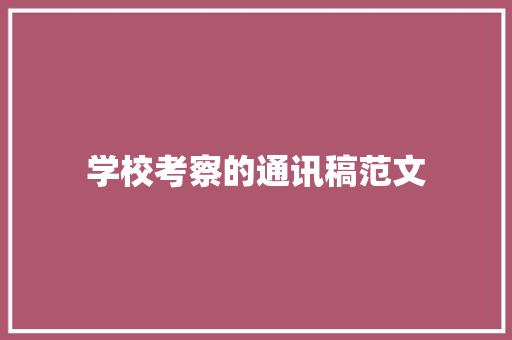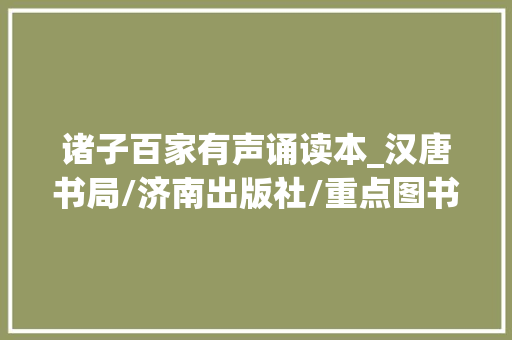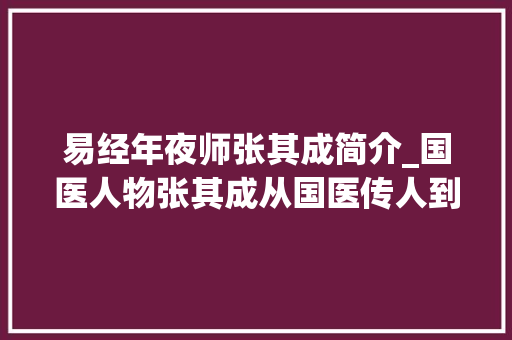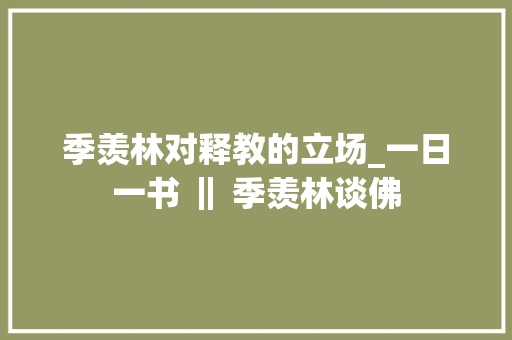“国学”究竟是什么?恐怕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国学可大可小,小到诗词歌赋,大到儒释道,凡是跟传统文化能扯上关系的学问,通通可以被纳入国学的范畴。以至于当今许多人调侃说,国学是一锅大杂烩,能放进来的食材,末了都可以被有心人烹饪成美味,至于有没有营养,亲自尝一下便知。
不可否认,国学是一套完全而丰硕的文化学术体系。生平深居简出、苦心孤诣,能在这个体系里节制了多种学问,有很深成绩,并且德才兼备的人,方可被戴上“国学大师”的桂冠。如,近一百年来,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冯友兰等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他们通过举一反三,熔古铸今,打通了不同学问之间的界线,创造出许多刺目耀眼的学术高峰,他们被公认为国学大师,没有什么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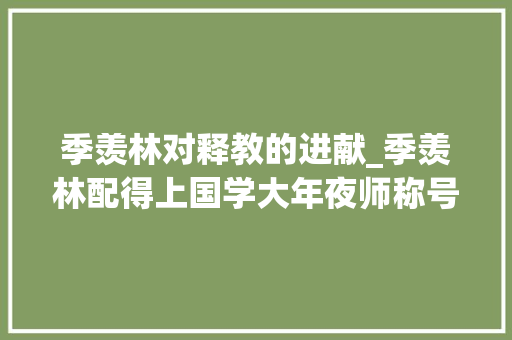
国学大师就像延绵不绝的山脉,不但崇高,在多个独门学科上创造了让人仰视的高峰,而且肚量胸襟博大,包罗万象,核阅起来有纵深感,深不可测,一眼看不到边。
如奇峰兀立那样,在独门学科上创造出高峰的人,学术成果显得过于单一,难以成为服众的大师,充其量是一位著名学者。
在当今学界,若论起学问,季羡林(1911年——2009年)绝对称得上是最有分量的著名学者之一,从措辞学、翻译、佛学、历史学,再到文学、国学和教诲,跟人文学科有关的许多领域,他多有阅读,并且造诣斐然,著作等身,当今学界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学者,确实寥寥无几。
季羡林像
再加上他活了98岁高龄,德高望重,把他定位为当今文化界的模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但要把他说成是文化泰斗或国学大师,就值得商榷了。由于他的学术成果不敷以支撑起这样的光彩。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季羡林因此措辞学家的身份著称于世的,他精通汉语、德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南斯拉夫语、梵语等12种措辞,是当代不多见的措辞学天才。
能节制这么多措辞,源于他在20岁就考取了清华大学泰西文学系,大学四年主修德语,课余韶光一边坚持用德语写作,一边翻译德语作品。
季羡林与饶宗颐
或许是打仗外语较早的缘故,以至于让他在后来的学习中,把大量精力和韶光用在了外语的学习上。尤其从1935年夏季开始,24岁的季羡林有幸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韶光长达10年。这次留学,直接开启了他在措辞学上的天赋,让他探索到了可以同时攻读好几门外语,并把每一门课程学到尽善尽美的好方法。由此,他用这十年光阴打下了远远超过同时期学者的深厚的措辞学根本。在后来,他发挥自己措辞学方面的上风,是迎刃而解的事。
连季羡林自己也承认,在德国留学十年,他除过研讨措辞学之外,对其它学问险些没有阅读过。在研究梵文时,须要对印度的古典文学选读一些,就像研究汉语时必须要阅读唐诗宋词元曲一样,但他身在异国他乡,留学韶光有限,为了争分夺秒地攻读措辞学,他连阅读课外读物的韶光都挤不出来。
季羡林《罗摩衍那》译本
靠着这份刻苦精神,到1945年返国之际,他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位精通多种措辞的专家。
往后的研究成果也证明,季羡林生平的主要学术贡献,多集中于措辞学方面,在古印度语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佛教史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及印度语文学名著的翻译等领域,他都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尤其在吐火罗语研究和佛教史研究方面,如,他的学术著作《〈福力太子分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以及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具有首创性,补充了我国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空缺。因这些学术成果的流传,他注定会留名青史。
季羡林书法
然而,这些学问很难跟传统国学扯上关系,它们跟国学,完备是两个体系的文化。
如果把季羡林看作是国学大师,不但对同时期的其他国学大师不公正,对季羡林自己也是不公正的,大有冤枉季羡林的嫌疑。就像某人本来是一位精良的小提琴演奏家,却要逼迫人家去弹奏钢琴,岂不是强人所难?也会凸显出是非不分的知识性缺点。
当外界把季羡林定位为国学大师和文化泰斗,常常向外鼓吹时,连季羡林自己都以为很反感,由于他有自知之明,身上流淌着民国文人的遗风,非常看不惯那些钓名沽誉之辈,他不想在历史长河里被千夫所指。
《病榻杂记》
在2007年,借助随笔集《病榻杂记》出版之际,季羡林终于站出来为自己澄清了,他难以忍受被人误解,不喜好自己的身份被外界张冠李戴。他用自己的学问,向人们阐明了国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学者才对得起“泰斗”的称谓。
他进一步昭告天下人: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还我一个自由清闲身。
这便是真实的季羡林,生平命运多舛,却直肚直肠,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这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值得当今所有学者去仰望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