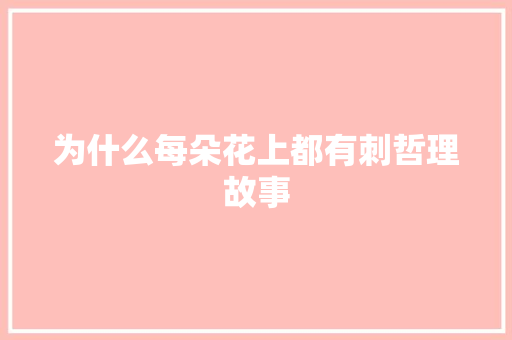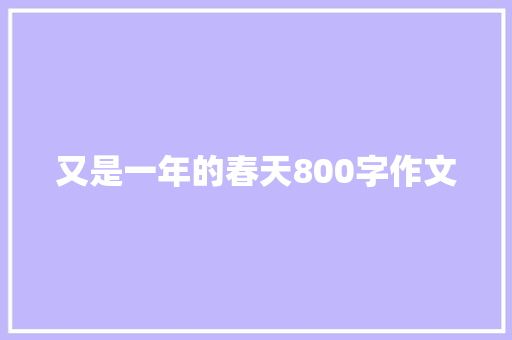在云南北方的冈子上,一树树梨花像白色的火把那样斜插在红木的山地中,剧烈地燃烧,大风吹过,各处是白色的火星子。与此同时,在云南之南,大河滚滚,波澜是蓝色的。两岸的低处和高处,阳处或阴处,干地或湿地,全都已经被花朵盘踞,它们正开得一片稀烂。花的脂肪从树枝上淌下来,壅塞了大河两岸的那些眇小的支流,也阻碍了其他植物通旭日光的道路。
你当然曾经像一只幸福的蜜蜂那样闯入过这样的春天,但你毕竟不像蜜蜂那样,和花朵是一种在家人的关系。你进入春天,但你是出家人。你的道路与一只蜜蜂正相反。它偶尔撞入你的房间,它终极要找到返回春天的道路。以是,你生平中,虽然每个春天都听见花朵在山冈上号叫,但你只有很少的韶光能亲抵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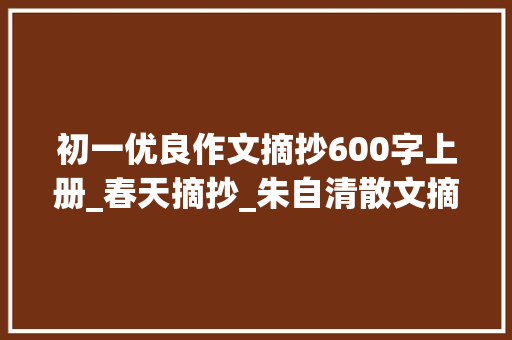
我曾经强烈地体验过这种残酷的无关,那时我在芒市附近的森林中,春月无边的夜晚,我独自一人,走过一座又一座铺满去年12月落下的,尚未腐败的树叶的冈子,地面被月光戳出无数的斑块,蜜蜂不知到哪里去了,一起上遇见无数的花丛,它们中的一些,当着的面打开,撬开烈酒罐子似的把气味放出来。这些花朵有些在月光中,有些在暗处,冒死地开放着,前赴后继,枯萎的才垂下,掉下,新的骨朵又打开了。仿佛有什么不可抗拒的诱惑在表面吸引它们,实在什么也没有,它们仅仅是要打开,要捐躯在盛开之中。在这俏丽无比,安静,风凉的春夜里,我却受着烦躁,怏怏不乐,像一只找不到活干的狼。
我又听见一朵马缨花“叭”的一声开放了,我忽然明白,我烦恼的根源是,我不想当人,我想当花,我要开放。我渴望作为花朵之一,与这个春天的故乡,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