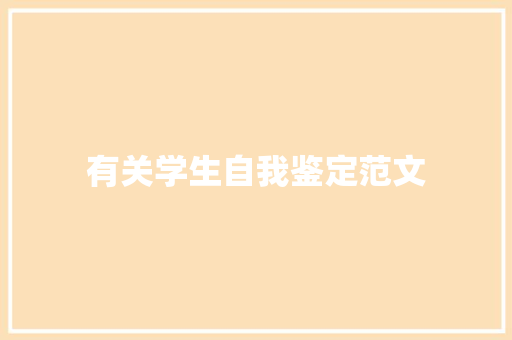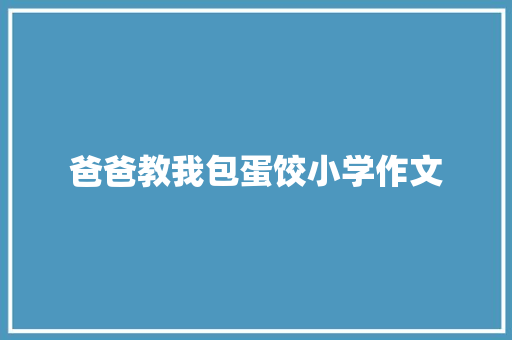对付《文献通考》的代价,四库馆臣所撰《四库全书提要》时称:“臣等谨案《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马端临继杜佑《通典》而作。《通典》于历代因革之故粲然详备,端临病其节目去取犹有未尽,因上本经史参之历代会要、百家传记以及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门分种别,或续或补,可谓广博矣,端临为宰相廷鸾子,隐居著书,宋、元史皆不为立传,他著述亦无闻,而是书特足千古。”
《文献通考钞》二十四卷 清康熙二年序美延堂刻本,书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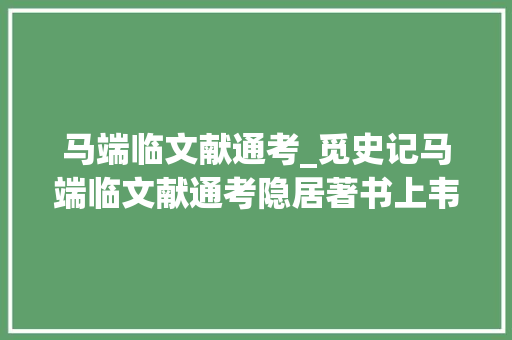
由此可知,《文献通考》乃是杜佑《通典》的续作。故杜维运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评价说:“中国史学史上乃至天下史学上第一部贯穿高下古今数千年的典章制度通史,是唐杜佑所撰的《通典》。自此往后,南宋史学家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而《通志》出。元初马端临衔亡国之痛,撰《文献通考》,一部最详赡客不雅观的典章制度通史,悠然涌现于天地之间。这是不朽的盛事,历史的伟业。”
杜维运将三通称为不朽的著作,其亦讲到了三通的递传关系,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媒介中则说了这样一番话:
有如杜书纲领伟大,校勘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仪式,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往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文献通考钞》二十四卷 清康熙二年序美延堂刻本,媒介
看来《文献通考》的确是把杜佑的《通典》视为撰写目标,马端临在媒介中首先夸赞《通典》体例之佳,而后称《通典》亦有欠精审之处,同时他也讲到了古今情形的变革,由于唐朝之后的变革杜佑不可能理解得到。同时,马端临也说《通典》一书短缺天文、五行、艺文等志,而这些志在历代史籍中都有。正是由于有这些毛病在,以是他扩大了《通典》的收录范畴。
杜佑的《通典》即二百卷,共分为九门,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有二十四门之多。对付后者的分类,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迨至宋末马端临出,乃以杜氏之书,天宝往后阙而未备,理宜续辑,乃因杜书而广之,以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立二十门:曰《田赋》、曰《泉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日《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凡十九门,俱因《通典》之成规,而离析其门类,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业绩之所未备,天宝往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凡五门,则《通典》所未有,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而该书的卷数则多为三百四十八卷。李宗侗在其专著《中国史学史》中把《文献通考》称之为:“总古今典章制度而考之者。”而后,讲到了该书的特点所在:“共二十四门,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可谓集古今典章之大成。”
《文献通考钞》二十四卷 清康熙二年序美延堂刻本,马端临媒介
虽然在门数和数量上有这些增加,但后者不是前者的扩编,王瑞明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文献通考》一文中称:“《通考》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把材料交融贯通之后写成文,照杜佑的话说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实现为现实政治做事的目的,而类从条贯,以供校阅阅兵之便。马端临写《通考》,则是从学术角度着眼,在材料处理上,突出史家治史的特点,尽可能保持史料的原貌,不加粉饰雕凿。该当特殊指出的是,其材料并非随便抄录,而是有所推敲取舍的。”
可见,马端临为了更多的保持文献的原来面貌,他并没有对一些史料进行改写,而是直接抄录于书中,这正是该书与《通典》不同之处。以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点明了《文献通考》在这方面的代价所在:“从《通典》到《文献通考》,典制体史籍有了重大发展。马端临写的24考纠正了《通典》‘节目之间未为明备’的缺失落。可以看出马端临对付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紧张是对付封建社会的一个横剖面的意见,这种意见把封建制社会的紧张组成方面都列出来了,并且从经济制度谈到政权机构、表达等级制度的礼制、弹压武器以至意识形态,这是按照社会征象和事物发展中本末先后的地位列出来了。虽然马端临勾画出封建制社会的素描的图景,但还不能说出其间相互的内在联系。”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明嘉靖冯天驭刻本,媒介
但正是由于《文献通考》部头大而原始文献多,有人说这正是该书的弊端所在,明王樵在《方麓集》中批评道:“马端临力不及古人远甚,联比无法,殊欠办法,中间议论不无可采者,而卷帙已多于本史,要之可备裁削,难号成书。故今只以本史为主,删其繁文,笔其领要,补其阙略。”而章学诚也同样认为:“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洁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不雅观止矣。至若古人所谓决议确定去取,各自成家,无取周遭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天河矣。”(《章氏遗书·邵与桐外传》)
章学诚认为马端临只是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而其书中没有自己的主见在,同时章学诚又称:“《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剖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文史通义·释通》)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明嘉靖冯天驭刻本,卷首
章称《文献通考》一书实在只是部类书,没有编纂者本人的思想在,这类书只可视之为科考参考书。杜维运在其专著中回嘴了章学诚的批评:“这是将《通考》算作整洁类比的类书,无别识心裁寓于个中,不敷以当一家之言。抑低《通考》之论,无过于此。然细稽之,殊为不然。《通考》于浩繁的资料渊海中,有其‘决议确定去取’,非仅‘剖析次比’;其所呈现的史学思想,尤为宝贵,值得效法。”同样金毓黻也认为章学诚贬斥《文献通考》没有道理:“章学诚讥《通考》无别识通裁,实为类书,便于对策敷陈之用(《释通》),此殊不然,章氏尝许《通志》一书有别识通裁矣。而二十略多抄自《通典》,不易一字,不识所谓别识通裁者果何在,而《通考》之于《通典》,则无是也。浅学之士,贵耳贱目,其轻视《通考》,实由章氏启之。”
但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所著,马彪所译的《中国史学史》中却基本赞许章学诚的不雅观念。该书中首先称:“《文献通考》的渊源可追溯至杜佑的《通典》,其体例虽亦依据了《通典》,但是其目的又是不同的。《通典》是为节制当时政治的贵族阶级供应经世策而撰著的,《文献通考》则是为了运用于王安石以来所实施策论考试而撰著的。但是作为出于这种目的的书,虽然由于其精彩的成书而与《玉海》一样都未被列入类书,而是与《通典》一同归入政书(《四库提要》也是同样),但实际上本来是作为类书撰写的。”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明初经厂刻本
内藤湖南认为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的目的,乃是为了适应王安石所实施的新的考试制度,而马端临也确实在《文献通考·职役考一》中评论辩论过王安石新法之事:
盖荆公新法,大概立于理财,以是内而条例司,外而常平青鸟使,所用皆苛刻小民。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盘剥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无弊。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
由此可见,马端临亦能复苏地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问题所在,故他对新法所实施的学校、选举等方面的变革多持否定态度。那如何评价马端临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呢?吴怀祺在其所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中总结称:“总之,我们不能笼统说马端临是附和王安石变法,或者是反对王安石变法。马端临在根本方面是肯定变革的,稽古经邦者,应该‘知时适变’。马端临以变通的思想写历史,总结历史,这种变通的史学思想和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是合拍的。他对王安石的新法也有评价不当和误解的地方,而这正是某种偏见的反响。”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明嘉靖冯天驭刻万历崇祯递修本,卷首
内藤湖南也不认为《文献通考》属于类书,但他同时又说:“像《文献通考》这种作为考试(决科)用书的,在此稍早些时候已经有《古今源流至论》。在当时此书明显地是为了论策之学(策学)而撰著的,这种体例的书本在明清时期仍多有撰著。这些书与其说是书写论策的材料,不如说是作为原本而撰著的,《通考》并非作为原本,而是作为材料成书的,个中有着作者自己的见地,是可以用于策论的著作。”既然如此,《文献通考》有没有作者的思想在呢?内藤湖南在其专著中持肯定态度:“与《玉海》是出于辞学目的而著述一样,此书该当说是出于策学的目的而撰著的,但是都有着超出其当初目的以上的成果,实乃作者的精彩贡献。”
但就整体而言,后世史学家对《文献通考》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虽然有人赞誉《通典》的代价高于《文献通考》,但金毓黻却认为这两部书各有千秋不分轩轾:“近贤之喜称《通典》,盖亦有故。《通典》一书,长于言礼,多存古训,极有裨于治经。而《通考》则否,此专经之彦所取资也。《通典》之文,简而不俚,首尾一向,极有助于文章,而《通考》则否,此又缀文之士所乐道也。若夫研史之士则不然:仪式贵明其因革,而不必多录旧说,文章贵详其原委,而不必过为润色。以体例言,《通典》之详于仪式未必是,以事实言,《通考》之详于纪载未必非,虽《通典》所载魏、晋六朝议礼之文,别有其名贵之代价,乃应划入经学范围,自为专书,混而为一,未见其可,此为经学、史学不同之分际,非深通其异同之故者不能知也。清儒之治史学者,多自经学入,以治经之法治史,故盛称《通典》,不悟总览全编,窥其大略,固以简严为贵,若专取某一门而磋商之,详如《通考》,犹病其略,况《通典》乎?此又治史之术之不同于治经者矣。”
清乾隆期间,敕令整理、翻刻《文献通考》一书,而天子特意写了篇媒介,弘历在此序的前半段夸赞该书说:“朕允儒臣之请,校刊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献通考》付之剞劂。是书曾蒙皇祖圣祖仁天子命礼臣补订残缺,御制序文梓行宇内。顾简帙繁重,年久不无漫漶。今悉仿十三经,二十二史成式刊订,盖于是家有其书矣。朕惟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长于《通考》之书。其考察精审,持论平正,高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落之林,固已粲然具备矣。”
至少在乾隆天子眼中,《文献通考》一书很有代价。而明末藏书大家胡应麟在《报童子鸣》一文中也大夸本书之佳:“得足下藏书目阅之,所摆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古今书目条例,惟《隋志》最详明,马氏《经籍考》荟萃晁、陈诸家,折以己意,几于豪发无憾,迨今得见古人著述,大都每每藉此。”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明嘉靖三年礼监刻本,卷首
胡应麟不但认为《文献通考》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并且很多古人的著述都是由于该书有《经籍考》一门,得以让后世得知。以是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又夸赞该书说:“番阳《通考》以四部分门,实因旧史,而支流派别,条理井然,且究极旨归,推明得失落,百代坟籍烨如指掌。倘更因当时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题,稍存故实,则庶几尽善矣。”
马端临虽然有此宏著,但关于他的平生资料记载却很少,他生活在宋末元初,然而《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他立传,直到明末清初,在《元史类编》的《宋元学案》中才有了他的小传,而正史 中只有柯劭忞的《新元史》有《马端临传》: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父廷鸾,宋右丞相。时休宁曹泾深于朱子之学,端临从之游。以荫补承事郎。宋亡,隐居不仕。著《文献通考》,以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后成书。延祜四年,遣真人王寿衍访求有道之士,至饶州路,录其书上进。诏官为镂板,以广其传,仍令端临亲赍稿本赴本路订正。初留梦炎与廷鸾同相,及梦炎降,召致端临,欲用之,以亲老辞。后为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教授三月,谢病归,卒于家。
看来马端临也是官宦之家出身,他的父亲马廷鸾曾在宋末任过丞相。宋朝灭亡后,马端临不仕新朝,虽然朝廷对他有征召,但他武断推辞,只将自己所著的《文献通考》转呈给朝廷,由此而这部大书刊刻出来流传后世。《新元史》中说马端临曾拜曹泾为师,关于曹泾的情形,《宋元学案》中称:“曹泾,字清甫,休宁人。八岁能通诵五经。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簿。博学有名,马端临尝师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