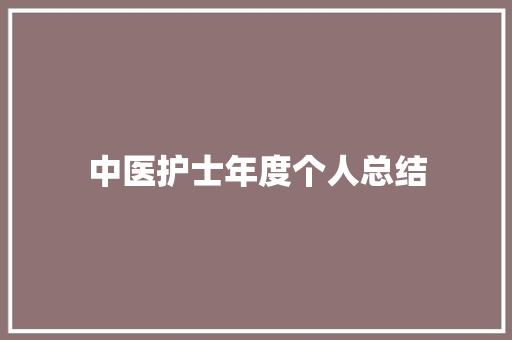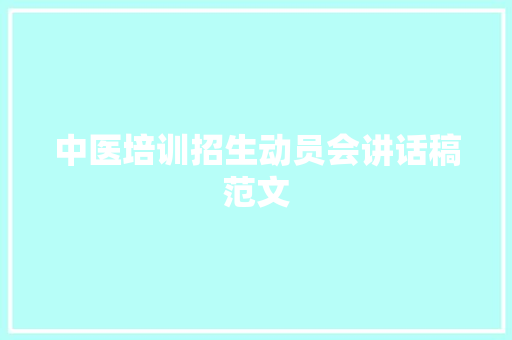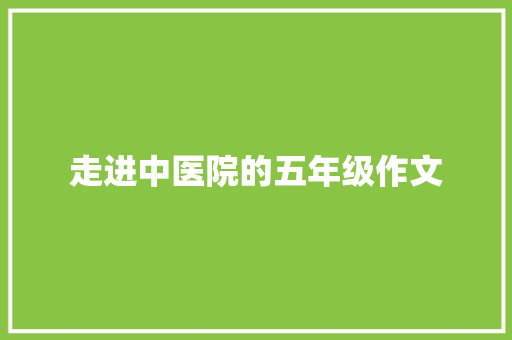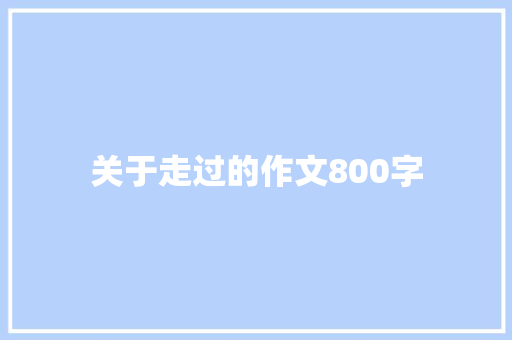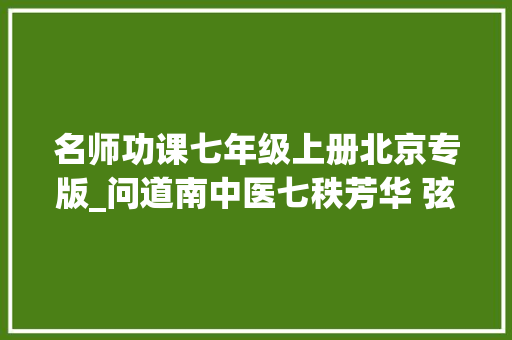大哉医乎,其来尚矣!
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周礼》“天官”一章记有“医师”。据记载,春秋时秦国著名医家“医缓”“医和”,分别为“病入膏肓”的晋景公、“病如蛊”的晋平公诊病,言“疾不可为”而获“良医”惊叹。更有扁鹊医“虢太子尸厥”、言“齐桓侯病至骨髓”,被奉为“神医”。
春秋后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使御用的医术逐步传入民间。自此以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钱乙、李东垣、朱丹溪、张景岳、傅山、叶天士等一批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医坛巨星纷纭出身,创造出浩若星海的中华医学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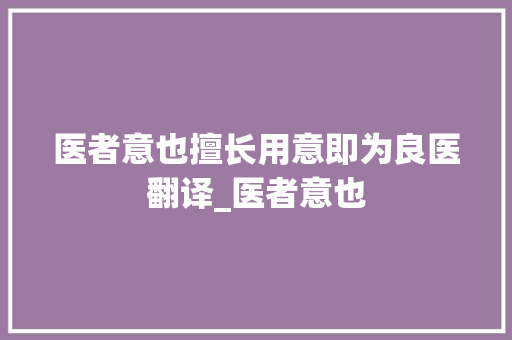
不雅观其妙,医者,意也!
这一不雅观点,《黄帝内经》就有昭示。《灵枢经·本神》曰:“心有所忆,谓之意。”唐代大医孙思邈认为:“医者,意也。长于用意,即为良医。”百名“都城名中医”之一、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科研究所所长王庆甫认为,“意”应有三:一是要居于仁,二是要合于道,三是要敢于出新。
首先,居于仁。北宋名相范仲淹云少年立志“不为名相,便为名医”。名相与名医虽分工不同,一个治世一个治人,但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安康,均为“仁心”所致。《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法自然”思想中的“天心”,即是民气。仁者爱人,“仁心”便是“天心”,中华医学精髓之处便在于“仁心”。
纵不雅观中华医学集大成者,莫不透彻“天理”,行仁道之术。与此同时,都是参透儒释道三圣而守正出新,辨症施治、情怀慈悲的“上善若水”之人。唐刘禹锡《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便是深秋时节北京北三环外那座普通医院门诊楼王大夫行医时的真实写照——面对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王大夫始终和蔼可亲,措辞舒缓而武断有力,对病理的剖析清晰通透,让每一名饱受骨痛折磨的寻医者如沐东风。
其次,合于道。医者的任务便是认识和把握“养生救病”之道,使人康健永生,度尽天年。王大夫认为,医者治病除疾,必须长于思考。在稽核病人的证情之后,还要结合地域、天时、景象、人事等等,进行深入剖析、综合,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方案。
物在天中,天包物外,天地万物,本同一气。人与天地万物不仅同“一气”,而且同“一理”,即遵照共同的规律。中医中的“天人一理”,是指阴阳变革之道。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成骸。因此,人性即天道,人的“小宇宙”与天的“大宇宙”,为四象应天,四体应地,人生于地,命悬于天,统统均应遵照规律。
与此同时,知常达变,才能先治本、再治标,抑或先治标,再治本,达到以身论之。《黄帝内经》云:“智者反物不雅观道,愚者反道不雅观物”,便是要“见表而知里,睹微而识著;瞻日月而见光影,听声音而解鼓响;闻五声而通万形,察五色而辨血气”。要通过问病由、“察色”“诊脉”等感知,而“知里”“识著”“见光影”“解鼓响”“通万形”“辨血气”,由感知而达“神知”,由表及里、由征象达实质,达到“知形为粗,知神为细”的境界,把抽象的观点、判断、推理的感性认识,不断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得到医之道。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敷。”《黄帝内经》指出,“实则泻之,虚则补之。”这便是中医辨析证情、以意施治的理念和方法,尤其长于思考是主要方法。
再次,敢出新。中医传承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精髓。天下上的四大古文明,完全保存到现在的紧张有中华文明,而中医正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相较西医经由短短两百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医学领域的最强音之一,中医、西医各有其妙!
大医精诚,便是要长于思古化今,中西结合,守正出新。守正,便是要守中医“医者仁心”之道,在望、闻、问、切中施以“先人再病”之治疗;出新,便是要长于利用西医的技能手段来精准探寻病灶,达到在中西医结合中系统、全面、辨证施治。
中医的本源是重整体。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等,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保持平衡性。因此,人的局部病理变革,每每与人的全身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等相互联系。诊断时,可以通过外在的变革而判断内脏的病变。
中医辨“证”论治,西医对“症”处理;“证”,便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位、病因、病性等)以及正邪关系,而不但是对“症”的处理。与此同时,中医重“开导”,西医讲“对抗”是其治疗方法的差异。
因此,长于用中医的理论来剖析病理,用西医的前辈科技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是当前疾病医治的最佳善策。仁爱与医术同行,中医与西医同轨,乃是医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