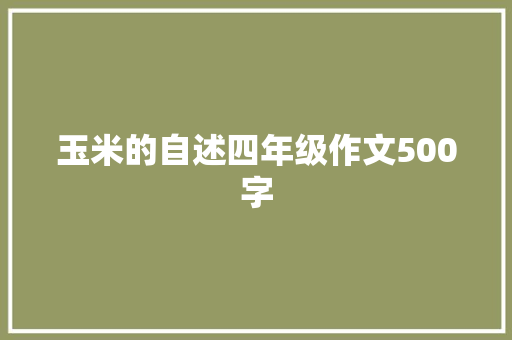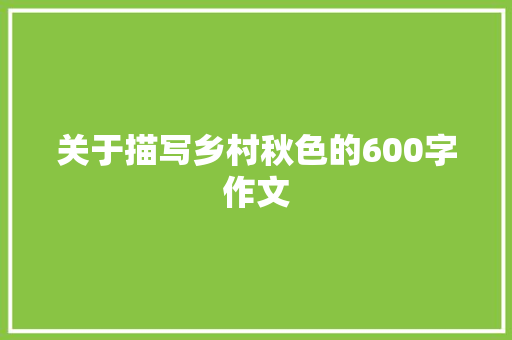爷爷奶奶和大伯是常住在老家的,爷爷和奶奶是农民,每到玉米收割的季节,他们就立刻变得忙活起来。
收割机割了玉米,一回到家,就开始剥玉米;每当这时候,家中的院子里除去两辆三轮车,便几乎遍地都是玉米了,黑乎乎的苍蝇在玉米粒群上飞来飞去,“嗡嗡”响着,噪声极大,很讨人烦。每次我都去拍苍蝇,可一时拍散了,下一秒它们又会飞回来。爷爷那块地产的玉米,每年都能卖个三四千,如果哪一年卖了五千,那绝对是大丰收了。

既然家中种玉米,那么玉米免不了要常常出现在饭桌上。奶奶会挑出几根看上去不错的玉米,放到一个大土灶里去烧。她一手拉着风箱,一手还不忘往土灶添上玉米秆。没多久,一锅黄中带紫的玉米就被端上了餐桌。我和堂弟堂妹都着急伸手去拿玉米,可一看到那一大堆的玉米须,我们又无可奈何——满玉米几乎都是须。虽然须难拔,但那浓郁的玉米香味,我却永远也忘不了。
大伯是村附近一所小学的校长。我去参观过那所小学,和苏州的小学比,不能算大。最近改装后,一个年级有六到七个班,操场不大,但器材却排放得整整齐齐。学校里还有一条狗,挺凶,上次追得我满学校跑。大伯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所以每年春节,村子里就有许多人排队让大伯写春联。我也打算要让大伯写一幅春联带回苏州。
虽说缝合村小,但它却有一道很美的风景。每个晴天的早晨五点多,我就会偷偷跑出家门去田边观赏日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早晨,烟雾弥漫,我开着三轮车打着灯,朝农田那儿开。太阳那时还是熟蛋黄的颜色,说黄不黄,说红不红。农田旁有根木电线杆,我在三轮车上静静地观赏着太阳越出地平线,到了木电线杆的位置,之后,又上升到了木电线杆上。在不强烈的阳光下,我看见了一位老人坐在田梗上,那正是爷爷。那个早晨的景色早已过去,过了四年我都没忘。
老家是美好的,可惜二伯、爸爸、姑姑和四叔都在苏州工作,每年回到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我一年都回不去一次。一有回到老家的机会,我就很珍惜,因为我担心哪一天农村老家拆迁了,我就再也看不到熟悉的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