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里,麦稍黄了。
树上,杏儿喷鼻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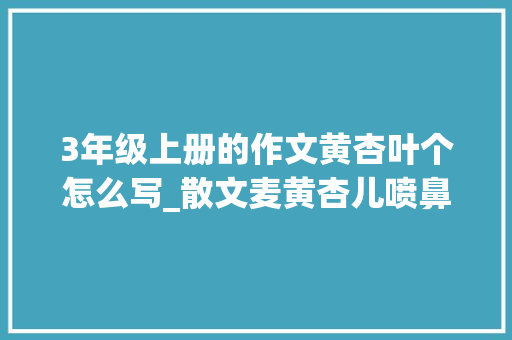
麦黄杏,踏着季候,如下凡的仙女,带着诱人的喷鼻香,来到人间。
杏喷鼻香,我久远的影象……
小时候,站在家宅上,望着不远处的杏树,看它着花,结果,直到黄黄的杏压弯了枝头。
希望,一次次被它撩拨着,按捺不住的心,渴望的眼睛,一次次的冲动,吃到它时的贪婪。至今,想起来,我都有点不解或是困惑。
杏树与家宅仅一起之隔。
长在老坟墙的东南角上。
很小的时候,不懂老坟墙是什么所在,稍大些,觉得名字怪怪的。直到有一年,那片老坟,一夕之间移为平地。心智未开的我,听大人说,这里是祖宗的宅兆。这彷佛与我没多大关系,由于,我只关注那棵年年着花结果的杏树。
老坟没了,杏树还在。
一株终年夜了的杏树,枝繁叶茂,肆意伸展着的枝头,彷佛要把那片空下来的地方都覆盖起来。
我盼着春天,看着它开出一树的杏花。我常常会爬上那道坡,围着杏树,转着圈的瞅着开艳了的花,看有没有一个小杏住在花的中间。虽然一次次让我失落望,可也不厌其烦的看着,想着,盼着。
花谢了,那豆粒大的小不点儿涌现了,狂喜的我,跑回家去见告妈妈,杏树长杏了。
妈妈只是微微的笑,淡淡的说声好,便也罢了。
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不像我一样,欣喜若狂呢。
鲜嫩的叶子长满枝条,掩在叶子里的青杏一每天终年夜。我便日昼夜夜的盼着。
当妈妈说;“杏子让你看的都不敢长了,你打草去,看田里的麦子吧,麦子黄了,杏便喷鼻香了。”
我去田里打草,看麦子长高,盼着麦子黄稍。
总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在清晨的早上,在夕阳西下的傍晚,偷偷去看一眼树上杏子的大小。
村落庄里,一样平常大小的孩子们,早早来树下张望,看到青杏微白,就急着品尝,一口咬下去,酸了牙齿,倒了牙床,还是狠劲的咀嚼,吞下的是诱惑,尝的是酸涩的希望。
麦子黄了,杏子,果真的喷鼻香了。
树低真个杏子,已被孩子们尝光。
树枝头的杏黄,馋的孩子们口水流淌。
大点的孩子,找来打枣的长杆,在竹扫帚上折根带叉的枝条,用布条把竹枝倒挷在长杆上,伸出长杆,用竹枝的倒叉钩下又大又圆的黄杏,落下一个,一群虎视眈眈的娃,轰笑着,打闹着,抢一个,吃一个,有时怕得手的杏被抢走了,顾不得擦净杏子落地时沾上的土,就急急忙忙塞进嘴巴里。
直到杏树上再也不见杏子黄,散了的孩子们,眼睛里流露出看的见的失落望。
杏树在终年夜,孩子们在发展,老坟墙那片地皮上,新栽下的梨树开了花,挂了果,还在的老杏树,依然着花结杏。
老坟墙的周围种下的刺槐,密密麻麻。
得到管理的老杏树,花开更繁了,杏子更甜了,喷鼻香气飘的更远了。
我终年夜了,在老坟墙坡下的路上,来回在家与学校的路上。
春天,杏花开的时候,是一种精神上的陶醉。麦子黄了的时候,杏喷鼻香,是一种享受的释怀。
站在教室讲台上的我,陈说着春天,杏树,杏花,还有麦黄杏的喷鼻香。是在见告我的学生,写一篇好的作文,须要什么样的构思畅想。
那一年,我走的时候,特意来到杏树旁。
看着它矮矮的树身,巨大的树冠,在玄月的蓝天下,威武的像个将军。
是呀,在它麾下的孩子已经终年夜。吃过它酸甜杏子的娃,来与它告别,就要离家。
哪一年,我未曾留神
………
哪一年,是它的拜别
………
是它记不得我了,还是我已经把它忘却
……
麦子又黄了,杏子又喷鼻香了,再有几日,我一定回去,去我成长的地方,去寻老杏树的影象!
我会去的
去觅麦黄杏的喷鼻香………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