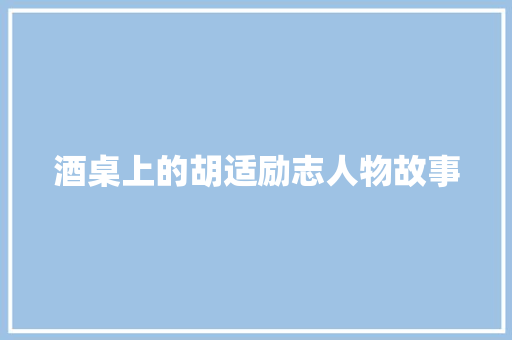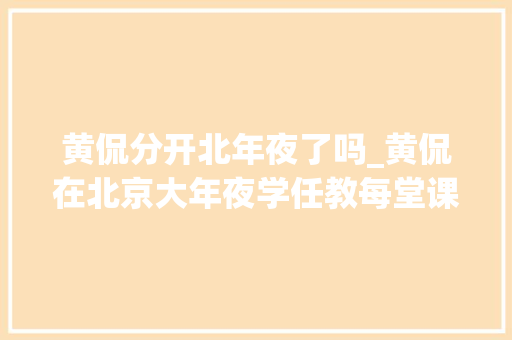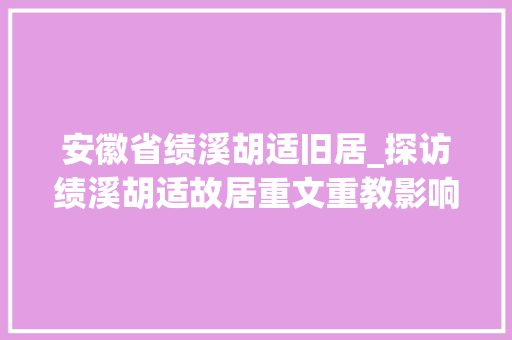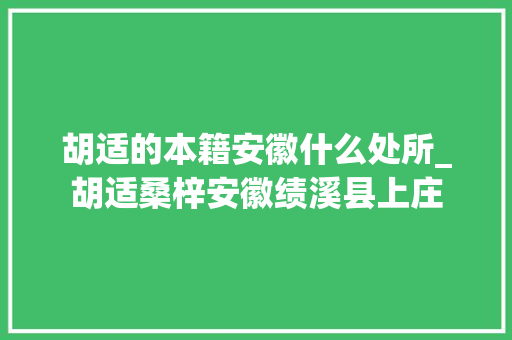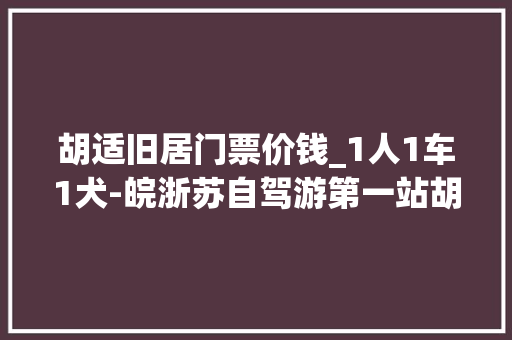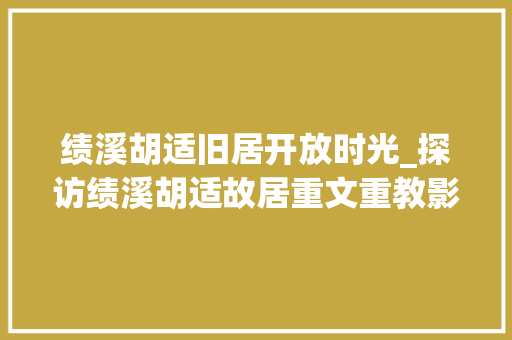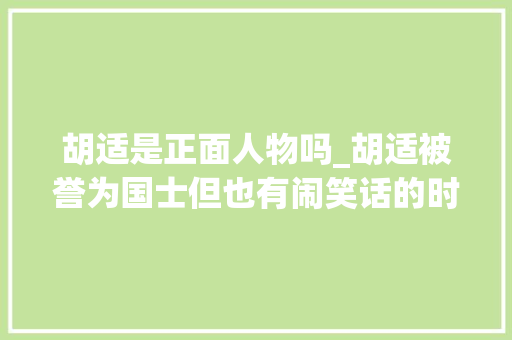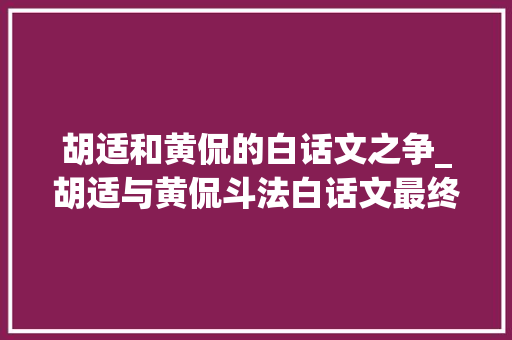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被称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被称为“人的文学”,但这并不是说从前的社会不重视人及其个性,也不是说从前的文学没有反映人的生活和表现人的精神。“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五四时期,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首要地位。中国古代、近代也重视人,但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时,个人才得到尊重,而五四则改变了这样一种个人与国家的从属关系。五四虽然仍然强调国家民族的终极性,但并不把人完全从属于国家和民族,“人”本身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具有根本性。周作人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1]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3],因此他主张提倡个人主义。所谓“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人间本位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即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近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属于中国现代的“自由”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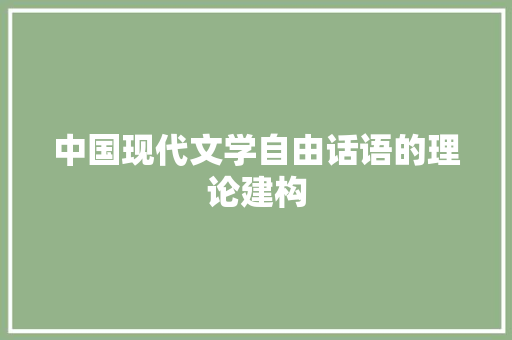
“人的文学”和“国民文学”就是在新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人”和“国民”具有同义性,在内涵上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人”和近代梁启超等人所说的“国民”有了很大的不同。“人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从根本上也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所以周作人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4]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兽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5]“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的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的,也不是神性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6]再有,他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7]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8]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周作人还有很多论述,从上面所引诸话来看,周作人实际强调“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他承认文学具有人类性,但这是建立在“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人类”在周作人这里实际上被个人化。他反对把文学纳入国家、种族和家庭的范畴,反对把文学当作实现国家、种族和家庭目的的工具,因为如果是这样,个人主义在文学中就会受到伤害从而泯灭。在周作人那里,个人主义文学本质上是把个人从国家、种族和家庭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纳入其中。当然,周作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比较特殊,他自己称之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极端个人主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人对国家、种族和家庭的态度都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但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李大钊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友好、同情、爱慕的东西。”[9]又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0]“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1]李大钊关于“人”及其“个性”的观点既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而言,但同时也具有理论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李大钊提倡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的意味,李大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的个性的本质。在个人的属于国家、家庭的前提下、在人的个性遭到压抑的前提下,“修身”不仅不能解放个人,反而会使个性受到更大的压抑,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语境中,“修身”就是按照纲常名教泯灭自己的个性,它不过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所以他说:“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故言之不觉其沉痛也。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李大钊对个人主义的提倡也是在理论上而言的,他认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认为“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12],就具有抽象性,这和近代的个人主义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显示了李大钊对于“人”的新的理解。
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物质繁荣其实只是其社会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根基则在人,具体地说,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走向富强,其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即“立人”,而“立人”的重要方面是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具有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和残留,即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或者说国家的终极性。
但对于个人的内涵,鲁迅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近代:“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又说:“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4]这里,鲁迅把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与西方现代的个人概念进行了区分,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在意义上与自私自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害人利己,而西方19世纪的个人则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即独立、自由、个性、知识和理性,从而从根本上表现出人的主体精神与创造精神。
五四时期,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则更趋现代化,在《随感录三十八》一文中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对于这两种“自大”,鲁迅的态度是鲜明的:“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15]可以看到,鲁迅五四时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优先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个人,个人的素质提高了,群体就自然强大了。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以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强调个人以及具体的个性、独立、自由、尊严等一直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部分。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个人主义具有较多西方个人主义的色彩。
但是,强调自由的个人性以及自由对于群体、国家的对立和反对,即坚持西方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价值观,这只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又把个人主义相反的内涵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包容进来,并在独立、自主、自由的意义上把二者整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时也重视群体,重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并把它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以李大钊为例,如上所述,他在多处地方强调个人自由以及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性原则。并且,他也清楚地看到了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扩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p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二者进行整合:“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中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17]在李大钊看来,个人与社会具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相谐和的一面,而相谐和不是在利益的层面上,而是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的层面上,而后者则是西方自由主义在19世纪之后所一直强调的。所以,李大钊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从中国具体语境出发对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某些反思。哈耶克说:“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持自身。”[18]把李大钊的观点和哈耶克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影响深远。
由于长期的留学生活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的结果,胡适对西方个人主义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所以他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原本的。胡适对个人主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大力提倡和宣传个人主义。他推崇易卜生对个人的肯定,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对易卜生的戏剧进行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解读:“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胡适并且引了易卜生书信中的一段话为证:“我所最期待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有意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直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9]所以他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为有益的为人。”[20]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非常重视个人的社会终极性,也就是说,理论上他认同发展个人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发展社会这一观点,他说:“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才建造得起来的。”[2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文化救国论”,而文化的深层基础是人,所以“为个人”也是“为国家”。
但与中国近代的个人主义不同,胡适提倡个人主义的终极目标虽然仍然是国家和社会,但在胡适的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中国近代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从根本上从属于社会、服从于民族国家。而胡适则“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22],在他的个人主义理论中,个人对于社会和民族国家具有根本性,国家和社会从根本上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深层的基础。所以,个人与国家和社会具有一体性。“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量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23]这就比从前的简单地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所属物的观点要深刻,也比西方的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为个人服务的观点要辩证。
和鲁迅一样,胡适也把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的自私观念作了区分。在胡适的概念中,自私是贬意,而个人主义则是褒义。胡适援引了杜威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区分:“假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其特点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为我主义”是中国古代的个人主义。而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则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是“真个人主义”。“真个人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24]个人主义除了个性和权利以外,重要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理性和自由决策。《终身大事》最后有一句台词:“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25]在这种意义上,胡适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属于自由主义。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文化传统以及现实政治语境的制约,胡适的个人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又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胡适坚持了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性,但同时,他也承认社会对个人种种限制的合理性。他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即一方面承认个人有不受他人和社会干涉的权利,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又要对他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他行为和言论的后果负责,即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26]他既承认“小我”即自我,也承认“大我”即“社会的我”,并且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27]有人认为,胡适在这里表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某种误解:“当胡适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等同于易卜生主义时,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他把‘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看作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真精神’。而人格典范或行动范式就是娜拉的出走与斯托曼医生的敢与众人对抗。而在哈耶克的观念中,这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严重歪曲。”[28]应该说,胡适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确有某种误解,但误解的情形并非如此。应该说,胡适对个人主义本身的理解是很符合当时西方对于个人主义的普遍观点的。至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点,那已经是20世纪中期的事了,二者之间的不同,具有一种时间距离,很难说是“偏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反映了西方50年代及以后自由主义对上个世纪初以及更为遥远的功利个人主义的反思,它在很多方面与胡适站在中国立场上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造”恰恰是暗合的。
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西方原本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误解”,还不如说是西方个人主义话语在汉语语境以及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变异。西方个人主义思想通过翻译的途径引入时必然会发生某种歧变,因而会出现差异。而更重要的,中国自晚清以来,“救亡”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一切西方思想形态包括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批判,西方个人主义作为这种批判的锐利而有效的工具相对得到张扬,因而也比较原本。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更多地是在个人的层面上展开的。但随着这种个人解放时代的淡化以及民族矛盾的突出、革命思潮的高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很快地便被纳入了国家民族自由主义的范畴,个人主义便被深深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很快便让位于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以郭沫若为例,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虽然他那时的“自由”与“解放”具有更多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的意味,但强调个人层面上的自由与解放也是非常明显的,“我赞美我自己”、“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梅花树下的醉歌》),“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他的“大我”实际上是把民族国家和个人二者合二为一。但到了革命时代,郭沫若的态度便发生了大的转变,完全否认个人及个性。“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郭沫若实际区分了两种个性和自由,即“个人个性”与“大众个性”,“个人自由”与“大众自由”,“大众个性”和“大众自由”同样是自由的范畴,同样应该尊重,并且应该优先尊重。“要发展个性,大家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29]“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30]“我们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31]把社会与个人完全对立起来,并且强调个人绝对地服从集体,胡适的观点在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话语中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个人”与“国家”始终是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核心范畴,不同的价值取向使自由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郭沫若的“革命救国论”不同,胡适可以说是“个人救国论”,郭沫若是从救国的角度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那里,革命作为集体行为与个性和不受限制与束缚的自由是不相融的;胡适则是从救国的角度肯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并在自由的意义上把个人和国家二者整合起来。这在中国现代个人主义话语中同样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2]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自由从一开始就不是随心所欲。因此,作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其实同时包含了个人的权力和责任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个人主义并不只有个人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个人与社会之间并不绝对地相互排斥,把个人利益看成是与集体利益完全相对抗的观点是狭隘和片面的。“个人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自我完成无疑会促进社团的发展,而一个好的社团也肯定会有利于每个个人的自我完成。”“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虽然反对以集体的名义要求个人作无谓的牺牲,但绝不是唯我主义者,他关心如何协调这两方面的关系。”[33]但另一方面,自由的限制与责任并不导致在逻辑上对自由本身的否定,个人权利和国家、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同样不导致在逻辑上对个人本身的否定。事实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直在调节这二者的关系,并在调节中形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鲜明特色。
我们看到,五四时所引入的西方个人主义主要是一种功利个人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由的权利,强调社会的最终价值只能通过个人的幸福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来实现。功利个人主义有它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就是在对西方功利个人主义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实,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西方也是备受批评的,比如在法国,它就长期遭受非议:“‘个人主义’这个术语在19世纪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在法国,它通常带有一种贬义,甚至至今仍然如此,意味着强调个人就会有害社会的更高利益。”[34]“个人主义所摧毁的恰恰是服从和责任的观念,从而也毁灭了权力和法律;剩下的不就只有利益、激情和歧见的可怕混乱了吗?”[35]“不难看出,一个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就不再能处于正常的社会状态,因为社会是精神和利益的统一,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分裂。”[36]“个人主义的原则把个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周围事物和他自己的惟一评判者,赋予他不断膨胀的权利,而没有向他指出他的责任,使他沉湎于自身的力量,对整个国家宣布自由放任。”[37]个人与国家或社会在权利上的冲突和精神上的矛盾,这是回避不了的。对于中国近现代来说,这种冲突和矛盾尤其敏感。就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来说,中国近现代与19世纪的法国如出一辙。
一半是出于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一半是环境、文化、翻译、语言使然,西方个人主义在五四时的中国在介绍和引进以及应用的过程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中国化,二者奇妙地纠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品质。事实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就是中国人从自己的文化和立场出发对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反思以及改造,借鉴、挪用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中西合璧性。所以,就状况而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和方式上非常接近7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西方对20世纪初到70年代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反动和修正,具有反思的味道。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则是中国现代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思、修正、补充,具有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中国性,同时在中国性的意义上具有超越性。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始终在这两个层面上复杂地展开。
【注释】
[1]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5]周作人:《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6]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9页。
[7]周作人:《文艺的讨论》,《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8]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9]李大钊:《精神解放》,《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0]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1]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2]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2页。
[1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56页。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1页。
[15]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312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17]李大钊:《自由与秩序》,《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1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页。
[19]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481、486页。
[2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2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1-512页。
[2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23]胡适:《不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24]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4页。
[25]胡适:《终身大事》,《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页。
[26]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27]胡适:《不朽》,《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8]任剑涛:《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汉语语境中的论说》,《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29]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30]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3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3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4页。
[33]钱满素:《爱默生与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3、234页。
[34]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5]拉梅内:《革命进程与反教会斗争》,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36]弗约:《宗教、历史、政治与文学文集》,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37]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