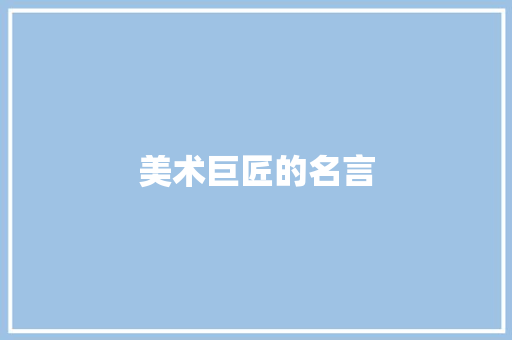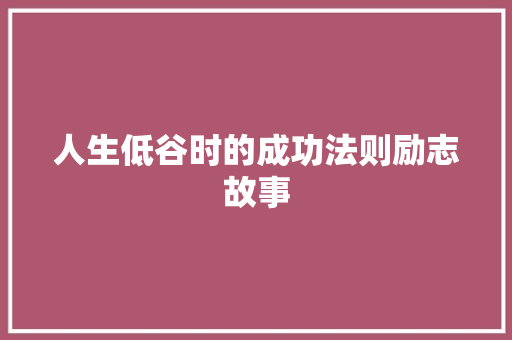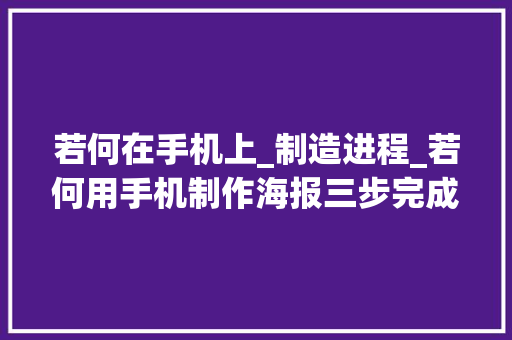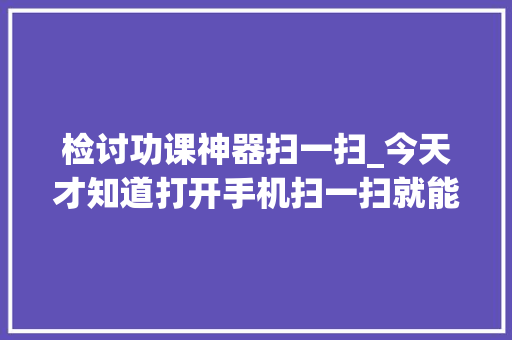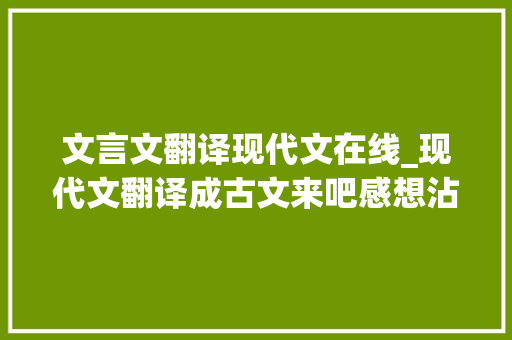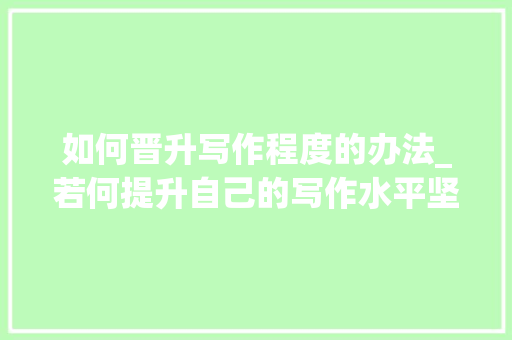陈振鹏 章培恒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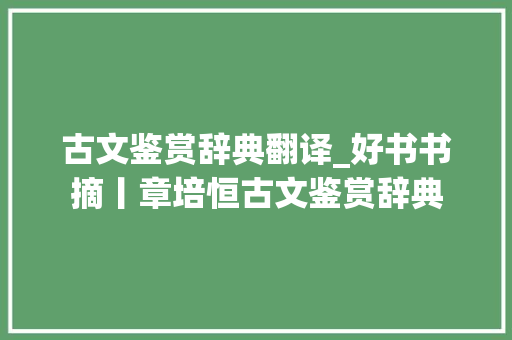
笔墨最初可能只是用来作为大略的标识,如不少研究者认为,在一些新石器晚期的陶器上,已刻有大略的原始笔墨,其意义大概便是如此。其后人们又用笔墨记录他们认为主要的事情,如贩子占卜之后,常把所问的内容与结果刻在占卜用的甲骨上,并将之收藏保存下来,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文献。一样平常评论辩论中国古代的文,都追溯到商代的卜辞,如朱自清《经典常谈·文》便是。但也正如朱氏所说,“这只算是些句子”,实际上还未成为“文”。商代的文献,该当还有通过其他路子保存下来的,像收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其真实性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它的内容比卜辞繁芜得多。载于《尚书》的包括《盘庚》在内的商、周两代官方文书,大抵是最高统治者就国家重大事宜揭橥的辞吐。这些辞吐虽然还保存着说话的语气,但笔墨显然是经由一定程度的整理的,因此它的意思能够表述得有层次而且比较完全。这些文书构成了古代最早的成篇的文章。
但《尚书》所记载的言辞还是很简朴。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对辞令的利用要讲究得多了。由于这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繁芜,说话欠妥当就随意马虎给国家利益带来很大危害。孔子说到郑国人“为命”即准备辞令,是“裨谌草创之,世叔谈论之,行人子羽润色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看来这彷佛已经是颇严格的书面起草了——当然临场利用还需机变。这一类外交辞令有不少还保存在《左传》《国语》等史籍中。到了战国时候,游说之士以口辩打动人主而取富贵,他们对演讲、鞭策的技巧都做过专门的研究,见于《战国策》的这一类笔墨,很有些滔滔不绝、辞采飞扬的长篇大论。
除了这些政治、外交场合的言辞,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讲学之风渐盛,学派林立,而各家的见地颇多相左乃至针锋相对,碰到一起难免发生口舌之争。在孔子讲学的年代,这种论争大概还不多,以是在其学生追记其辞吐的《论语》中,大抵是片断的语录。而《孟子》则已经因此善辩著称的了。但不同学说之间的论辩在口头上进行总是不能够十分严密和透彻,须要发展成为笔墨的表达。孟子晚年和学生在一起把从前他同人论辩的经由以及其他言辞加工致顿出来,成为《孟子》一书,实际是一种介于言辞记录和书面论述之间的东西。——以是书里面他的论辩对手,彷佛不过是拳击的靶子似的;有些恐怕只是虚设的论敌。《墨子》《庄子》也有类似情形,但也有更进一步的,便是纯挚环绕一个问题作书面的论述,这样就有了分开言辞记录的文章。而到了战国末年的《荀子》《韩非子》中,则可以看到篇幅伟大、构造严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了。
另一方面,对历史事宜的记叙,也由简单逐渐趋向于详明。如春秋时期鲁国的官史《春秋》(古代把它视为阐明《春秋》的书,现在的研究者则大多认为它原来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只是纲要式的历史大事记,笔墨十分大略,前后不相连贯,严格说来也不大能称为“文”。而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虽然记叙的历史阶段与前者大致相同,但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历史事宜的发展过程和有关人物的言行。因此在前者只用一句话就说完的事情,在后者每每铺展成相称长的篇幅,不少部分还描写得颇为生动。后来的《战国策》对有些历史事宜(包括历史传说)的描写,较之《左传》又更为详细和细致。这些史籍既保存了许多古人的言辞,又使记叙文得到很大的发展。
从上面简述的来看,文和紧张起源于娱乐的诗歌不同,它在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紧张是受实用目的的影响。孟子说春秋时期的特点,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这实在是社会和思想繁芜化的表现。这种特点在战国时期表现得更强烈,人们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更多不合,因此战国成为古文发展特殊迅速的阶段。不仅议论文,历史著作也向人们供应了作者认为是有代价的政治履历。
但在实用性的文中,一开始就并不排斥艺术成分的存在。举例来说,《左传》记晋楚邲之战,晋军败逃,有一辆兵车陷在泥坑里,追击的楚兵在后面教他们若何把车子弄出来,晋人得以摆脱窘境,很不好意思,转头说了一句:“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咱们不像贵国常常打败仗逃跑,以是没履历。这种小故事没有什么深意,只因此诙谐的意见意义让人以为好玩。而从整体上来说,历史著作除了记叙史实,向人们供应政治履历,那些人物故事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包涵着意见意义性,能够引发读者的人生感想。像《战国策》记苏秦游秦,狼狈归来,家里人都不给他好神色看;后来他游赵成功,得富贵荣华,家人遂对之恭敬有加,使得他感慨不已。这里面颇带有小说的气氛。拿诸子散文来说,目的虽然是在说理,但过于严明乃至呆板的说理总是不能让人喜好,以是作者须要在文章中加入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之类以造成生动的气氛,使读者随意马虎接管。而有的文章——如《庄子》中的多少篇,还常常直接抒产生发火者的感情,使人为之产生感情的共鸣。至于修辞技巧——如调谐音节、铺饰文辞、利用夸年夜手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增加阅读和记诵的愉快感。总之,只管人们须要从理性、从逻辑上去理解天下,但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究竟是最基本和无所不在的。文如果不能给人以鲜活的感想熏染和某种情绪上的打动,就很随意马虎令人厌倦。
秦汉以降,文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革。在记叙文方面,《史记》把《左传》、《战国策》的传统大大推进了一步,它不仅长于刻画人物,而且这种刻画中还蕴涵了激情。战国纵横家夸饰风格的笔墨与楚辞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汉赋。这种分外的文体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美文”,由于它虽然也拿儒家的大道理作掩饰笼罩,其本色却是追求文辞的美和想象力的表现。而赋的盛行影响了散文的骈偶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成为不胫而走的骈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精细的一种文体,讲究对偶、藻饰、用典、声律,形式华美,一样平常侧重抒怀。骈文在推进文的艺术化、提高其审美代价方面起了很大浸染,但作为一种带有贵族文化特色的文体,它也有自身的弱点,这紧张是形式的拘束太严,不便于作自由活泼的表达,而且随意马虎陷入陈套。再加上骈文较多偏离儒家文化规范,使它更随意马虎受到责怪。
到了唐代,骈文仍旧很盛行,但反对的声音多了起来。进入中唐,遂发生了由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韩愈他们所说的“古文”原是针对当时盛行的“时文”即骈文而言,指先秦两汉时不重骈偶的散体文。后来唐宋“古文”成为狭义的专称,不是泛指“古代文章”;其意义与这一派的理论不雅观点密切干系,其用意一在复兴儒学,一在解放文体。这种“古文”传统又为宋代欧阳修等人所继续。唐宋“古文”在过去常被视为文章的典范,所谓“唐宋八大家”也成为最为人们熟知的习称,但实在这种“古文”也是具有两面性的。从解放文体、规复散体文的主导地位并在客不雅观上造成了骈散结合的趋势这些意义来说,“古文运动”是有主要代价的;但这一运动以“明道”为理论宗旨,将“文”置于对付“道”的寄托性和工具性地位, 也造成很大弊害。至于唐宋“古文”家的创作则较为繁芜,像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都有些不为儒道所拘、富于创造力、颇见个性的精良文章。——苏轼的一些短文,还是晚明小品的来源。
明清时期,唐宋“古文”被推崇为文的正统。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这时候的“古文”已经熏染了浓厚的道学家气味,重“道”而轻“文”的方向加倍强烈。而偏离这一正统的,则以晚明所谓“小品文”为代表。它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标榜,与产生于东南城市工商业经济背景上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密切关联,其风格亦以轻灵巧泼、自由抒发为紧张特点,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某些方面已向当代散文靠拢。它不仅在清代保持着一定影响,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五四季代以及后来的口语散文的创作。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谓“文”原谅范围极广,其面貌亦极为纷繁繁芜。以上只是略举大端,详细情形不可能逐一解释。借用南朝梁代萧绎的话,是所谓“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势推移,属词之体或异”(《内典碑铭集林序》)。
那些古文距我们年代已经久远,笔墨对付不同的读者来说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疏隔,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鉴赏的工具呢?
“鉴赏”按照文艺学理论家的说法,其情形颇为奇妙。从最大略的意义来说,鉴赏总是哀求工具中有可以抚玩、可以引发某种人生感想而带来一定愉悦的东西吧。而这种审美主体受审美工具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按人的办法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有些东西恐怕是难以“鉴赏”的。譬如“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的人们,常须写反省或思想申报请示之类,如果将它们拿给现今的年轻人看,虽然韶光相隔不远,笔墨也随意马虎读懂,却恐怕完备无法理解这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更不用说“鉴赏”了。由于读者实在难以从这里得到一点点“自我享受”。相反,有些文章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却能够被理解和鉴赏。譬如《孟子》里面关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短文,写齐国某男子在外乞讨残食,回到家谎称与富贵者同餐,且做出一副了不起的派头傲视自己的大老婆、小老婆。读者不一定赞许作者借这个故事论说的道理,却能够从文章对“齐人”卑琐可笑的行止的讥刺中体会到对人的肃静的赞颂,倘若遐想到现实环境中某个整日夸耀自己曾同阔人吃过一顿饭或同大人物握过一次手的角色,不免会会心一笑。——这里分明是有些“自我享受”的意味了。
那么,人的“自我享受”的根本是什么呢?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自觉的活动正好便是人类的特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符合这种特性的东西归根结柢是无法被人接管的,个中也就不可能含有可供人们“自我享受”的成分。实在,反省书也是古已有之的,《文选》还收有曹植的《责躬表》(与《责躬诗》一起)。只管他“才高八斗”,文章也写得很俊秀,但他这种不得已的自我羞辱、自我贬损,显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对立物,因而这样的作品仍旧使人讨厌。至于文能够让人喜好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供应给人们由鉴赏而得到的“自我享受”丰富到何种程度。古人的笔墨展开了一个空间,阅读与鉴赏的过程,既是对这一空间中所蕴涵的精神内容的体会,亦是人作为自由的主体对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的验证。而且,由于历史不可重复,某些具有特定时代特色的审美形式、审美履历只能从前代遗籍中得到。换言之,精良的古代文篇,具有扩展和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代价。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排列于韶光流程上的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篇中,我们又看到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及详细个人遭遇下的生活情景与人生神往,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喜怒哀乐、恩仇好恶,它们和当代人的生活感情、艺术意见意义的逐步靠近,这对付本日的读者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通过对古文的阅读和鉴赏,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知识,并在文章写作、语词利用方面得到某些益处,这道理比较大略,就不想多说了。
古文的选本过去有过很多,旧时最盛行确当数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所编选的《古文不雅观止》,这书至今仍拥有很多读者。但以今人的眼力来看,编者的选择标准难免不免偏狭,所作的评注也颇有八股气息。重新编一部原谅范围较广、选择较精、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和评析的《古文鉴赏辞典》,实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本书便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编纂的。由于我国过去的文包括文艺性的与非文艺性的两类(也有非文艺性的作品而含有多少文艺性身分的),前者可供“自我享受”,后者则可借以加强文化素养和提高写作方面的能力,本书的选目和释文都企求只管即便顾及这两个方面。在注释方面,凡从辞书中随意马虎查得的文言词语一样平常不注,以避免噜苏;着重对人名、地名、典故、史实及难解难查的词语作注,冀便读者办理疑难,开卷得益。但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示正。
资料:上海辞书出版社
编辑: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