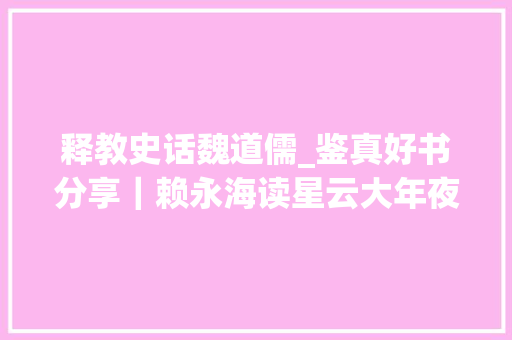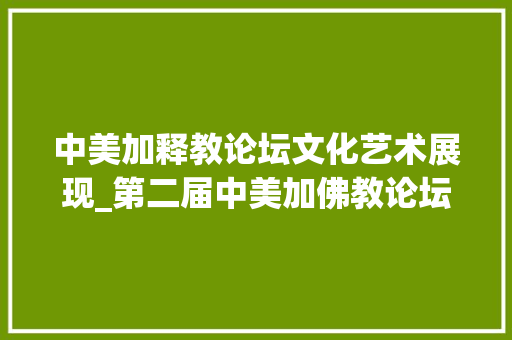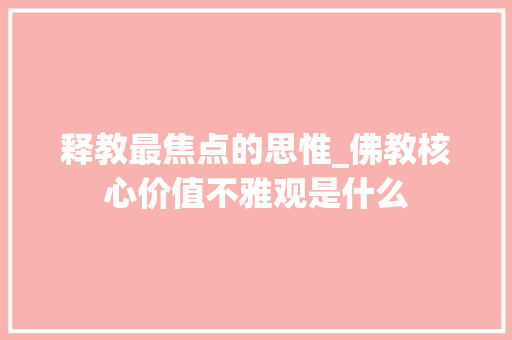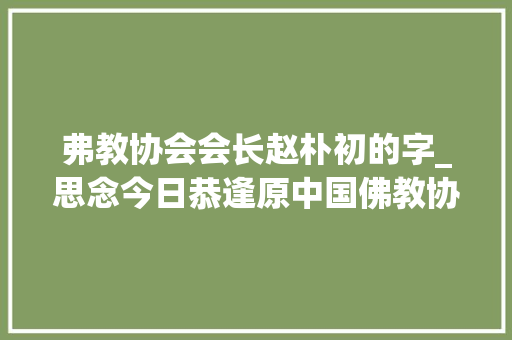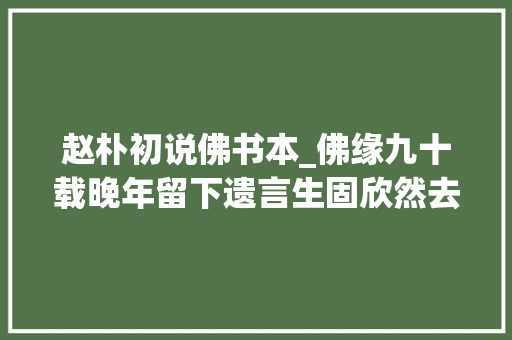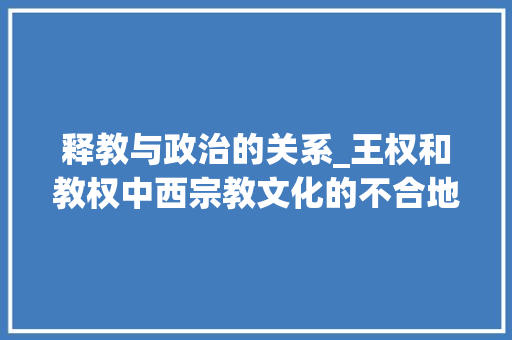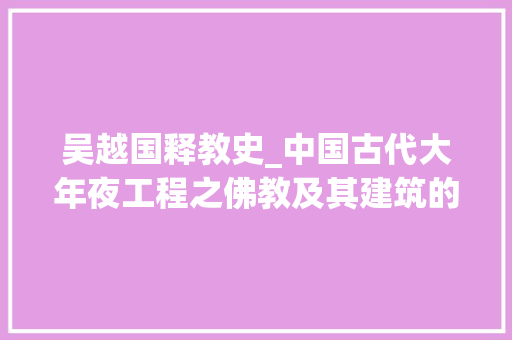当时佛教虽然也在南方的民间广为流传,但是在知识阶层中却遭到了抵触,士大夫们认为儒道乃是中原之术,而佛法却来自戎狄,北方既然已被五胡所乱,那么为了保持中原文化的纯洁性,应该当心佛教会造成变更华俗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徒与传统的士大夫们针对佛教要不要融入中原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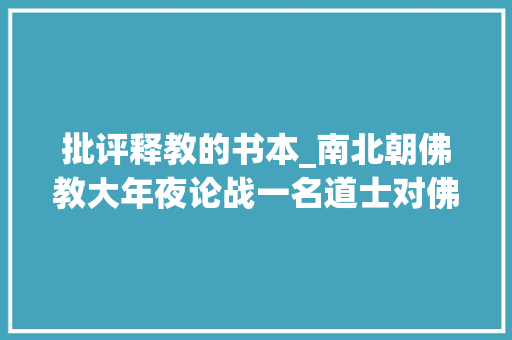
佛教东传
佛教是否须要融入传统的中原文化?东晋时,针对僧人只膜拜佛祖而不向帝王屈膝的做法,曾掀起过一场关于“梵衲不敬王者”的辩论。晋成帝在位时,大臣庾冰想要规复儒学独尊的地位,他向天子奏请说佛教徒弗成膜拜之礼,有碍朝廷的典章制度,应下严令哀求僧人必须膜拜君主;对此,政敌何充武断反对,他认为佛教礼仪与儒家虽有不同,但同样有利于教养百姓、巩固王权。且如今佛教信徒甚重,应尊重其固有的礼仪,不要无事兴做,瞎去折腾。末了晋成帝采纳了何充的建议,许可佛教徒不用行膜拜之礼。
六十二年之后,桓玄官拜太尉,故意篡夺晋室,自为君主。为了确立君主的威信,他调集八座,重提庾冰的“梵衲应敬王者”之论。桓玄对众人说:“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乎视听之外,以敬为本,此出处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表明自己不信佛教、认为其虚幻荒诞的态度,同时又承认佛教也“以敬为本”,具有教养的浸染,乐意尊重这种崇奉,但条件是佛教徒要把稳“恭敬”。他还说:“《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就连玄门徒都知道要尊敬王侯,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佛教徒怎敢唾弃王侯而弗成膜拜之礼呢?且僧人既来中土,享受朝廷给予的恩情,“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朝士名贤对答甚众,纷纭表示反对。彼时僧人慧远写出了五篇《梵衲不敬王者论》,认为佛教以出家、在家为异。在家之时为顺化之民,自应奉亲而敬君,屈服礼法;然而既已出家,则应“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不应再与顺化之民同一而论。梵衲能够“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普度众生,净化风尚,礼敬的办法既然不一,何不各从其俗?
终极,“梵衲应敬王者”之议在佛教徒的抵制下不明晰之。
僧侣是否可以不用膜拜君主?
羽士写的《夷夏论》再次引爆论战到了南朝刘宋期间,佛教猖獗发展已经引发了统治者的担忧。宋文帝在元嘉十二年敕令沙汰梵衲数百人,不准百姓在未经审批的情形下擅自修造寺庙与佛像。其子孝武帝又于大明二年勒令除了苦行僧之外的其他人僧人全部还俗,结果因僧尼交卸后宫妃嫔,使政策未能落地。过了四年,孝武帝指示有司上奏,说儒法分离,名墨殽杂,中国的百家学术虽然相互争鸣,但都同等“崇亲严上”,佛教也应像它们一样服从礼法,敬事王者与双亲。准备逼迫哀求佛教徒遵守礼法,结果也未能成功。
在当时佛教已经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可,唯有朝廷与士大夫阶层出于统治的须要,想哀求佛教徒向王侯将相屈膝,以示尊卑有别。在这种背景下,究竟要不要逼迫佛教徒屈服中华的风尚成了辩论的焦点。为了抵御佛教,儒学与玄门也开始打仗,有相互联合的方向,他们自称为“夏”,而把佛教称为“夷”,欲以传统的夷夏之论来排斥佛教,迫使其做出改变。就在此时,一名奇怪的羽士涌现了,此人名叫顾欢,著有《夷夏论》。
顾欢生于晋朝末年,小时候接管儒家教诲,诵读《孝经》与《论语》。成年后在晒台山开馆聚徒,向学生们传授儒家经典,每次读到《诗经》里的“哀哀父母”时,他都会恸哭堕泪。宋武帝曾征其为扬州主薄,他不愿意出来做官,便回寄一封信,还献上自己删撰的《老子》与《治纲》;宋武帝便赏给他塵尾与素琴,可见此时顾欢已经以隐者自居,并且具有了玄门徒的身份。晚年时,顾欢愈发“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已经从一名儒者转变成了羽士。
针对玄门与佛教相互诋毁的局势,顾欢选择与儒家联手,用孔子的夷夏之论来排斥佛法。他的辩论手段不是直接向佛教开炮、斥其为异端,而是谆谆教导,明面上调和二教之间的抵牾,暗中却左袒玄门。因此被司徒袁粲撰文驳斥,使辩论的焦点转移到是否要调和玄门与佛教的抵牾上来。顾欢主见领悟二教,让“玄门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实际上便是把佛教当做玄门的补充。对此,明僧绍、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等人武断反对,想要正二教之本,不使其混为一谈。竟陵王子良还曾哀求羽士孟景翼星期佛祖,景翼不肯,辩论持续扩大,成为南北朝期间的一场佛教大论战。
一名利用儒家“夷夏之论”来批驳佛教的奇怪羽士
顾欢欲使三教同流,迫使佛教改革在《夷夏论》的开头,顾欢援引《玄妙内篇》和《法华无量寿》的说法,认为老子入关至天竺而化为佛,才使佛教兴起;又说“国师羽士,儒林之宗”,将老庄与周孔并列起来,认为他们是最高的宗师。既然道经说老子化胡,佛经又讲释迦有劫运之数,二者不谋而合,那么“道则佛也,佛则道也。”道与佛在内核上是同等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生于中原,另一个生于戎狄,故而涌现了星期形式上的不同,这是由地理风尚所造成的。
中原之人端委缙绅,全形守礼;戎狄之人断发旷衣,毁貌易性。在这两种不同的风尚下,造成了佛道之间的差异:羽士们束发长袍,礼敬天地,懂得涵养精神,服食妙药,爱护身体以求永生;僧侣们则剃发左衽,顶礼膜拜,通过苦行来修身,神往来世而急迫往生——此乃夷夏之别也。如果生为中原之人,却去学习戎狄之法,不正向陆行坐船、水行乘车一样荒谬么?
因此,羽士与僧侣都须要明白“理之名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的道理,不要在风尚的细枝末节上去创新,而是要捉住二教相同的核心要点,这样才能避免进行无谓的论战、揭橥没用的门户之见。顾欢认为“佛号正真,道称正一”,追求“真”的讲究无生,追求“一”的神往无去世,二者名异而实合,具有互补性。其余,佛经博而繁,道经质而精,佛言实而引,道言实而抑。佛理显而道理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比较于佛教来说,玄门理论过于幽深而难解,故而在民间不能广为流传,应对佛教进行借鉴和吸取。
末了,顾欢做结论说:“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佛教设地狱以劝善,使奸邪不敢胡为;玄门说永生以劝善,使人皆欲修行功德。对付明达之士而言,应该兼收儒释道三教之所长,而不是在详细的风尚差异、礼法分别上做文章。
在顾欢的立论之中,实在隐含这样一个不雅观点:对付佛教基于异俗的礼节,可以尊重,不须要非得哀求“梵衲应敬王者”;而对付佛教的功用,则必须得服从于中国的社会管理,与周孔老庄互助,发挥“破恶”的浸染。
佛教不能一味置出生外,而是要发挥“破恶”的浸染
佛教徒对顾欢的反击,引起论战袁粲读完《夷夏论》后,看出了顾欢的本意。他便托名写了一篇文章进行驳斥,说佛祖出身在老子出关之前,“孔、老、释迦,其人或同,不雅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不能强行附会稠浊。佛教徒已是出家之人,与孔老入世之人早已分道扬镳,何必要强令佛教徒去入世破恶呢?
对此,顾欢在复书中回嘴说道经之书著于两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对付中国人来说,道家自古以来便有,而佛法在数百年后才第一次听到,说佛法比道家早,“是吕尚盗陈桓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的奇谈怪论。既然道家为先入之见,佛教为后来之说,就应以道为本,以佛为末。佛教已经传入了中国,便不再是“鱼鸟异渊,永不干系”,中国人务实经世,不像天竺人一样淡薄出世;如果不对佛法进行改造,令其适应中国本土,而是造搬不改,那跟五胡乱华一样,会使戎狄之俗取代了中原之风。因此,顾欢主见遵守佛教的戒业而摒弃其蛮夷的言貌,并使之与玄门相互合营——“玄门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顾欢的核心主见可以归纳为这么几条:
第一,周孔之儒与老庄之道代表着中原,是“本”,具有兴善的浸染,不能变更其主流地位;
第二,佛教来自异国,存有戎狄之风,是“末”,但它具有破恶的浸染,以是可以进行适度改造与接管;
第三,既然佛教已经传入中土,那么就应承认它的地位,把它当做儒、道的补充,使三教领悟起来。
顾欢已有三教合一的方向
顾欢既反对粗暴地“灭佛”,也反对过分地“崇佛”。他认为佛教可以在中土传播,但条件是它不能取代儒、道的地位,应屈居末节,作为补充,发挥破恶的浸染。在宣扬佛法的时,也须要把稳风尚的差异,不能变华风为夷俗。
比较于守旧的朝廷与士大夫来说,顾欢的不雅观点已经算是较为温和的了。但他“虽同二法,而意党玄门”的做法不能被佛教徒所接管,而且在南北朝时,佞佛的风气是越来越严重的。佛教徒们没有看出《夷夏论》的用意,反而是集中去辩论“玄门与佛教是否殊途同归”的不雅观点,通过《正二教论》、《正一论》之类的文章去教顾欢玄门与佛教有哪些不同的大略道理。
在封建社会中,佛教徒不敢主见独尊佛教、罢黜儒学的不雅观点,以是《夷夏论》中以“儒道为本,佛法为末”的的不雅观点才没有进一步展开辩论,论战的重心被转移到了无关紧要的地方,收入《弘明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