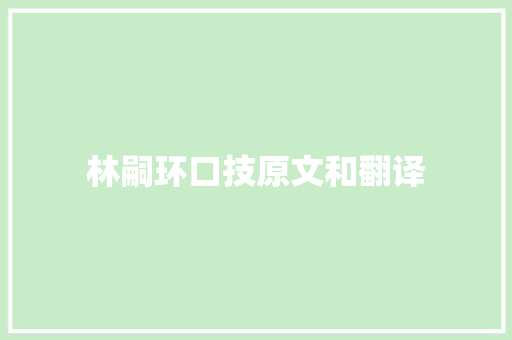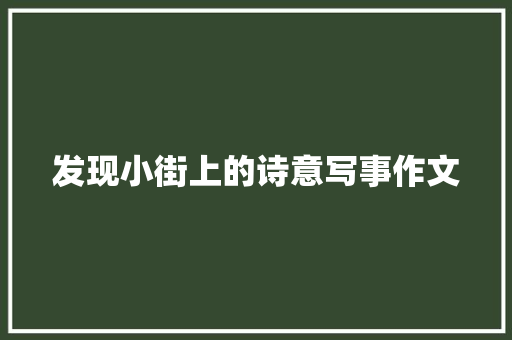原文: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早孤,绝慧,十四入泮。母最爱之,寻常不令游郊野。聘萧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会上元,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游。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去数武,顾婢子笑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母忧之,醮禳益剧,肌革锐减。医师诊视,投剂发表,忽忽若迷。母抚问所由,默然不答。适吴生来,嘱秘诘之。吴至榻前,生见之泪下,吴就榻慰解,渐致研诘,生具吐其实,且求谋画。吴笑曰:“君意亦痴!此愿有何难遂?当代访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谐矣,不然,拚以重赂,计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闻之不觉解颐。吴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访既穷,并无踪迹。母大忧,无所为计。然自吴去后,颜顿开,食亦略进。数日吴复来,生问所谋。吴绐之曰:“已得之矣。我以为谁何人,乃我姑之女,即君姨妹,今尚待聘。虽内戚有婚姻之嫌,实告之无不谐者。”生喜溢眉宇,问:“居何里?”吴诡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生又嘱再四,吴锐身自任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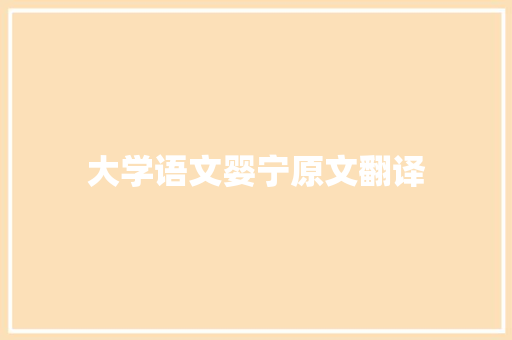
生由是饮食渐加,日就平复。探视枕底,花虽枯,未便雕落,凝思把玩,如见其人。怪吴不至,折柬招之,吴支托不肯赴招。生恚怒,悒悒不欢。母虑其复病,急为议姻,略与商榷,辄摇首不愿,惟日盼吴。吴迄无耗,益怨恨之。转思三十里非遥,何必仰息他人?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意其园亭,不敢遽入。回顾对户,有巨石滑洁,因坐少憩。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方伫听间,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审视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骤喜,但念无以阶进。欲呼姨氏,顾从无还往,惧有讹误。门内无人可问,坐卧徘徊,自朝至于日昃,盈盈望断,并忘饥渴。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似讶其不去者。忽一老媪扶杖出,顾生曰:“何处郎君,闻自辰刻来,以至于今。意将何为?得勿饥也?”生急起揖之,答云:“将以探亲。”媪聋聩不闻。又大言之。乃问:“贵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我视郎君亦书痴耳。不如从我来,啖以粗粝,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归,询知姓氏,再来探访。”生方腹馁思啖,又从此渐近丽人,大喜。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如明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裀藉几榻,罔不洁泽。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媪唤:“小荣!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嗷声而应。坐次,具展宗阀。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吴否?”曰:“然。”媪惊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来以家屡贫,又无三尺之男,遂至音问梗塞。甥长成如许,尚不相识。”生曰:“此来即为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并无诞育,弱息亦为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颇亦不钝,但少教训,嬉不知愁。少顷,使来拜识。”未几婢子具饭,雏尾盈握。媪劝餐已,婢来敛具。媪曰:“唤宁姑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瞶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婴儿。”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答曰:“无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媪亦起,唤婢襆被,为生安置。曰:“阿甥来不易,宜留三五日,迟迟送汝归。如嫌幽闷,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有书可读。”
译文:
王子服,莒县罗店人。父亲很早就死去。他非常聪明,十四岁考取秀才,入泮宫读书。母亲最钟爱他,平常不让他到郊野游玩。聘定萧氏为妻,还没嫁过来就死去,所以王子服求偶未成。恰逢正月十五上元节,舅舅的儿子吴生,邀王子服同去游玩。刚刚到村外,舅舅家有仆人来,把吴生叫走了。王生见游女多得像天上的云彩,于是乘着兴致一个人到处游玩。有个女郎带着婢女,手拿一枝梅花,容貌绝美,笑容可掬。王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女郎,竟然忘记了顾忌。女郎走过去几步,看着婢女笑着说:“这个年青人目光灼灼像贼!”把花丢在地上,说说笑笑地离开了。王生拾起花来神情惆怅,像是神魂都丢掉了,于是怏怏地回家。到了家里,把拾来的花藏到枕头底下,倒头就睡,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母亲为他担忧,请和尚道士施法以消灾祛邪,病情反而加剧。身体很快消瘦下去。医师来诊视,让他吃药发散体内的邪火,王生更恍恍忽忽,像是被什么逮住了。母亲细细地问王生得病的来由,他默默地不作回答。恰好吴生来,王母嘱咐他细细盘问王生。吴生到王生榻前,王生见到他就流下泪来。吴生靠近床榻劝解安慰王生,渐渐开始细问。王生把实情全说出来,而且求吴生代为谋划。吴生笑着说:“你的心意也太痴了,这个愿望有什么难以实现?我将代你访求她。在郊野徒步行走一定不是显贵家族。假如她尚未许配人家,事情就一定成功;不然的话,拼着拿出众多的财物,估计一定会答应。只要你病愈,成事包在我身上。”王生听了这番话,不觉开颜而笑。吴生出去告诉王母,寻找那女子居住的地方,但探访穷尽,一点踪迹也没有。王母十分忧虑,拿不出什么主意。但是自吴生离开后,王生的愁容顿开,吃饭也略有长进。几天之后,吴生又来了。王生问谋划的事办得如何,吴生欺骗王生说:“已经找到了。我以为是什么人,原来是我姑姑的女儿,就是你的姨表妹,现在还在等人聘定。虽然是家中亲戚婚姻有些隔碍,但以实情告诉他们,一定会成功。”王生高兴的神色充满眉宇间,问吴生说:“住在什么地方?”吴生哄骗说:“住在西南山中,距这里大约三十余里。”王生又再三再四嘱托吴生,吴生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下来。
王生从此之后饮食渐渐增加,身体一天一天地恢复。看看枕头底下,花虽然干枯了,还没有凋落,细细地拿在手上赏玩,如同见到了那个人。吴生不来他感到奇怪,写信叫吴生来。吴生支吾推托不肯赴召。王生因怒恨而生气,心情悒郁,很不高兴。王母担心他又生病,急着为他选择女子作妻,稍微和他一商量,他总是摇头不答应。只是每天盼着吴生。吴生最终没有消息,王生更加怨恨他。转而又想,三十里地并不遥远,为什么一定要仰仗别人?于是把梅花放在袖中,赌气自己去西南山中寻找,家中人却不知道。王生孤零零地一个人走,没有人可以问路,只是朝着南山走去。大约走了三十余里,群山重叠聚集,满山绿树,空气新鲜,感觉特别清爽,四周安静,一个行人也没有,只有险峻狭窄的山路。远远望见谷底,在丛花群树中,隐隐约约有小的村落。走下山进入树林,见到房屋不多,都是茅屋,而环境十分幽雅。向北的一家,门前都种着柳树,院墙内桃花杏花还开得很繁茂,夹杂着几株美竹,野鸟在其中鸣叫。猜想是人家园房,不敢贸然进去。回头看着,对着门有块石头平滑而光洁,就坐在石头稍事休息。不久听见墙内有女予高声叫“小荣”,声音娇细。正在静心听的时候,有一女子由东向西,手执一朵杏花,低着头自己想把花簪在头上;抬头看见王生,于是就不再簪花,含笑拿着花走进门去。王生仔细一看,这女子就是上元节时在途中遇见的。心中非常高兴,但是想到找不到关系门路进去;想喊姨,只是从来没有来往,害怕有讹误。门内又无人可问,坐立不安,来回徘徊,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眼光顾盼,几乎要望穿,连饥渴都忘了。时时望见女子露出半个面孔来窥看他,似乎是惊讶他久不离去。忽然一位老妇扶着拐杖出来,看看王生说:“你是哪里的年青人,听说你从早上辰时就来了,直到现在,你想要干什么?不会肚子饿吗?”王生赶忙起来行揖礼,回答说:“将在这儿等亲戚。”老妇人耳聋没听见。王生又大声说了一遍。老妇人于是问:“你的亲戚姓什么?”王生回答不出来。老妇人笑着说:“奇怪啊!姓名尚且不知道,怎么能探亲?我看你这年青人,只不过是书痴罢了。不如跟我来,吃点粗米饭,家里有短榻可以睡,到明天早上回去,问清楚姓名,再来探访,也不晚。”王生正肚子饿,想吃饭,又因为从这以后渐渐接近那美丽女子,非常高兴。跟从老妇人进去,见到门内白石铺成的路,路两边树上开着红花,一片一片坠落台阶上。顺着路曲折转朝西边,又打开一扇门,豆棚花架布满庭中。老妇人恭敬地请客人进入房舍,四壁泛白,光亮如镜;窗外海棠树,枝条带花伸入屋子里;垫褥坐席,茶几坐榻,样样都非常洁净光亮。刚刚坐下,就有人从窗外隐约窥看。老妇人叫道:“小荣,赶快吃饭。”外面有婢女高声答应。对坐的时候,详细介绍家族门第。老妇人说:“你的外祖父,是不是姓吴?”王生说:“是的。”老妇人吃惊地说:“你是我的外甥!你母亲,是我妹妹。近年来因为家境贫寒,又没男孩子,于是致使相互之间消息阻隔。外甥长成这么大,还不认识。”王生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姨,匆忙当中忘了姓名。”老妇人说:“我姓秦,没有生育,只有一个小女儿,也是妾生的。她的母亲改嫁了,留下来给我抚养,人也不算愚钝;只是教育太少,喜嬉闹,不知道忧愁。过一会儿,叫她来拜见你认识你。”没有多久,婢女准备好了饭,鸡鸭又肥又大。老妇人不断地劝王生多吃,吃完饭后,婢女来收拾餐具。老妇人说:“叫宁姑来。”婢女答应着离开。过了不久,听到门外隐隐约约有笑声。老女人又唤道:“婴宁!你的姨表兄在这里。”门外嗤嗤的笑声不止。婢女推着婴宁进门,婴宁还掩住自己的口,笑声不能遏止。老妇人瞪着眼睛说:“有客人在,嘻嘻哈哈,成什么样子!”婴宁忍住笑站着,王生向婴宁行揖礼。老妇人说:“这是王生,是你姨的儿子。一家人尚且互不相识,真是让人好笑。”王生问:“妹子有多大年纪?”老妇人没有听清,王生又说了一遍。婴宁又笑起来,笑得俯下身子,头都没法抬起来。老妇人对王生说:“我说教育太少,由此可见了。年纪已经十六岁,呆呆傻傻像个婴儿。”王生说:“比我小一岁。”老妇人说;“外甥已经十七岁了,莫非是庚年子出生,属马的?”王生点头说是。又问:“外甥熄妇是谁?”王生回答说:“还没有。”老妇人说:“像外甥这样的才貌,怎么十七岁还没有聘定妻室呢?婴宁也还没有婆家,你两人非常相匹配,可惜因为是内亲有隔碍。”王生没作声,眼睛注视着婴宁,一动也不动,根本无暇看别的地方。婢女向婴宁小声说:“眼光灼灼,贼的样子没有改变。”婴宁又大笑,回过头对婢女说:“去看看碧桃花开了没有?”赶快站起来,用袖子掩住口,用细碎急促的步子走出门。到了门外,才纵声大笑。老妇人也起身,叫女仆铺设被褥,为王生安排住的地方,说:“外甥来这儿不容易,应当留住三五天,慢慢再送你回去。如果嫌幽闷,房屋后面有小园可供你消遣,也有书可供长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