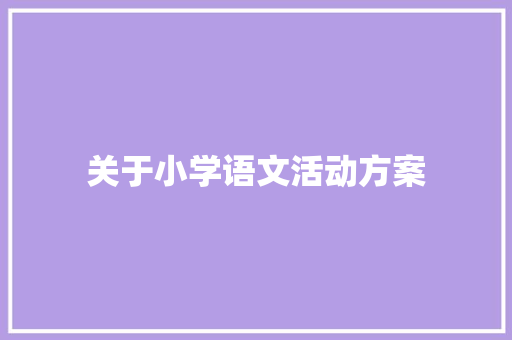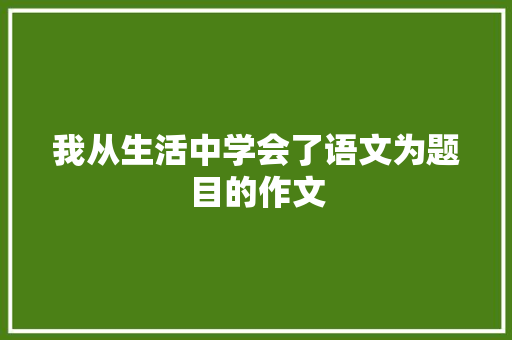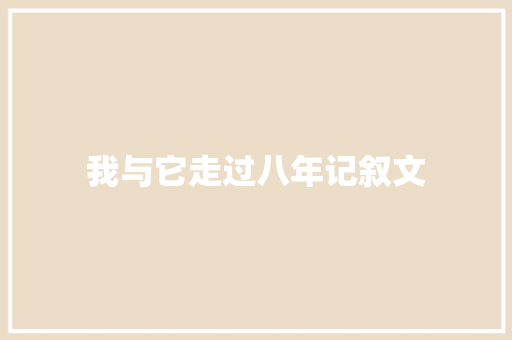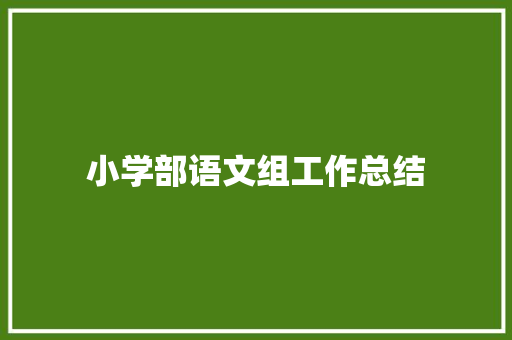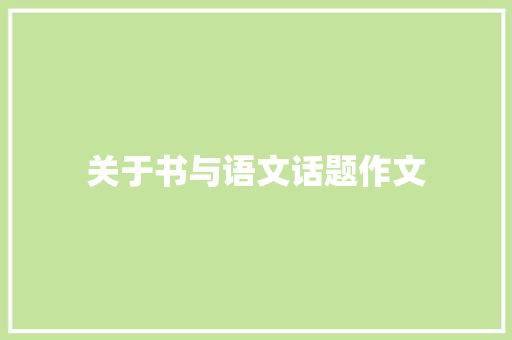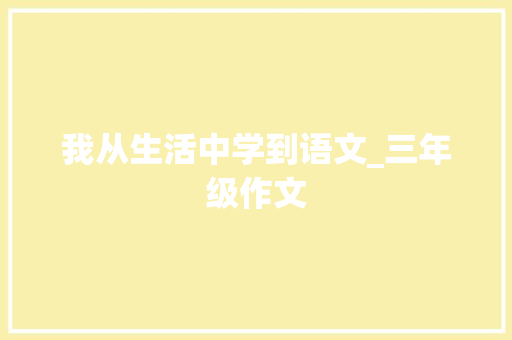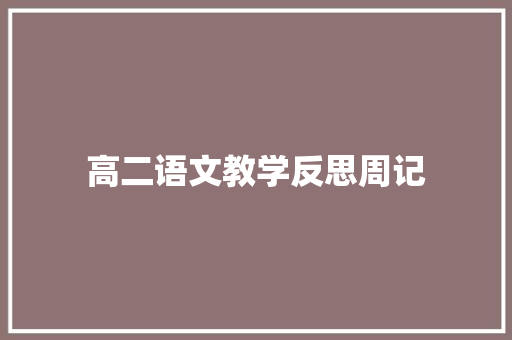语文是什么? 多年来,我们总想给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这是语文的核心理论,若有谬误,将给课程实施带来无穷麻烦。经过反复争论和权衡,终于,新课标一锤定音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于是,语文界皆大欢喜,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就天下太平。可是,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问题一个个出来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指什么?语文课怎样上才能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又怎样才能实现统一?统一的标准在哪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定性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语文教什么的问题,因此,许多教师仍处在不知语文教什么的迷雾之中,教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语文、泛语文、反语文的非理性倾向。虽然新课标对课程目标和学习方式、方法等做了较好的论述,但与存在的问题比起来,这些亮点也都显得黯谈
出现这么多问题,的确是始料不及的。我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工具性、人文性这两个舶来品与我们的汉语文不那么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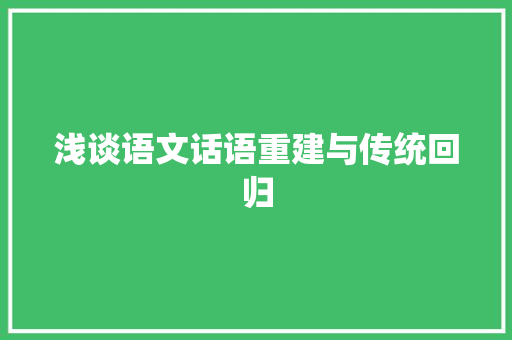
工具性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法同启蒙思想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都曾提到语言的士具属性。最为我国学人熟悉和信奉的是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语言是士具,是武器,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话语。其后,我同的语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就接过了工具论的说法,奉为圭臬,再也放不下来。其实,工具性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人是语言的动物,人具有语言性;而语言是人独有的天性,语言也具有人性,因此,属人性质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而我们将这不是语言本质属性的工具性拿来作为汉语文的性质,怎么能不出问题?
至于“人文性”,虽然我国古代的《易》“观乎天问,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有 人文词,但这人文是与天文相对,指的是人世间的各种现象,与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好像没什么关系。人文性来自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它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打出的一面鲜亮的思想旗帜,是体现那个特定历史阶段进程的进步文化思潮,用它来概括汉语文的特点是否合适,也是值得研究的。当然,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结果,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它毕竟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用它来概括汉语文的特点,总给人以用西方观念来套用的感觉。汉语文的特点还是应该从汉语语言学、汉语文章学和汉语文艺学的实际来考察,为什么一定要搬用西方人的概念?我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的是仁政、民本思想,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从孔子的仁者爱人、诗可以怨,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与民间乐;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沸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钟荣提倡的建安风骨;从李白的济苍生、安黎元至杜甫的三吏、三别,再到白居易的救济人病,禅补时阙;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苏轼的言必中当世之过,再到李费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这种追求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反对压迫抨击黑暗的抗争精神,贯穿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这就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主要精神和光辉传统,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用西方的观念来概括汉语文的特性呢?
工具性和人文性这两个舶来品都不是汉语文的内在属性,都是外在于汉语文的属性,外在于汉语文的属性当然不能统一在汉语文之内。所以,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个想当然的命题。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也证明了它们离汉语文很远。比如谁说话、写文章想到了什么工具性?谁又想到了要表达什么人文性?说话、写文章,首先想到的是用什么样的言来表达自己的心中之意一一 心意、情意、意见、意思、意图、意志、意愿、意念、意趣等等。因为它们是生硬移植来的洋玩意,不服我们汉语文的水士!难道我们的汉语文就没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的话语系统吗?难道我们的汉语文真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