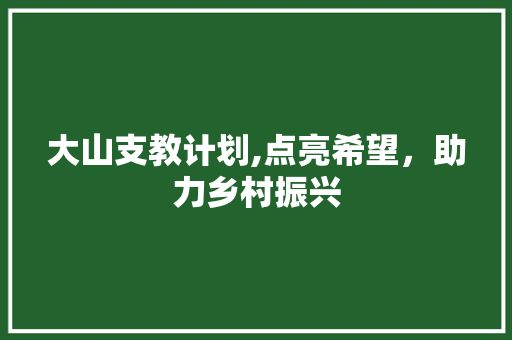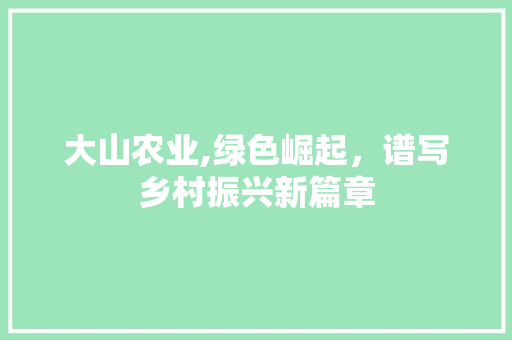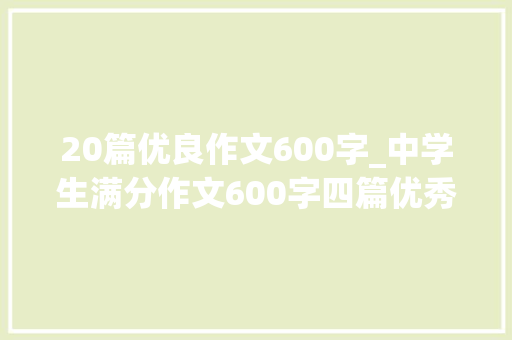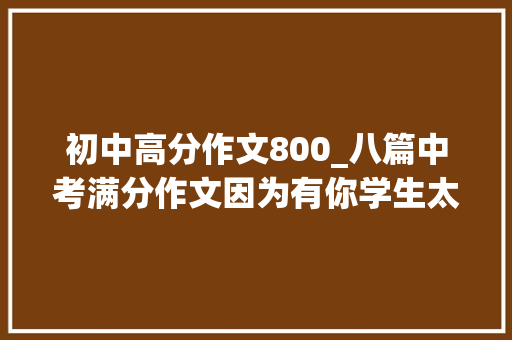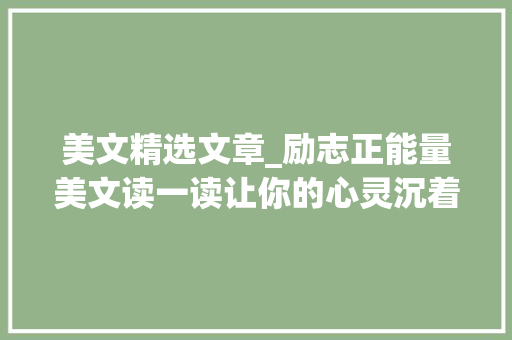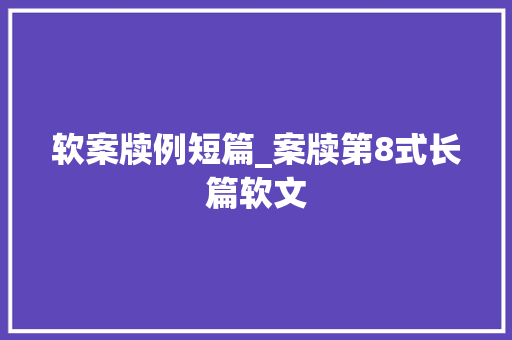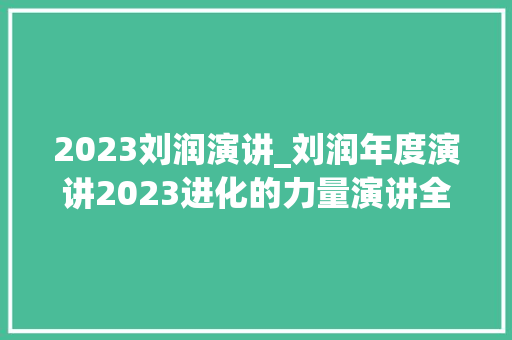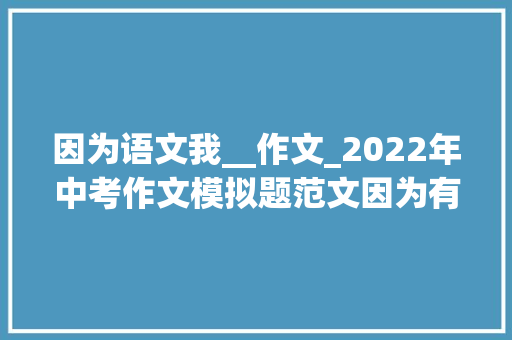那年,父亲外出谋生,年幼的我和姐姐与母亲相依为生,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就圈好了羊群,栓好了狗,坐等入夜。
年幼的我们总是对阴郁充满了恐怖,等天一黑,无尽的大山就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巨人,每当看到这一情景,我的心就开始恐怖起来,这时,母亲就会点起一盏油灯,灯光很微弱的摇荡在阴郁里,我则寸步不离那盏油灯,等她把统统整顿妥当,就会过来陪我们一起守着灯光,她会诉说故事,会逗我们愉快,会让我们忘掉恐怖,然后逐步进入梦乡,当我进入梦乡的时候,母亲就悄无声息的熄灭了灯,一个人在阴郁里辗转反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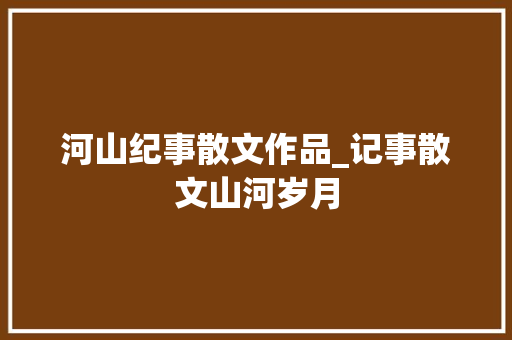
我时常站在屋后那个大石上向远处守望,由于孤独,心里总渴望远处会走来一个许久未归的亲人 ,带给我未曾见过的礼物,还有让我垂涎已久的小吃,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涌现过,我每次都是失落落而归,但并没有把这个想法见告给母亲和姐姐,由于怕他们取笑。
日子久了,这份希望自然破灭,我始终没等到那个安慰,只见一座座大山层层遮挡,巍然耸立。
我每天游走于山间,牵着那头老牛,数着漫长的日子,奈何这份孤独,伴随了我全体童年,只惜年幼,尚不能征服千重山,踏过万里路。
我在寂寞里发展,风风雨雨,许多印象都开始模糊,多年后,尚能忆起母亲为我们点燃的那盏灯,某年某月某日,深山寒屋.....
我记得在某个夏日的午后,我放学回家,吃完一些剩饭,准备上学去的的时候,听见母亲又在和姐姐争吵,由于家里穷,只能坚持一个人的上学费用,由于家里须要劳力,来分担父母沉重的包袱,也由于姐姐是个女孩,迟早要嫁人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上那么多学没用,于是母亲天经地义的停了成绩精良的姐姐的作业,由她卖力看放家里那一群羊,而我,则连续在村落里唯一的小学堂里读书。
由于少不更事,我天经地义的接管了这份美差,每天上学放学。我有一帮很好的玩伴,有一个可以当做梦想来憧憬的未来,那便是好好学习,将来走出大山,走入想象中的繁华都邑,开启另一种人生。
今后,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或者听到姐姐在哭,想象一下,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小姑娘,每天赶着一群羊,游走在大大小小的山谷里,她须要多大的勇气,去面对那种孤独,那种寂寞无助,那种大自然的沉默带给她无尽的恐怖感。
各类觉得我当时是无法体会的,我乃至不止一次的嘲笑作弄她,笑她胆小,怨她老惹母亲生气,纵然没有作业的时候,我乃至直接谢绝她哀求我陪她一起去深山放羊的要求,而是去找那些玩伴一块玩耍。
我无法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只是记得她哭得很伤心,赶着羊群的背影是那样弱小无助,那样无可奈何,我乃至不愿想象当她一个人步入深山时如何排解那种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寂寞,如何面对群山压抑下的那种恐怖,如何看好那些不听话的羊群,以防他们走失落。我只是去找伙伴玩耍去了,下河抓鱼,上山摘野果,玩游戏,捉迷藏,好烦懑乐。
日子不紧不慢的过着,刮风下雨,炎炎烈日,滔滔山洪,茂密丛林,幽暗峡谷,所有搜罗万象的场景里,我都能想起一个弱小的女孩,赶着白色的羊群走过,她的寂寞我不懂,她的失落落我不懂,她的苦楚我更不懂,我只是在等,等自己快些终年夜,等自己有一天长出翅膀,就像那时常翱翔在山顶的雄鹰那样,飞的高,看得远,摆脱这梦魇一样平常的大山,摆脱这梦魇一样平常的生活。
我好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天下,每当我爬上自以为最高的山顶时,看到的却是更高的选山,更远的迷茫,我一次又一次的败给了自己,败给了将我层层包裹的群山。
今后,我的童年,变得支离破碎,活着的艰辛,父母肩上沉重的苦难,姐姐的伤心.....我一每天的发展起来,坎坎坷坷,一起走得非常艰辛,到了本日, 依然做个平凡的小角色,躲在平常的小角落,过着平淡的小生活....
我想发迹乡老屋门前的那棵树,树下的那块巨石,也曾是我的居住之处,在没有事干的时候,我就躺在石头上仰望蓝天,窃听风云。
再次来到此地,老树已成枯木,腐烂难辨了,唯有那块石头,悄悄的侧身躺着,未曾偏离一点方位。
我仰身其上,舒活筋骨,那蓝天云海,那绿水青山,在我心中,再也没了尽头,彷佛要无限延伸这个天下的宽广,苍茫之间,早已倦怠的心,随着那条奔流不息的河随波逐流。盲目的激情,一起上随着雀跃欢呼!
恍惚如那人流,来时路上并不知要去向何方......
闲适之中,看风景秀美如画,画虽未尽人意,却尽天籁。梦若能入一种意境,醒便是一种超脱,等看淡了世俗,也看清了自己。降服不了自己,就永久摆脱不掉所谓的‘世俗’…
石头无才,也无心,谈不上百年沉睡,千年寂寞;高山流水的情殇,于我心,或许真能泛滥成伤,由于凡人的心是薄弱的,经不起沉沦与颠覆......
山阴小道,应接不暇。实在,我只是过客,而并非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