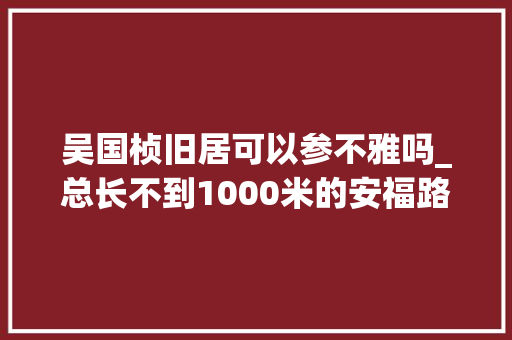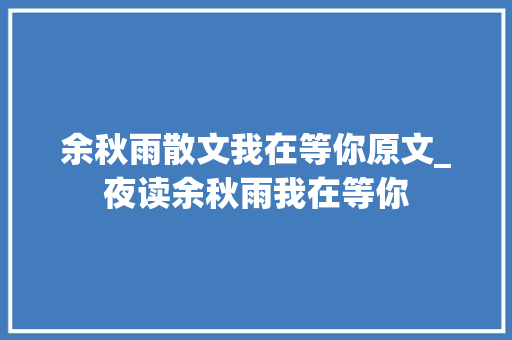我的读书体会,是看书学习要多向名家名著求教。这些曾经产生过学术影响的东西,总有它的上风和值得学习的地方。戏剧领域也不例外。我阅读的戏剧著作,可能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看过,但有些书是值得反复阅读反复体会,碰着问题时,拿出书来对照读,这样的感想熏染与纯挚地阅读浏览是不一样的。首先是《焦菊隐戏剧论文集》(华文出版社)、黄佐临的《我与写意戏剧不雅观》(中国戏剧出版社)和阿甲的《戏剧演出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前两位是话剧导演,后一位是戏曲导演。前两位导演,一位留法,一位留英,他们在总结自己的话剧舞台履历时,都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性,哀求多看多读文学原著,熟习和理解文学作品人物,尊重文学作品的原貌,领会作家作品的精神。他们同时又很把稳话剧艺术自身的特点,强调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不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舞台艺术的演出特点加以取舍。话剧艺术是舶来品,根基浅,积累少,随意马虎被人牵着鼻子走、洋腔洋调,流于“话剧腔”的形式主义泥潭。以是,焦菊隐、黄佐临等艺术家们始终都在探索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出路,希望话剧能够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去。他们不谋而合地把稳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精良传统,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有强大的生命力。
焦菊隐师长西席反复强调话剧要学习中国传统戏曲表现手腕。黄佐临师长西席总结中国戏曲的写意特点,在话剧领域最早提出“写意戏剧不雅观”。其他像欧阳予倩、田汉等也教诲话剧演员要多向中国戏曲学习。阿甲是著名戏曲导演,京剧《红灯记》等,都是他导的。他在《戏曲演出论集》中,有不少文章是总结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特色和舞台履历的,由于他有实践有思考,有长期的舞台导演积累,以是,一些文章意味深长很耐读。像《论莫成的悲剧——一段戏的导演剖析》、《体验和技巧》、《戏曲导演事情中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戏曲学院导演学习班上的报告》和《我们若何排练京剧<白毛女>》等,在思考了传统戏曲的局限和特色、比拟了话剧艺术的上风和不敷之后,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戏剧的意见,这给我们本日学习和理解中国传统戏曲供应了宝贵的履历。《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和《李健吾传》,值得负责读。李健吾是中国戏剧领域的大家,在创作、翻译、评论和演出上都做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1945年发起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这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1949年后,他是第一任戏文系主任,直到1952年离开上海,到何其芳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事情,1982年逝世。有关他的情形,我阅读了韩石山师长西席的《李健吾传》,这本书材料丰富,对我们理解李健吾师长西席的贡献有帮助。我曾到上戏档案室去查看过李健吾的档案,可惜留下的东西不多。我读李健吾的书,感触良多,他的笔墨不像焦菊隐、黄佐临那样明晰清楚,但敏感灵动,一如他的文学批评。像他评老舍的《茶馆》,对曹禺《雷雨》的批评和对夏衍《上海屋檐下》的推举,都让人有线人一新的觉得。他谈戏剧改编,也有很好的见地。李健吾的戏剧评论最大的特色是笔墨干净利索,没有一丝一毫的媚俗味,这是职业批评家应有的品质和素养,也是本日的戏剧评论家该当向李健吾师长西席学习的地方。其余有几本中国当代剧作家谈创作的书,值得看。如《老舍论创作》《曹禺论创作》和《夏衍论创作》,这套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代出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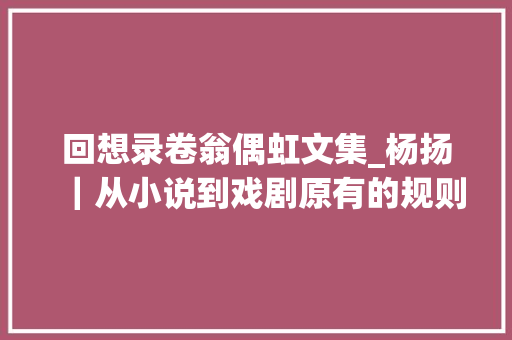
曹禺、夏衍和老舍都是著名的剧作家,他们首创了中国当代话剧的三种剧作模式。一种是严格的三一律戏剧,像曹禺《雷雨》的时空构培养是,自成一体,结实紧凑,戏剧冲突强,电光雷鸣,一气呵成。还有一种是时空切割,分割成多个碎片的戏剧构造,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五户人家,五个小空间,很家常,很平淡。但这种平淡就像精良的散文作品一样,有一种淡淡的诗意,正如别林斯基盛赞的“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了作者过人的才华”,五个不同的小空间像镜子一样相互照射,在舞台上散发出五光十色的戏剧光彩。其余一种是“图卷戏”构造,这是李健吾师长西席对话剧《茶馆》的经典概括 。这三种话剧模式为什么会在这三位剧作家手中出身,对照他们的剧作,体会他们的戏剧创作履历,再结合他们的个人传记,我感到有很多值得玩味之处。以往做学术研究,强调根基要正,学问要有来历,实在放到这些剧作家身上,何尝没有文学文化上的来历和渊源呢?通过研读这些剧作家的创作谈,让我遐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大师之后,很少有剧作家能够超越他们?文学文化教化和履历积累实在便是一道分水岭。
老舍从上世纪20年代揭橥第一篇小说,到1957年揭橥《茶馆》,期间经历了30年韶光,这中间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落败教训,但他长于不断摸索、总结,终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曹禺的女儿万方亲耳听到曹禺对采访者说:“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心血啊!
心血这东西,是多少年的履历,多少年的思想情绪里渗透出来的。”这些当代剧作家的写作履历,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也是本日很多从业者值得吸取的履历。当代剧作家中,我喜好读《翁偶虹戏曲论文集》、汪曾祺的《晚翠文谈新编》。这两位都是戏曲名家。翁偶虹师长西席生平创作、改编戏曲作品一百多部,个中编剧的《锁麟囊》经由程砚秋师长西席排演后,成为程派京剧的代表作品。翁师长西席晚年还担当京剧《红灯记》的编剧。他在总结自己的编剧履历时说:“由于一个有时的机会,供职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耳闻目接,无时非戏,无处非戏,从此就置身于戏曲圈中,奠定了以编剧为终生职业的根本。”(《翁偶虹文集·回顾录卷》)汪曾祺师长西席虽然以小说、散文创作名世,但他后半生是在北京京剧团度过的,他改编的京剧《沙家浜》,个中的一些唱段,至今受到追捧。汪曾祺认为外国戏剧的构造模式有点像山,威武森严、非常结实,而中国的戏曲构造像水,滔滔不绝、委婉弯曲,有点靠近小说的叙事风格。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小说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拜会汪曾祺《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读他们的戏曲文章,给人的启示是不一般的。这个不一般便是他们都是戏曲领域的里手里手,对戏曲熟习。他们谈问题,不是先先容某种理论,再依照理论的哀求来展开问题。他们总是依照自己的欣赏习气和戏曲传统特点,谈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意见。他们论述问题,清楚明白,从容不迫,从不野蛮无理,也不故作姿态。笔墨上,挥洒自如,很有风采。
外国戏剧方面,我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这是杨衍春师长西席的译本,笔墨顺畅,意思明白,胜于别的译本。这本书以前读过,由于涉及到很多戏剧演出方面的知识,自己不熟习,初读会以为有点零星和繁琐,抓不住要点。现在逐步读下来,尤其是对照契诃夫戏剧演出,感到有所收益。我仿佛是在亲耳聆听一位戏剧理论大师谈自己的思想发展经历,他让我明白戏剧之路并不平坦,戏剧探索永无止境。他的困惑、他的视野、他的奇迹的立足点和他的进取目标的选择,都是一步一步由低到高慢慢取得的,像涓涓细流,一点一滴,终极汇成了汪洋大海。他的讲述让我想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世时,天下上有那么多出色的演艺剧团、那么多精良的艺人,但为什么只有斯坦尼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宗师呢?我以为与他交往的职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除了与演员、剧团交往外,还与很多天下级的文学大师交往,像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梅特林克、高尔基等,这些文学家加深了斯坦尼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思考。换句话说,我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中,体会到了戏剧理论的思考不是伶仃的,而是与文学等艺术门类举一反三。譬如如何来解读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如何来剖析戏剧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情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这些文学大师的交往中,获益良多,由于这些文学大师对人性的理解、对文学人物性情的理解,都是凡人所难以抵达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通过与他们的互换,直接启示了他对戏剧理论和戏剧人物的思考。当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解读办法不一定穷尽了当时戏剧理论的所有问题,但与同时期的戏剧家们比较,他的视野和思考的问题都具有划时期的意义,表现出大师的风范和深邃的理论探索眼力。中心戏剧学院导演系姜涛老师的《斯氏体系在中国》(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容了斯坦尼体系在中国的传播情形,给我们理解斯坦尼体系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及其得失落,供应了一壁历史参照镜子。布莱希特的《戏剧小工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他的戏剧论文集,不仅表达了他对戏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显示了德国戏剧的理论思考深度。对他的戏剧理论,中国很多戏剧人都熟习。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戏剧理论思考与德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我读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的回顾录《哲学生涯:我的回顾》,个中记录了他与布莱希特以及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密切交往情形。我不知道中国的戏剧家是不是与哲学家有过类似的密切交往关系,但布莱希特与哲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使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思考得到了方法论上的帮助,同时也给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哲学家们以艺术创造的灵感,换句话说,德国戏剧的理论打破,不是局限于戏剧领域,而是与哲学、文学同步展开。海内先容布莱希特一样平常都比较看重“间隔理论”、“陌生化”等,但我想他的这种创造动力的哲学来源该当引起广泛的把稳,这是海内戏剧理论创新中最缺少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哲学方法论问题是他的戏剧探索的理论驱动力。德国戏剧之以是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个华夏因之一是它总有一种不知足于现状的理论冲动,希望理论跑到戏剧实践前面,给戏剧探索供应某种不雅观念上的支持。这种传统,或许与他们跟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
其他三本书,可能与现在盛行的后当代戏剧有点渊源关系。格洛托夫斯基的《迈向朴实的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中国友情出版社)和汉斯-蒂斯·雷曼的《后戏剧戏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三本书让我想到“戏剧构作”的主体行为问题。在西方影视工业的冲击下,作甚戏剧,戏剧作甚,不仅是戏剧实践领域中一个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也是戏剧理论领域须要办理的戏剧合法性问题。三本书的理论主见之间明显有某种关联,在眼花缭乱的变革面前,他们都向自己提出最基本的问题——所有这些变革都是戏剧所须要的吗?离开了这些,尤其是过度奢华的舞美(格洛托夫斯基称之为没有主体的“富余戏剧”),戏剧还能够坚持吗?但我以为这些思考的实践性指向比它的理论思考更故意义。戏剧该当如何来建构?是连续依照剧作家作品的预设,在舞台上不断重复展示,还是让导演、演员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将统统有益于舞台呈现的东西,参与到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上来?这在理论层面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舞台实践上,却是无法回避并随意马虎引发辩论的问题。
2020年底至今,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环球演艺市场普遍受到冲击,国外来华演出项目被迫中断。随着海内疫景况态得到掌握,从2021年2月开始,上海话剧市场逐渐规复、回暖。上演了一些话剧剧目。个中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的《狂人日记》、胡宗琪导演的《尘埃落定》和周小倩导演的《长恨歌》引来较大的社会反响。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研究中央曾与《狂人日记》剧组和《尘埃落定》剧组分别举办过两次研讨会,谈论干系的理论问题。这三部话剧集中表示了当代话剧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便是从改编小说开始。《狂人日记》是波兰导演陆帕根据鲁迅师长西席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此前他根据史铁生的小说改编成话剧《酗酒者莫非》,这次陆帕改编鲁迅的作品,并强化了他的中国意识。他将戏剧《狂人日记》取名为“中国三部曲之二”(第三部作品将是改编王小波的小说)。周小倩导演的话剧《长恨歌》是根据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来,剧本由上海戏剧学院赵耀民任编剧,2003年首演,苏乐慈总导演,今年是复排。胡宗琪导演的《尘埃落定》是根据阿来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编剧由上海戏剧学院曹路生教授担当,这次为首轮巡演。三部文学作品篇幅不同。《狂人日记》原作4700字,听说陆帕的执导条记达60万字,剧目演出长达四个半小时。小说《长恨歌》原作30万字,剧本是3万1千字,演出韶光近三小时。小说《尘埃落定》31万字,剧本为2万9千字,演出韶光近三小时。
小说改编戏剧,这对戏剧而言,并不是新鲜事。《李健吾戏剧评论选》中,就收录了《小说与剧本——关于<家>》和《改编剧本——主客答问》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40年,一篇写于1959年。在前一篇文章中,李健吾师长西席指出小说改编成戏剧,并不虞味着小说的成功一定会带来戏剧的成功,“剧本和小说是两回事,工具不同,表现办法不同”。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指出戏曲中一百个本子里,九十部是改编而来。针对改编不如原创的意见,李健吾又指出,莎士比亚戏剧险些全都是改编而来。从创作的角度,他强调改编是戏剧成功的一条捷径,但戏剧改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原为难刁难改编是一种限定,原作越是精品,对改编限定越大,因此他提醒编剧,“剧作者必须时候想着演出的客不雅观条件。”《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中也有一篇《和青年作家谈小说改编剧本》,焦菊隐师长西席认为要把改编看着跟创作一样主要的事情。在改编时,“请把情节再压缩一下,把篇幅让给人物的刻画吧。宁肯剧情的弯曲少些,不让人物的面貌平淡。天下的戏剧大师们,都是人物形象的卓越的塑造者。”有关小说改编戏剧的这些原则和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接管,但对照2021年上海话剧舞台上演的三部话剧,我以为有一些变革正在磨练着我们原有的戏剧规则。最紧张的聚焦,集中在陆帕执导的《狂人日记》上。
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演出,是不是符合不雅观众的欣赏习气?只管几年前,上海的不雅观众已经领教了陆帕长达六小时的戏剧《酗酒者莫非》,但那时更多的不雅观众可能被一种好奇心使令,想看一看这位被誉为国宝级大师的波兰导演,他所执导的六小时的超长演出,会给不雅观众带来若何的惊艳演出。而今他连续这种超永劫的演出,并且因此中国人熟习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改编工具。濮存昕师长西席在哈尔滨大剧院不雅观看试演后,提出的第一条建议便是希望演出能考虑到普通不雅观众的不雅观剧习气。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之后,不雅观剧的见地截然对立。在戏剧《狂人日记》研讨会上,一些话剧专业职员不主见超永劫光的演出,强调要顾及不雅观众的欣赏习气,也便是二三小时的演出时长。有个别专家批评该剧没有笔墨剧本,演员临场发挥,不雅观众犹如《天子新衣》中的群众,没人敢说什么都没看到。但有一些专家肯定陆帕的作品,认为《狂人日记》给人以戏剧审美上的期待和知足,有一种久违的不雅观剧激动。有专家认为,在思想内容上,一位波兰导演将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情绪体验发挥到了极致,像吃人、铁屋子等文学意象很真切地建构起陆帕戏剧的核心内容。在审美形式上,陆帕式的迟缓和延宕,表示了舞台演出的节奏和力度,形成了陆帕戏剧特有的符号措辞。一些长期研究欧洲戏剧的专家认为五六小时的不雅观剧体验,在欧洲并不奇异,乃至还有更永劫光的。永劫光不雅观剧,在戏剧演出中并不是最突出的抵牾和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追捧影视剧的不雅观众一样,只要戏剧作品本身吸引人,再长也不是问题。
在我看来,陆帕的《狂人日记》涉及到很多戏剧方面的问题。作为波兰导演,他的戏剧不雅观念延续着后当代的脉络,特殊是格洛托夫斯基的“朴实戏剧”的不雅观念。像《狂人日记》没有戏剧剧本,这并不是说可以非常随意轻松地排戏演戏,而是与格洛托夫斯基所说的“承认戏剧的朴实,剥去戏剧的非实质的统统东西”有一种内在的呼应。由于在格洛托夫斯基看来,“剧本本身并不是戏剧,只有通过演员利用剧本,剧本才变成戏剧”。利用剧本和根据文学作品阅读体验来加以舞台演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朴实戏剧”中,强调戏剧的主体是演员-不雅观众,以是,那些太阿倒持、影响戏剧的成分,包括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笔墨符号,都要剥掉和去除。分开了浩瀚客体约束的戏剧要有自己的建构法则,这种建构便是戏院演出。
陆帕阅读了大量鲁迅师长西席的作品,并做了60多万字的事情札记。凭借他对鲁迅小说的阅读理解,陆帕哀求演员在演出中通报那些压抑人性的力量——家人的、邻居的、自己内心的和社会文化的,凡此各类压抑的力量,都化为戏剧舞台上“吃人”的演出。整场演出共三幕,第一幕:第一次拜访/日记/鹞子;第二幕:满月/笑声/狼子村落/夜晚;第三幕:鱼和大夫/火车上的青年人/母亲/发热/救救孩子。这些片段式的场景和情景展示,并不依照我们以往不雅观看话剧的习气在行进,也不拘泥于小说的叙事轨迹,而是印象式的、随想式的,带着即兴演出的特色。如果对照鲁迅的《狂人日记》,你会创造,陆帕的作品有时彷佛离原作很近,严格遵照着小说的叙事轨迹,如开头老同学的拜访,是照着小说的笔墨节奏缓缓展开的;如创造吃人的人中有自己的亲哥哥;还有赵贵翁的眼神等。但有时则是离小说很远,漂离于小说之外,自由遐想、自由发挥。像嫂子的出场、高铁上的大学生,都是小说中没有的添加物,这些添加物在舞台演出中,横向拉宽了戏剧的构造,让不雅观众穿越时空、不受原作人物情节的约束,在某个剧情节点上,自由想象、即兴发挥。这种随意性,是中国话剧演出中不太常见的,如果是换一个中国导演,会格外小心。但在陆帕的《狂人日记》中,导演和演员自由发挥,小说原著中所没有的存在物在舞台演出中涌现了。像高铁上的大学生那一段戏,从民国直接穿越到本日。这样的戏剧改编和舞台演出,在理论上显然可以纳入导演为主体的“戏剧构作”范畴。但对很多普通不雅观众而言,如此构作鲁迅的《狂人日记》能接管吗?事实上,陆帕的“做剧法”在中国舞台上也不是第一次呈现,数年之前,根据史铁生小说改编的戏剧《酗酒者莫非》也是如此做出来的,但为什么那时的批评之声很少,而落到鲁迅作品的改编上,人们的质疑就多起来了呢?再扩大一点看,陆帕对付契诃夫小说也有类似的“做剧”,在世界戏剧舞台上为此形成了“陆帕戏剧”这样极具标识度的戏剧艺术。
我们暂且不去谈论陆帕的《狂人日记》是不是可行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长恨歌》和《尘埃落定》吧。从戏剧编剧角度,这两部戏都是中规中矩,极其尊重小说原著的面貌,又根据舞台艺术的须要做了一定的取舍。王安忆评价话剧《长恨歌》,认为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所有改编中,“话剧最靠近我”。而阿来对话剧《尘埃落定》的评价,认为小说原著的精气神都在,“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如果不是客气和搪塞媒体采访,这两位小说作者对改编的评价,是对戏剧改编的高度认肯。编剧赵耀民用三幕戏来表现王琦瑶超过四十年的情爱生活,从戏剧构造来说,前后对称,非常饱满。前一场戏是少女王琦瑶参加选美,结识党国要员李主任,与李主任开始了一段情爱生活。这种男女欢场戏,在小说和戏剧中,习认为常,谈不上特殊。如果说有什么特殊,该当是李主任与王琦瑶之间不对等的爱。一个是年迈的党国要员,一个是青春年少的上海女孩。一个是久经疆场、见过大场面的政客,一个是情窦初开、涉世不深的少女。两人碰到一起,擦出情绪火花,对王琦瑶而言,很难说是爱上李主任,至多只是体验了一把榜上权势人物后所能得到的短暂安逸罢了。这种情绪进程可以纳入张爱玲所说的传奇——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阵烟似的。1950年代一段戏,是王琦瑶与康明逊的遭遇,这该当有点触及情绪。两人年事相称,正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但人算不如天算,阴差阳错,终极还是失落之交臂。1980年代,人生即将落幕的王琦瑶碰着了小自己很多岁的小混混“长脚”,两人糊里糊涂坠入情网,直至王琦瑶被谋财害命、呜呼哀哉。如果说,王琦瑶的前半生是被人追、被人爱,那么,到了晚年的王琦瑶则是试图追一回、爱一回。但无论追与被追,王琦瑶究竟是个没有自主性的都邑漂浮物。她彷佛生平都没有碰着过一个真正适宜她的男人(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须要若何的男人)。如果从戏剧构造上讲,《长恨歌》非常紧凑、完全。但看着看着,你会以为有一点不知足。这种不知足源自于不雅观众对人物结局的某种期待。彷佛王琦瑶末了有点游离于她的性情,变成了另一个有点风尘味的不相关的女人。生平从没有主动追求过别人的王琦瑶,到了生命的后半段,溘然改变了,变得有点盲目主动,热衷于各种热闹和时尚。对照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都邑生活,这段戏有点编的痕迹。王安忆《长恨歌》的故事原型,是一个旧时的上海名媛。杀害这位名媛的凶手,是慕名而来的片警。两人关系中看不到名媛方面有一丝一毫的主动。当然,戏是可以编的,目前这样的剧情和构造安排,是对应着第一幕的构造,第一幕是王琦瑶被别人追,末了一幕是王琦瑶追别人。构造是完全了,但构造没有服从人物性情,不是随着人物走,而是人物为构造的完全须要做事。这样的戏剧变革,让人感到太像戏了,彷佛是人生顺着来和倒着来奥妙地重叠在一起。人生如戏的机缘巧合,反倒有点减弱了不雅观剧效果,由于统统都已经按构造的须要安排好了,人物性情自身的发展变得可有可无。这让我想到黄佐临师长西席援引川剧大师张德成的话——“不像不成戏,太像不算艺。”一部戏剧作品编得太像戏了,有时反倒达不到最佳的戏剧效果。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不能走程式化的道路,为构造而构造,而是要破圈、走新路。正如老舍师长西席所说的,戏曲要规矩,要在规定的程式中让人欣赏到歌舞演出的魅力,而话剧则是要创造,要让人体会到话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有点像创作小说一样,不能依样画葫芦,而是要破除陈规,自由发挥。格洛托夫斯基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被问及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意见时,他说:“东方戏剧的符号般的示意动作是固定的,像字母表一样。而我们利用的示意动作是人的行动的概括形式、是角色的形象化、是演员的分外精神生理学的形式。”参照话剧《尘埃落定》的改编,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探索。这一探索,紧张集中在戏剧的阐述措辞和构造上。作品讲述了阿坝藏区土司家族末了的瓦解历史。作品是借土司的二儿子傻子的阐述来构造全篇。这个傻子既是全剧的阐述者,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人物,有时是复苏客不雅观的察看犹豫者,有时又是懵懵懂懂沉浸个中确当事人。当代戏剧演出中所常见的布莱希特的间隔手腕,在《尘埃落定》中非常有节制地掌控着舞台的演出节奏,有时是叙事,有时是展演,穿插有序,调度适宜。话剧《尘埃落定》的构造是从未知的过去走来,终极走向灭亡的宿命。在间隔手腕助推下,舞台充满张力,有节奏的剧情展现,不断掀起高潮。
对照陆帕的《狂人日记》和话剧《长恨歌》,话剧《尘埃落定》的舞台美术十分出彩,更靠近于现实主义美学的自然呈现。藏人的衣饰打扮、土司的深宅庭院和雪域草原上艳丽的罂粟花海,这统统舞台布景效果逼真,表示出导演的戏剧风格和艺术追求。胡宗琪导演没有像本日常见的话剧编导那样,通过声光化电的多媒体手腕,将舞台弄得花里胡哨。他谢绝多媒体舞美主导舞台场景,哀求依赖实物布景来呈现,以是,舞台背景有些地方过于幽暗,就像自然环境中,院落有照不到光的地方,胡宗琪导演任其幽暗,不会为了让不雅观众看得清某个角落、或角落里站着的某个人,而故意补一束光来照亮这些角落和人物。导演是希望用这种近似逼真的状态来呈现藏区的人物风貌,让不雅观众感想熏染到雪域高原的风采绰约和诗情画意的远方。胡宗琪导演的这种艺术追求,在此前话剧《白鹿原》中有非常成功的表示,赢得一片赞誉。而曹路生教授在编剧艺术上,追求诗意和抒怀的特色,在他上世纪80年代辅导的话剧《黑骏马》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曹路生是话剧《黑骏马》的编剧辅导)。这些优质的戏剧元素,照理该当在《尘埃落定》的舞台演出上有更加惊人的发挥,但事实上,争议之声并未减少。一些不雅观众认为《尘埃落定》是一部朗诵剧,而不是话剧。舞美精彩,台词精彩,但舞台彷佛没有动起来。换句话讲,编剧忠于原作,导演忠于剧本,演员忠于剧作和导演意图,但全体舞台彷佛没有充分活动开来,是一个一个片段在动,而不是整出戏在展开,达到像花一样依次盛开绽放的惊艳效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让我们又不得不回到陆帕对戏剧提出的问题,——要让舞台活起来。编导、舞美和演员,在这一过程中要成为最大略最积极的要素,而不是相互牵扯的力量。他把舞台演出当作是一种类似于作家的写作。以前的戏剧“写作”,是编剧、导演、舞美、演员等一起参与。好处是人多势众、分工协作,但负面效果是背离了“朴实戏剧”的本意,大家都想自由发挥一下,“各种凌乱的戏剧场面,混成一团,没有主体,或者说缺少完全性”。事实上,人类最远古的戏剧,没有那么繁芜,人们只服从舞台演出的须要。当代戏剧有了职业分工,但戏剧并不是分工越细、职业化程度越高,演出效果就越好。彼得·布鲁克批评美国百老汇,不是戏剧的丛林,“而是齿轮紧密咬合的大机器”(拜会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以是,陆帕的做剧法极其简约,他是编剧,他是导演,他是舞美,他是音乐设计。他不要演员背诵台词,而是情景发挥。他没有预先设计好固定的台词。大的戏剧构架,是编导与演员互换心得所致,个中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阅读体会和生活感触。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演员直面不雅观众,用演出点燃不雅观众。为了调动演员的潜能,陆帕阅读了不少鲁迅的作品以及干系材料,多次去绍兴乡下体验生活,直接感想熏染、体会鲁迅当年的生活环境和小说的场景。他不想复现鲁迅小说,而要积极解读鲁迅小说,以一个波兰人的阅读理解,来展示鲁迅的小说意义。陆帕用“中国印象”来命名他的这两部中国戏剧。
如果人们以为陆帕的解读可以成立,那么,是不是鲁迅或史铁生的原作改编,倒变得不那么主要了,主要的是戏剧本身的问题——也便是戏剧可不可以这样来做?从格洛托夫斯基的“朴实戏剧”到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再到陆帕的“做剧”,彷佛都想延续戏剧最本源的空想状态,他们不想把与戏剧不干系的东西扯得太多,而强调把稳力要集中在激活戏剧最基本的要素上。原来格洛托夫斯基在“戏剧实验所”(格洛托夫斯基语)实验的是演员和不雅观众无差别的领悟,乃至演员冲进不雅观众群里,与不雅观众拥抱在一起演出。到了陆帕手里,这种编、导、演的领悟变成了戏剧舞台的做剧法,他不否认舞台艺术,但舞台艺术必须是牢牢节制在导、演手中,而不是依赖于“一剧之本”。陆帕在接管采访时曾说过:“我常常看剧本,我以为有一点烦,由于都是要符合一些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假的,以是我以为这个可能是戏剧的弱点。”没有剧本的戏剧会是若何?陆帕的《狂人日记》事情札记以及事情团队清晰的舞台事情程序,见证了陆帕式的戏剧构做法和它的戏院效果。对付陆帕的导、演方法,参与演出的中国演员王学兵、李龙吟接管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认肯。海内从2015年开始,对陆帕首次巡演中国的戏剧《伐木》,有较多的文章予以先容和关注。自此以来,他是中国戏剧研究的一个主要工具。2018年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波兰哥白尼大学和国际剧协举办过“从格洛托夫斯基到陆帕——波兰戏剧对当代天下戏剧的影响”国际研讨会。我感到陆帕的戏剧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戏剧符号,在世界戏剧舞台上,有很高的标识度。它不涉及对戏剧作品好坏的评判问题,而是匆匆使人们不断思考戏剧的边界是什么。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舞台上涌现无场次话剧以及实验话剧时的情景,这些实验戏剧好不好本日来看,实在已经不主要了,主要的是它寻衅了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不雅观剧定势和戏剧编导演的事情程序,由此开启了中国当代戏剧多样性和可能性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历史时候。
回顾以往的戏剧史,我们会把稳到很永劫光我们的戏曲是没有底本的,上演前演员相互谈论一番,说定演什么,排练几遍就上场了。导演制在中国也是上世纪50年代才在艺术院团中遍及开来,很永劫光中国戏剧体例中是没有导演这样的设制的。中国戏剧艺术的重大变革,上世纪五四季代及80年代是最主要的两个期间,是中国戏剧创制订规矩的高光时候。经由了这两个主要期间的变革,才有我们本日现行的戏剧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不是一劳永逸、不可变动的?新世纪以来,这种潜在的改革呼唤,彷佛还在滋长繁殖。因此,对付陆帕戏剧的关注焦点,不应该全部集中在不雅观剧韶光太长、有没有文学剧本这样的表面问题上,而该当深入到当代戏剧变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问题上。陆帕戏剧引来的争议,只是一个方面,它让人们看到当代戏剧扩展的边际并没有划定,须要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这一领域中来。如此看来,戏剧实验在本日还是须要的。
作者:杨扬(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系作者2021年上戏导演系导师大师班系列讲座文稿
编辑:童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