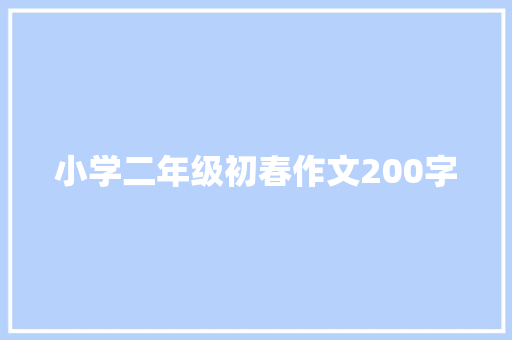卷帘暗问何故是,帘外风香蜜如新。莫怨小雨湿人面,春来江水贵如金。
写下这首诗当在去年的初春。伴随着细密的雨丝落地声,在阴暗的小书房怀着寒意走笔下这首诗后,忽地看到锈蚀的防盗窗外爬山虎盘出的幼藤,翘着嫩黄的脑袋直插浓密的云层,我就知道,春天终归还是来了。

于是我披上外衣就去拜湖,依我看来,初春的颜色应该是黄。淡黄,嫩黄,鹅黄的一点。从枝头上,灌木丛中,泥地子里偶尔闪过,仿佛跳动的穿着薄纱的精灵。还记得陆蠡的《囚绿记》,百无聊赖的他在黑暗的小房间里囚禁了一枝常春藤。陆蠡死于四月份,正是初春,可惜他再也看不到那抹绿意,不过在那个炮火纷飞,生命贱于草芥的年代,他恐怕也看不到如此淡的“绿”吧?
湖边间或两只长嘴长脚的水鸟飞过,立在湖中心的木桩上,盯着水中的游鱼。一只不知什么品种的雀子贴着泥地掠过,它那丰满的胸脯擦过的地方便是一线绿。收起伞,站在桥上,有鸟会从桥拱下飞过。平静的湖面无声地吸收了雨丝,雨一丝丝银线般悬在远方,偶尔地跳动仿佛老旧的电影。想到程小青,他的苍白的脸庞,他的苏州,他的堤,他与周瘦鹃的友情和他的坚持。又想到那历来为人称颂的断桥,想到白娘子,但是断桥游客太多了。谁在那边船上,撑起一湖烟?在这影影绰绰的江南,竟似虚幻的画卷。我站在桥上遐想,等一个丁香般芬芳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我身后飘过。仿佛一丝紫罗兰的幽魂,飘过。
中国的武装革命往往发生在夏秋之际,那时侯人们才有粮食吃,吃饱了才有工夫闹革命,像这种初春天气,再细密的春风也无法把志士们的热血从寒冬的肃杀中唤醒。但既然春天已经来临,希望也想必不会遥远。我最尊敬的国父孙文先生正是弃世于这么样一个初春,3月12日,冬季还未远去,国父的灵柩就已停在了南京。他的离世宣告了一段历史的结束,预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岂不正像这初春的生命?虽然脆弱,但蕴含着大地永不熄灭的强大生命力。
我想我是爱着一个季节叫做初春的,再过十几天,那些嫩芽就会像教学楼上每层种满的迎春般汹涌地绽放。从教学楼的背面看,就是一面几十米高的淡黄的花墙,这是本不属于初春的美啊!初春的美该是朦胧的,含蓄的。如果说诗歌之美在于含蓄,那么初春便是四季中最美,最美的那一首小令。
[髙中800字作文之初春]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