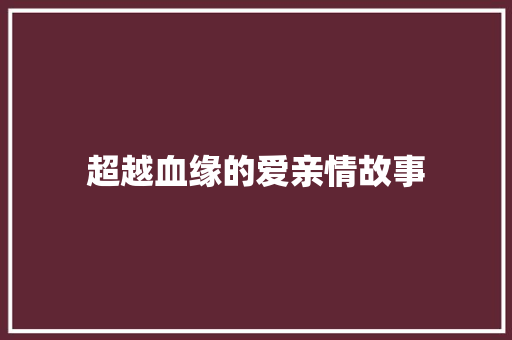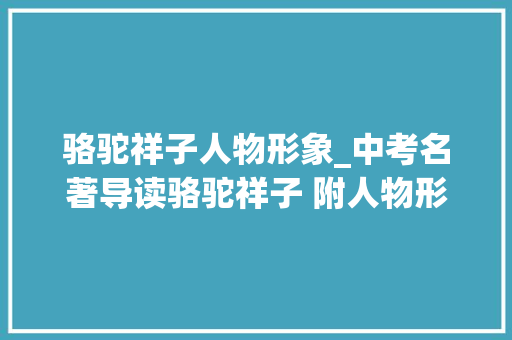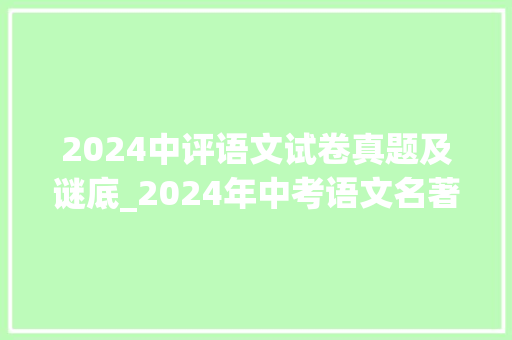志怪传说的书写一贯是文人墨客的后花园,晚近尤盛,从张岱到袁枚到纪昀,网络那些或阴森或吊诡的行状故事,遂成一类,到民国年间,周作人挟此遗传,捋袖子拿希腊神话动刀,乃兄鲁迅不甘其后,《故事新编》虎虎生风。建国后倒是少有成精的人了,今日看到祥子(笔名念远怀人)写《搜神札记》,又见这些故纸堆里钻出来跳脱的鬼怪列传,可谓“鬼贯中西”,把古今中外暗黑中隐蔽的各种活物一锅乱炖,视野极大,又信手拈来,点到为止。
祥子说“赏怪如赏花”,书里“花”是一帧帧古今中外的雕塑绘画,切实其实是怪诞的美术史,只是这“美术史”只是随笔的旁注。本雅明曾有年夜志,用引文写巨作,祥子却用注文构建神话宇宙。注文里上天入地,一下子是六千年前巴比伦的天空女神与西王母对视,一下子就涌现了漫威里的美国队长黑化的寓言内涵……炫目的腾挪姿态,才能呈现惊奇的神鬼面孔。读注的意见意义,才是博物学的意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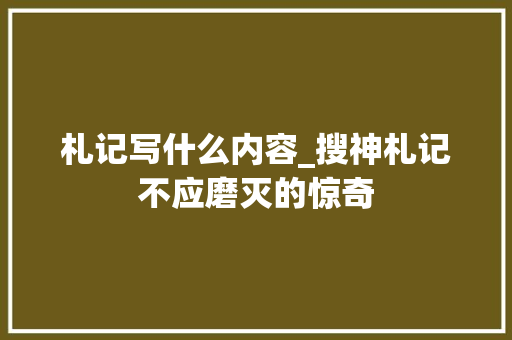
太有趣了!
有用吗?无用!
贡布里希说过:文化本来便是没用的,但不能没有,那关乎天真,关乎想象力,关乎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鬼神原来也不待在意见意义的后花园里。祥子在后记中说,“怪”是“心”和“圣”的组合,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敬畏鬼神是古人的共性,使徒保罗在圣经中描述希腊人所树立的铜像上书“未识之神”,透着不敢年夜声语的畏惧。一边敬畏着,一边又本能地瞩目光所不能照透的方向,想象认知之外的秘密。
仓颉造字,“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笔墨被创造,口耳相传的秘密从此被准确地记录和传播,解密意味着须要承受谩骂,以是天上都下起了粮食,而灵界的鬼怪由于人类洞悉他们的秘密,无以遁形而哀号。
笔墨因此被目为神秘力量的载体,传讲奥秘的人则更是被特殊的光环和特殊的阴影所笼罩,巫或者先知是职业更是宿命。然而,人类发展依据已知而揣测未知,人所知的越多,未知的畏惧就越少,笃信就加倍被疑惑所替代,理性的大旗带领文明的前行,那个“圣”日益的淡泊,惟余一“心”,内容失落去震慑民气的功效,在朝为“巫”的,跌落野外成为“戏”,悦己娱人,传讲的人变为小丑,圣愚或游吟墨客,渗透进了小说家言,戏剧舞台,话本,类书,草堂之上或夜航船中。审美在不知不觉间搭建,“神话”跳出了宗教或道德的框架,成为艺术的源泉。
但是,在历史长河里人们丢失了什么?又以自己的想象力添加了什么?人类确实走入了一个“祛魅”的时期,自我成熟之后,天真渐泯,大多数人都以为那些传说或者无稽,或者不主要。神话去掉了神圣,只留下了意见意义和刺激。我相信在成年人的愿望和义务之外,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部分从不会终年夜,从不会失落去追问和寻求一点小刺激的本能,以是,人们须要“怪”,须要讲怪故事的“怪蜀黍”。
我第一次见祥子就隐约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脸上带着诡异又天真的笑,说出一些奇怪的类比,惊异的故事,你问他“真的假的?”他会得意地说“当然是假的”。这是一种有着刁滑本领的“孩子王”,一种力量,他既有迷恋神话的好奇天性,又有娓娓道来的叙事能力。我相信如果在某个丛林边缘的部落里,一定会有人指着他喊“捉住那个行巫术的家伙”。
认识祥子之初,他就先容我读《金枝》,然而我委实不喜好,在人类学的系统框架里,弗雷泽井井有条地类比着各地的巫术神话,我承认他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信息大全,然而,那些故事不再好玩——作为好奇而精力充足的孩子,我们须要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享受惊喜和惊吓,而不是将它们置于显微镜之下。爱好魔术的不雅观众一定讨厌“魔术揭秘”,我甘心去破庙重逢狐狸精,墙头等候美女蛇,或者想象袁洪的头颅被砍之后莲花如何开放出新的。以是,一打开《搜神札记》,我就仿佛瞥见祥子露着诡异的微笑,手作拈花地讲一个个故事。这才是“孩子”所须要的东西。在网络时期,多数人活着的重心不在于“相信”什么,也不在于“热爱”什么,而是“什么我都可以找到”。这显出前所未有的聪慧吗?不,这是前所未有的屈曲。我很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网络旗子暗记,祥子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给他们讲西王母和“虎魄”的故事。
我说祥子的《三十六骑》,把历史写成了神话,而《搜神札记》,他又把神话写成了童谣,那是每个人不应该磨灭的意见意义,敏感,畏惧和愉快。那是一些无用的知识,然而让我在这个无味的时期,瞥见本能,瞥见活泼泼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