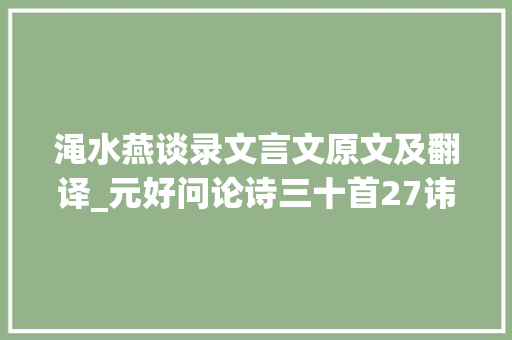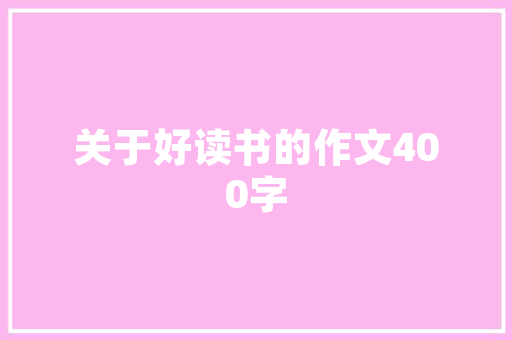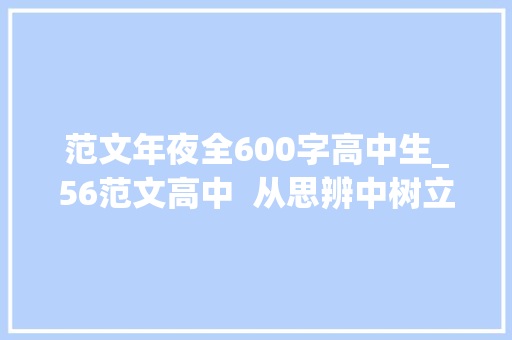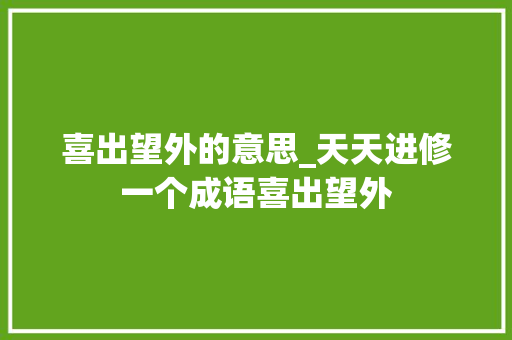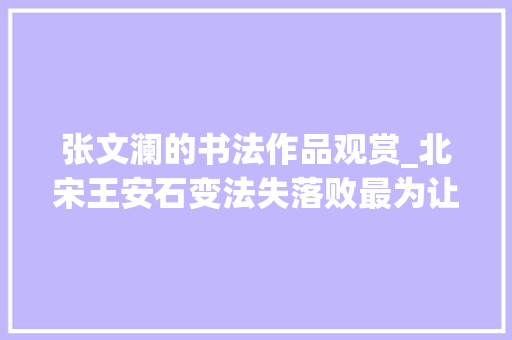人们总是希望天才能和天才相遇,并想象着他们相遇的情景。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记载了苏轼(1037-1101)和王安石(1021-1086)之间的三个故事。一为苏轼擅改菊花诗。苏轼拜访王安石未果,见到文几上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认为菊花并不落瓣,于是信手依韵续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墨客仔细吟”。苏轼后来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见到黄州菊花落瓣,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二为王安石以自己有“痰火之症”需瞿塘中峡水为由,让苏轼代为携取。苏轼因“鞍马困倦”,错过中峡水,取下峡水代替,为王安石看破;三为苏轼在与王安石对句和识典上落于下风。“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个天秀士物碰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争强好胜之心撞击出充满机警的火花”(刘勇强《虚拟的历史公共空间》)。这是一则“天才遇挫型”的情节类型叙事,故事的来源该当是宋元杂剧。冯梦龙在篇首提到本则故事的意义是“奉劝众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在其余一个同类型的故事中,苏轼却充当了“强中手”的角色,为秦不雅观解围。(见《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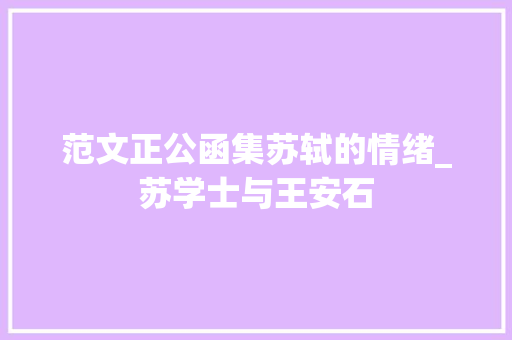
说苏轼“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师长西席门下”,对王安石执弟子礼,见必曰“晚学生”,自是小说家言。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听说,苏轼的策论《刑赏虔诚之至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1007-1072)的赏识,因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门人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他由第一降为第二。按照唐宋人习俗,举子对付提拔他们登科的知举(主考官),必奉为坐主,以门人自居。实际上,欧阳修对苏轼早有知遇之恩。早在进士及第前,苏轼就通过雅州知州雷简夫认识了欧阳修,并得到了后者的赏识。在登第后,通过欧阳修,苏轼得以进入当时的士大夫核心圈,“是岁登第,始见之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琦)、富(弼),皆以国士待轼”(苏轼《范文正公函集叙》)。苏轼对欧阳修一贯是尊敬有加,视之为师的,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苏轼《上梅直讲书》)欧阳修去世后,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函》中说“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故意思的是,据《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看到王安石的“咏菊诗”写出续句的倒是欧阳修(笔墨少异,欧文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传语墨客仔细吟”)。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来日诰日启间金陵兼善堂刊本)中的“苏轼和王安石”形象
苏、王的首次打仗是在嘉祐年间。此间,王安石不喜苏氏父子的文风,称老苏的文章“有战国纵横之学”。先是制科考试时,王安石声称苏轼文章“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再是王安石谢绝为苏辙起草任命制书。两年后,苏洵的《辨奸论》一文称王安石“不近人情”“囚首丧面”,“鲜不为大奸慝”,将王安石与三苏的抵牾推上一个高潮。熙宁年间,苏、王之间的紧张抵牾实际上是环绕变法的政争。苏轼反对新法,紧张是反对科举由“诗赋取士”变为“经义取士”。“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条)熙宁四年(1068),苏轼被外放为杭州通判。
虽然对付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人们毁誉不一,却很少有人对他的人品提出疑问。连他的政敌司马光也称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与吕诲叔简》二)后世如陆九渊也对他赞誉有加,称他“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洁白之操,寒于冰霜”。(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苏东坡本人在《王安石赠太傅》一文中给予王安石以很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天才和天才总是惺惺相惜的。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于诗文“谤讪朝廷”被逮捕入御史台狱。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因之此案也被称为“乌台诗案”。相传,苏轼下狱后,王安石曾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其弟王安礼也向神宗进言,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犯人”“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宋史·王安礼传》)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的态度为他和苏轼之间的关系缓和埋下了伏笔。
天才之间并非总是充满张力。苏轼在回答“新党”官员李琮的信中说“知荆公见称《经藏》(指《胜相院经藏记》一文)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苏轼《答李琮书》)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的苏轼,绕道北上,道经江宁,拜访了王安石。苏轼称这次会面“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两人见面,自然不会只是“诵诗说佛”,但发言的详细内容,恐怕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旁人只能从记载中看出来两人相见甚欢,“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在此后致王安石的书信中,苏轼也自称“某游门下久矣”(苏轼《与王荆公二首》之一)。当然此处的“门下”只是对付地位高于自己的长辈的客套话,不能理解为便是“门人弟子”的意思。
对付晚年的苏轼来说,对王安石不能释怀的大概便是对“同”和“异”的不同理解了。苏轼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答张文潜书》)肥沃的地皮可以成长多种多样的植物,贫瘠的地皮才会成长单一的黄茅和白苇。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24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