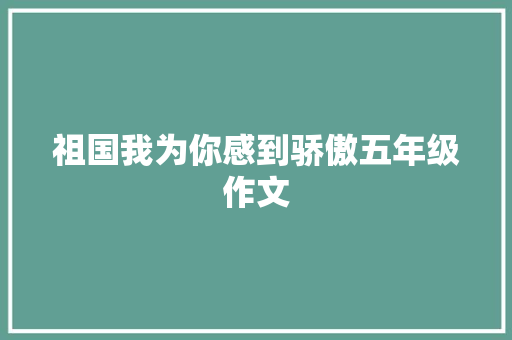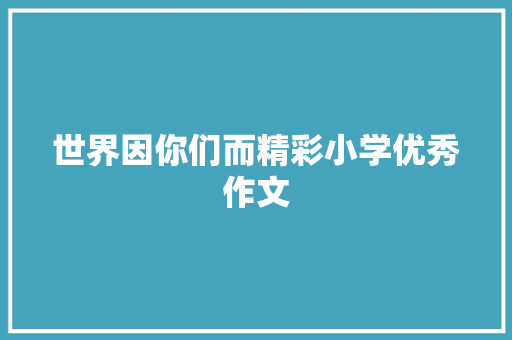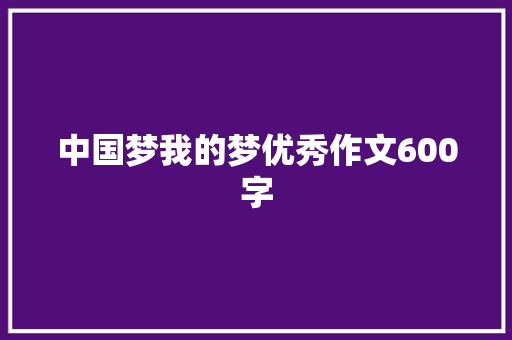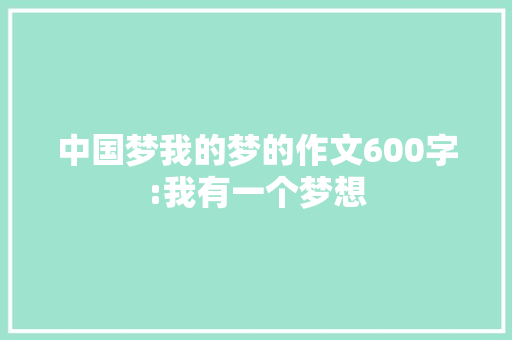卫匡国,1614年9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文化之城特伦托市。他自己曾说:“有人说我这天耳曼人,也有人说我是意大利人。事实上,我来自特伦托,一个位于意大利和日耳曼边疆的城市。”1638年9月19日,从热亚那动身,历经坎坷,大约于1643年10月抵达杭州,他开始了在明清转换之际在中国的传教生涯。1651年3月,受其上司叮嘱消磨,卫匡国以耶稣会中国传教团代理人的身份动身返回欧洲,去罗马教廷传信部为耶稣会在中国尊重中国传统礼仪的传教路线辩解。在漫长的将近三年的旅途中以及其后在欧洲的数年间,卫匡国撰写并出版了《中国新舆图集》《中国历史:从上古年夜公元元年》《汉语文法》《鞑靼战纪》等不朽的著作,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习俗、措辞、当时的社会现状等先容给了急迫希望理解中国的欧洲人。这些著为难刁难于欧洲全方位而又深入地理解中国做出了极其主要的贡献。正由于此,美国学者孟德卫将卫匡国与曾德昭(1585-1658)、安文思( 1609-1677)、柏应理(1623-1693)、白晋(1656-1730) 一起并称为继利玛窦(1552-1610)之后奠定和发展早期欧洲汉学的五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正是这些早期汉学家,终极导致了“中国热”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如果说利玛窦将西方的科学引入了中国,那卫匡国则是将中国先容给了西方。
在卫匡国之前,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有影响力的著作是葡萄牙道明会传教士克鲁兹(1520-1570)于1569/1570年在葡萄牙埃武拉出版的《中国志》,他比马可·波罗更清楚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包括许多以前西方人从未所知的细节。他的著作在葡萄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也陆续被翻译成其他欧洲措辞,但真正地被大众所广为知晓则是由于1585年西班牙奥斯定会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1618)所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个中大量引用了克鲁兹著作中的内容。门多萨的著作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并在西方天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像一部关于当时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尚、礼仪、宗教崇奉以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形的百科全书。虽然门多萨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550年,以及各朝天子和他们的名号,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细节来支持这些不雅观点,以是他所提到的悠久的中国历史并未引起历史学家们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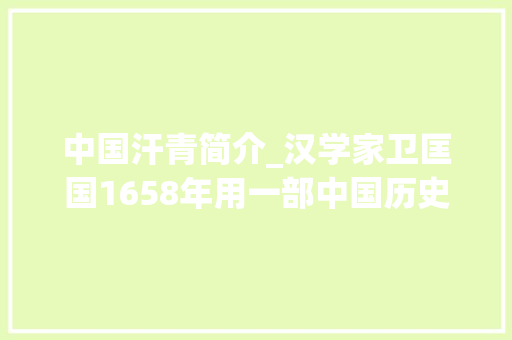
1615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翻译、改写和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书内容的75%来自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所有经历的记录,25%来自金尼阁的耳闻目睹。它虔诚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朝廷、风尚、法律、制度等等,似一部中国见闻录。1642年,在中国生活20余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1586-1658)出版了《大中国志》, 与《利玛窦中国札记》类似,曾德昭的这部著作也仅仅是对自己在中国事情和生活经历的虔诚呈现,记录了中国各地的地理分布、物产、官场制度、风尚习气、措辞、学问、科举考试、衣饰、宗教等情形,实质上仍旧是一部关于当时中国的百科全书。
卫匡国于1658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才算是西方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真正关于中国历史的威信著作。他以翔实的笔触和丰富的内容,给西方描述一个可信的、可以上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一个文明国度的历史。而他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尊重,以及对西方“正统”历史的疑惑精神和开放的心态,使得其著为难刁难西方历史叙事的根基构成了严重的寻衅。因此,美国历史学家科雷(1930-2002)声称:“卫匡国对中国古代史的‘创造’,开启了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纪,并终极匆匆成了天下史籍写办法的重大变革。”而卫匡国《中国历史》出版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风尚论》中用中国及其历史来嘲笑博苏埃主教和其他历史学家的狭隘,他们将天下历史局限于西方文化及其起源”。虽然卫匡国曾试图调和中国历史年表上的韶光与西方历史记载的大大水的韶光的冲突,但客不雅观上其《中国历史》却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
阅读卫匡国的《中国历史》,给我们感触最深的是他对中国公民、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良政善治的溢美之词,详细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中国人身上的这种品行值得称颂,也正是因此,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精良”、“我无意搪突任何人,但我敢说在从事农业生产上,论技能、论毅力、论细心,任何国家都比不上中国。根本无需惊异于中国土地上种出的粮食居然能够养活那么多的人口”;“通过对良政善治艺术的详细定义我们也可以窥见中国哲学的独创性”。
我们如何能打消这些溢美之词不是出自他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好感和赞颂呢?卫匡国在华期间,中国险些在所有领域都是天下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欣欣向荣的东西方贸易使得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其他手工艺品从中国运到欧洲,同时也使得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客不雅观上构成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的上流社会乃至普通百姓都过着富余、得体、风雅的生活。
卫匡国在《中国历史》中对中国的风尚、伦理道德和古代哲学家的赞颂,与他和中国文人与士子们的密切交往分不开,这为他认知中国文化供应了极其主要的根本;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社会本身对人伦和德治的重视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生名誉教授罗波坦在大约80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位欧洲人文学者比耶稣会传教士更热心于研究儒家经典的美妙之处并理解它在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中的实际运用”,在他们的眼里,儒家哲学“即便没有超越,也是可以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思想并驾齐驱的”。卫匡国在《中国历史》中花了不少篇幅专门先容孔子的学说,由卫匡国在第二次来华时带到杭州的西西里人殷铎泽(1625-1696)将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时,就将《中庸》这一书名译为《中国政治伦理学说》,可谓极其精辟。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光阴并没有让卫匡国在中西文化互换史上的贡献被人们遗忘,数百年后仍旧还有学者研究或提及他的著作,关于卫匡国在将中国先容给西方上的贡献还是留给读者们去创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