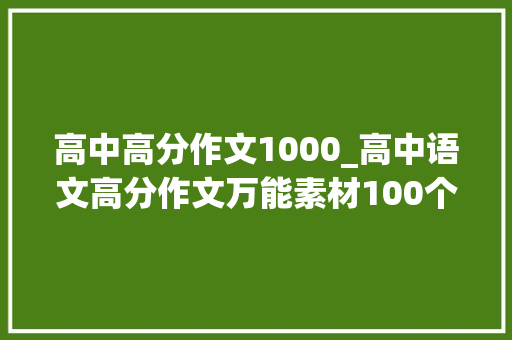“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
1990年,一行外来作家看到陕北的穷苦闭塞,想当然地问身旁的路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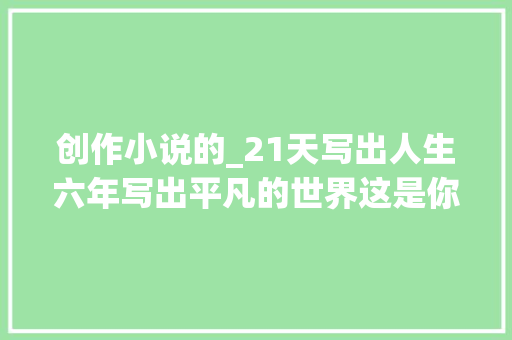
路遥一怔:
“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地皮是很有感情的啊!
早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赤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是王安忆吊唁路遥的文章里写到的一段对话。
后来,他们亲眼见到了那样一枝桃花。也是在荒脊的黄土中,涌现了一枝不遗余力开出的桃花,在周遭景致的映衬下,这点娇嫩的粉红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我想,形容路遥,用牛、用马,都不如用这枝“不合时宜”的桃花。
路遥人生中的第一次“不合时宜”,在他14岁那年。
他本是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落一户普通庄家家的孩子,可家里太穷了,穷得只有一条被子,这种景况,在他的弟弟妹妹出生后更加严厉,没办法,小小的路遥,被送到了延川县的大伯家。
在那个极度穷苦的年代,普通庄家的孩子,走的都是一条约定俗成的道路——在家帮农。纵然读书,最多读到小学,知道怎么算工分,就足够了。
路遥的养父也为路遥方案了同样的人生道路。
1963年的夏天,路遥考上了延川中学,养父却把早准备好的一把小镢和一条长绳交到他的手上,让他和自己一同干农活。
然而路遥却不这么打算。
在这片地皮上生活了14年,贰心知肚明,这里的人们世代贫穷,生活中只有黄土、日头、庄稼和汗水,要在这里做一个农人,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样辛劳而乏味的生活。
他有个纯挚的空想,走出去,靠读书这条路离开这里。
于是,路遥做了人生中第一件“不合时宜”的事。
在别的孩子已经开始在家帮农的时候,路遥拿着养父给他准备的劳尴尬刁难象,跑到河滩,把东西一件件地丢到河滩里,又跑回村落庄,挨家挨户地哭着求人凑报名费。
村落里的人们都不富余,东凑西凑,总算凑得了两升黑豆。
在延川中学读书的日子里,由于家里没钱交粮,他总是饿得发狂。
午饭韶光,别的同学吃着学校供给的餐饭,路遥却只能就着“熬锅水”,两口咽下掺着麸糠的冷糠团子。
到了晚上,他就跑到城郊,在地里翻找统统能吃的东西,野菜、草根……睡觉的时候,听着隔壁床“嘎嘣嘎嘣”嚼干膜片的声音,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那个黄土之外的天下,是他唯一的念想。
路遥人生中的第二次“不合时宜”,是和北京知青林虹的恋爱。
1966年,路遥考上了陕西石油化工学校,这意味着他可以从此跳出农门,去城里拥有自己的“铁饭碗”,偏在这时,一纸“知青下乡”的关照下来,路遥随着大流回到了村落庄里。
心中愤懑不平之时,他碰着了活泼俏丽、说一口普通话的北京姑娘林虹。
在林虹之前,有不少本地女子向路遥示爱。
一次,一个高挑身材、白净脸皮的陕北俊女子向路遥表达爱意,路遥赶忙找借口谢绝:“我便是个农人。”
女孩儿露出满口整洁的白牙:“你是农人,难道我不是?我就喜好农人。”
路遥暗暗叫苦,又打马虎眼:“我啊,农人也不是个好农人,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边九样不会。”
没想到女孩心意已决:“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呆着,什么也不要管。”
话说到这份上,再加上这女孩本身长得俊秀、性情又好,实在算得上良配,可路遥却拔腿就跑,留下女孩僵在原地。
直到1969年的一次文艺演出,路遥看到了台上穿着红衣服、蹦蹦跳跳的北京姑娘林虹,顿时惊为天人。
与本地女子比较,林虹身上散发着的气质,正是路遥空想中大城市的气息。
与此同时,路遥的才华和人品也让林虹爱慕,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了。
身边的人都苦口婆心地劝路遥,知青迟早会离开陕北,最稳妥的还是找个本地女子,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这些话如数灌进路遥的耳朵,他却充耳不闻,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
在那个多雪的冬天,两人时常缓缓地在河边闲步,踩着吱吱呀呀的积雪,聊着刚读过的书,唱着《三套车》和《拖沓机手之歌》……
1970年的一天,县里分给路遥一个指标,让他到铜川市“二号信箱”当工人,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招工,机会十分难得,对付一贯想飞出黄地皮的路遥来说更是十分宝贵。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路遥转手便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恋人。
身边的朋友都想着法劝他,路遥却一副铁了心的样子,眉头一皱:“为了她,去世也值得!
”
热恋中的恋人离开了陕北,路遥孤独极了,每天盼着林虹的来信,可恋人的信件却从一月一封逐渐减少到三月一封,后来乃至一年也见不到一封信。
一天,上边溘然宣告要对路遥进行政治审查,这样一来,路遥出息堪忧。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收到这个确当天,路遥终于等来了恋人的来信,没想到,信件的内容却是要与他绝交。
政局变革,让路遥那走出黄地皮的空想实现无门;恋人的绝交信,更是断了他与表面的天下仅存的微弱联系。
他哭得肝胆欲裂,心无所恋,冒出了却束自己生命的动机。
这天夜里,他走到村落庄里的一片水潭边,水面很平,一轮又白又圆的玉轮映在水面上,余照映照着阁下绿油油的瓜地,这时,他忽然“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奥深厚的爱恋”,轻轻地从水潭边折转回来,摸到一片瓜地里,一口气吃了好几个甜瓜。
回味着甜瓜清甜的味道,路遥想,这个天下,“有的只是最平凡不过的生活,和在生活中不断困难前行着的普通的人们”,这个中,支撑着人们的,不过这样一个甜瓜的美好念想。
如果说,之前的路遥是纯挚的空想主义者,纯挚地想逃离地皮,逃离乏味的生活本身;现在的路遥,在看破生活之后,选择了热爱生活,他有了新的空想:用手里的笔,为这片黄土上的人们,创造一个“甜瓜”的念想。
于是,路遥重新回到山沟里,当民办西席之余,在《山花》上揭橥作品。
1981年的一天,他忽然有了创作的灵感。
那一阵子,甘泉招待所的院子里,老瞥见一个头发蓬乱的人,在夜色中徘徊来徘徊去,招待所的白所长狐疑地盯了这人好几天,给县委通了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
县委果人听了描述,知道是路遥,哭笑不得地见告白所长:“别惊动他,那人在写书呢。”
那段韶光,路遥每天能写上18个小时,“浑身犹如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欠亨顺”。
21天后,路遥写出了小说《人生》。
《人生》揭橥后,路遥一下子成了名人。
火车上,只要广播里在播《人生》,本来喧华的车厢急速变得悄悄静的,都侧耳专注地听着,听完一章,还不尽兴,纷纭互换对“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意见;全国各地的读者信件纷纭飞向路遥的住处,有人还写道,如果“人生导师”路遥不复书,就“去世给他看”;作家们也在评论辩论路遥,陈虔诚琢磨着,之前那个胖乎乎的人,整天还聊着闲天,说自己和哪个女的好过,竟然一写就写出了一本这么成功的书,把其他作家甩得老远,太打击人了!
路遥也很得意,省作协换届的时候,他和贾平凹的票数很高,上厕所的时候,他兴冲冲地对贾平凹说:“好得很,咱要的便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
”然后把尿尿得很高。
这时的路遥,完备可以靠着这部作品,一辈子当个“白白胖胖的文学编辑”。
可路遥偏偏做了第三件“不合时宜”的事,他选择了“重新投入严厉的牛马般的劳动”。
他说:“这生平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生平中最主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那件主要的事,便是为底层人,创造一个“甜瓜”一样平常的精神皈依之处;那本规模最大的书,便是《平凡的天下》。
1985年秋日,在完成了长达三年的准备事情之后,路遥拎着两大箱资料、十几条喷鼻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来到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天下》。
创作的六年间,路遥因严重的肝病多次吐血、住院,可他总说:“只要没有倒下,就该连续出发。”
每天都从中午写到凌晨,“清晨从中午开始”。
这个中,他还有项特殊的活动——贿赂事情间里嚣张的老鼠,每次用饭的时候,路遥总会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把老鼠喂饱了,它们就不会总是“吱吱”地跳上事情台来打扰他写作,这办法很灵,路遥只要看到门背后的一滩馒头渣,就知道两方能和平相处。
1988年5月25日,下午六点旁边,一支圆珠笔,从路遥的房间扔了出来。
路遥缓慢地,移动到陕西作协的大院门口,一下瘫坐在门口的破藤椅上,堕泪嗟叹道:“太累了!
”
他才不到四十岁,却宛如老了二十岁。
他脑海里涌现了托马斯•曼的那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便是好的。”
这本书里,贫苦的人们,经受着现实与精神的双重痛楚,却能在无比的痛楚中巍然站立,终极改变了命运。
读了这本书的人们,在孙少安孙少平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苦闷是相似的,他们的挣扎是相似的,他们的奋斗也是相似的。
书里的人们末了享有的奋斗成果,更成为了人们在现实中爬起来连续挣扎的念想。
有人说,路遥笔下的现实是假的,现实天下里,奋斗的人们不一定能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想的人,无疑是复苏的。
但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们,须要这样“甜瓜”样的念想,书里人物的精神定力,更是他们无法谢绝,也不能废弃的。
1990年,那一行作家临走的时候,路遥做了第四件“不合时宜”的事。
那是在饭桌上,人们感叹,某些作家活了一辈子,到了也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
个中一人指着路遥、莫伸等人说道:“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
”
听了这话,其他人都张口结舌,路遥却一下子起身,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
”
那人坚持:“便是这样的!
”
说完起身想走。路遥急着扯他的袖子,大声辩驳道:“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
那人说:“走着瞧吧!
”
没有办法急速证明自己,路遥急得脸都白了。
所有人都不明白,明明是一句戏言,为什么竟那样伤了路遥的心。
这件事过去没两年,路遥便因创作过劳去世了。
那句关乎名利权财的戏言,要等一个人老了才能证明,可路遥,还没老,便已故去了。
“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路遥,由于知道这片地皮的贫苦,前半生,一贯想着逃离。
也是由于知道这片地皮上的贫苦,后半生,他选择扎根在现实的地皮中,为人们创造一片精神的甜瓜地。
他彷佛始终是“不合时宜”的。
在其他人屈从于现实之时,他挣扎着要拼出一番名堂;又在可以逃离贫苦、享受富贵时,选择留下来,实现另一种人生的意义;在30年后的本日,他同样是“不合时宜”的,很多人颓废丧气地活着,路遥却把“若何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主要得多。
这样的“不合时宜”,是一种空想主义。
是不甘心淹没于黄土,抽空全部情绪,从中生发出来的那枝桃花,那种颜色在满目的黄色中十分突兀,却伤及心肺。
路遥之去世,去世于空想,这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