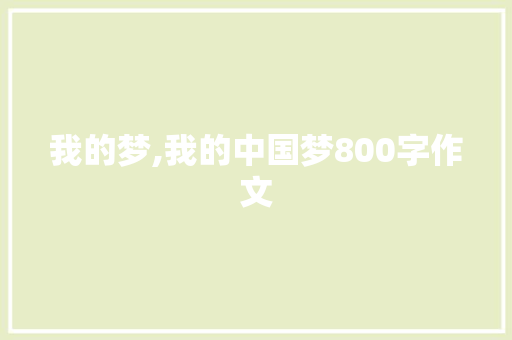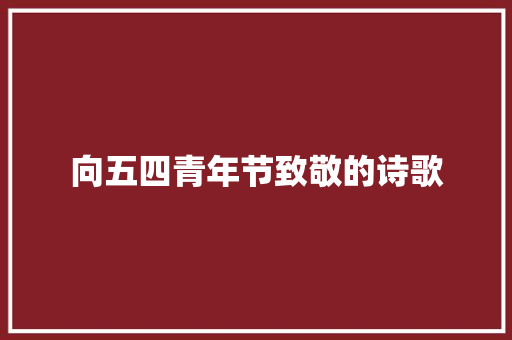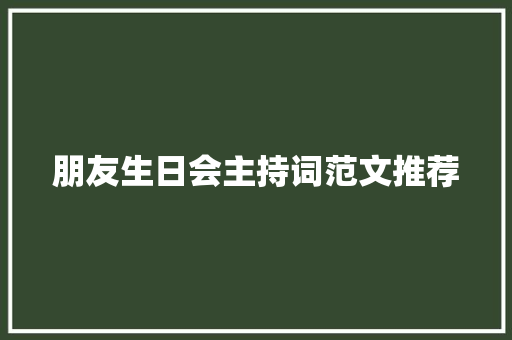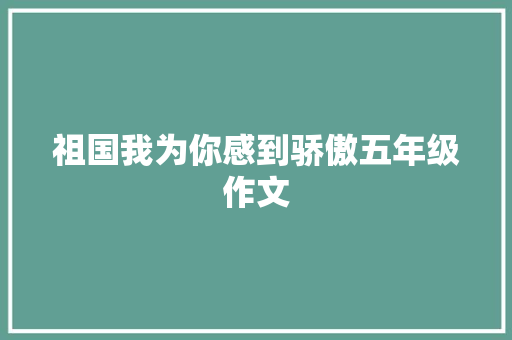若何开始写最初的学术论文,在本日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有什么可说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跨出这一步,实在并不随意马虎,缘故原由可能是历史条件不同。
1951年,金冲及师长西席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那时的他虽然喜好读历史书,但却还没有写过一篇学术论文。1955年,24岁的金冲及师长西席揭橥了他的最初的两篇史学论文。在《经历:金冲及自述》一书中,他谈到自己若何开始写最初几篇史学论文的经历。其内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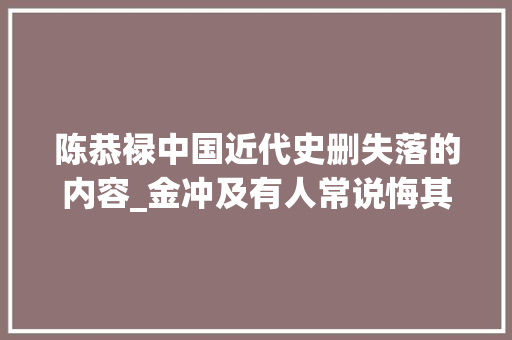
我是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一年复旦文学院和法学院师生六百多人到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参加地皮改革事情。历史系主任周予同教授担当大队长,谭其骧教授等也参加了,四年级学生由于参加土改,都没有写毕业论文。我由于正担当校团委布告被留在学校。参加土改的师生归来后紧接着是“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毕业论文也没有做。只管自己喜好读历史书,到那时却还没有写过一篇学术论文。
若何开始写最初的学术论文,在本日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有什么可说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跨出这一步,实在并不随意马虎,缘故原由可能是历史条件不同。
我最初揭橥两篇史学论文,都在1955年,也便是24岁时候。1952年,教诲部规定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新闻等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那时说的中国近代史,指的是鸦片战役到五四运动那一段历史。教授中专治中国近代史的极少,有些人还持有中国近代史不能算“学问”的偏见。于是,这副担子在各校相称普遍地落到和我同辈的青年西席肩上。
青年西席担负起这门课的传授教化,如果同时要开展专题性的研究事情实在有很多难处:第一,中国近代史在各校大抵是一门新课,处于草创阶段,须要适应新中国的须要,但没有现成的教材,紧张参考的学术著作是范文澜同道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同道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本书可以说勾引着青年西席入行,但并不是教材的文体,范老的书又只讲到义和团运动为止。金陵大学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解放前的“部颁教材”。我在中学时期曾买来读过,这也是我曾报考金陵大学历史系的主要缘故原由,但它究竟已不适宜作新中国的该课教材。各校之间当时可以说没有什么往来和互换。以是,承担这门课的西席,险些全力以赴地从事备课,还谈不上有多少从事史学专题研究。第二,当时刊载史学论文的场所十分少,求得揭橥相称困难。由尹达、刘大年主编的《历史研究》在1954年中期才创刊。此外的史学刊物有天津的《历史传授教化》、河南的《新史学月刊》,篇幅比较少,每期只有几十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集刊》,论文水平较高,给我很多启迪,但彷佛只刊载本所学者的文章,而且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此外,在综合性刊物《新培植》、《文史哲》、《学术月刊》和大学学报等有时也刊载一些史学论文,但为数并不多。高档学校从事中国近代史传授教化的西席,人数不少,但忙于备课,论文揭橥既然相称困难,就顾不上了。第三,当时按教诲部规定在高档学校从事中国近代史传授教化的青年西席,是这方面最大的群体,但彼此长期并无交往,自己无论知识积累和思考深度,都处于起步阶段。读了范文澜、胡绳的著作和罗尔纲师长西席连续出版的太平天国史学考辨著作,都有望尘莫及之叹,一时不敢轻于下笔。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丛刊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但大家都忙于备课,没有多少精力从事专题研究。陈锡祺教授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期间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都大约只有六七十页,已十分引人瞩目了。
回忆起来,1961年的辛亥革命六十周年学术谈论会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事情所起的浸染是不可忽略的。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在外地举行的全国性学术谈论会。到会的前辈学者有吴玉章、李达、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黎澍等,中青年学者有陈旭麓、李侃、胡绳武、汤志钧、祁龙威、戴逸、章开沅、茅家琦、陈庆华、李时岳、龚书铎、李文海、张磊等(李文海与张磊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往后成为至交。会上的热烈谈论和自由交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繁荣和培植。谈论会的论文出了专集。这往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同以前比较,确实发生了重大变革。
《经历:金冲及自述》,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再讲讲我自己最初的两三篇史学论文是若何会写出来的。
1952年院系调度,教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复旦历史系的西席阵营很强,一级教授有周谷城,二级教授有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蔡尚思,王造时六位,还有耿淡如、马龟龄、陈仁炳、田汝康等教授,真是人才济济。但那时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的人十分少,复旦历史系又没有这方面的副教授和讲师,以是这门课第一年由陈守实教授开设。陈守实教授是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他的专长是明清史和中国古代地皮制度史,不能长期要他再担当这门课的讲授。那时,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不但没有教材,连传授教化大纲也没有。就由胡绳武同道(他和我是同学,比我高三个年级,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向来熟习)同我两人边学习,边编写传授教化大纲。1953年,由我们两人分别担当历史系和新闻系这门课程的讲授,内容是从鸦片战役到五四运动前的历史。从此,我先后在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讲这门课(从1953年到1964年),职称在1955年定为讲师。说实话,对付讲这门新课已很费力,顾不上再去做什么专题研究事情。
讲课使自己受益极大。我讲了12年课,只管一贯是传授教化事情和行政事情“双肩挑”。但深深感到有这样多年的传授教化履历和没有这种履历大不相同。当西席的好处,我的感想熏染至少有几点:
一、讲课要在不永劫光内向学生讲清楚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包括有关基本理论,要使学生能够听明白,并且对主要内容留下比较清晰的印象。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这门课程内容的基本脉络线索和内在逻辑;二是今后事情中常随意马虎打仗到的主要知识和学生学习时随意马虎产生疑问的地方。这就哀求任课老师事先充分准备,分清主次,理清思路,记住一些该当记住的事实。不能呆板地只讲一些详细的历史事实,备课的过程,实际上是自己深入学习的过程。如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生自然不会满意。而且,学术研究总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知识和理解也有进步和变革,不能每年拿着老讲稿去讲,总要年年都有所补充和修正。这样的备课自然比自己平时看书所得的印象要深得多,而且养成把个别问题总放在全局中去稽核或同周围其他成分联系起来剖析的习气,既积累了知识,也在头脑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只是大略地就事论事。这就为后来从事研究事情打下比较踏实的根本。
二、西席讲课时是面对学生的,面前是满教室的年轻人,讲话是讲给他们听的,处处都要想到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考虑他们能不能听懂,会有哪些疑问须要帮助他们解答。这门课,我在复旦教了十多年,比较熟习,后来讲课就不带讲稿,主要的引文也事先整段地背熟,上课就像同朋友谈天那样一口气讲下去,当然,和平时谈天不同的是:条理要分明,叙事要准确。这样,教室空气很生动,也很自然。我觉得写文章同讲课一样,要处处替对方着想,由于你写的是准备给读者看的,不是自己关在书房里写给自己看的读书条记。教书一定要处处都想到那是讲给学生听的,要为他们着想不是自言自语。这是没有当过西席的研究者不随意马虎强烈地感想熏染到的。我当过几年校团委布告,那时政治活动多,须要向团员和学生讲话和作报告,在这方面也是受益不少的。当然,现在常向听众作学术报告的研究者,也会有这种觉得。
三、做西席还有一个“传授教化相长”的主要好处。一些书读得多或长于思考的学生,对问题常会有很高明的意见,是西席原来没有想到的。常同学生打仗,思想就更生动,更随意马虎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这比总是一个人苦思冥想,乃至会钻入牛角尖里还拔不出来要好得多。我在讲课时曾采取一种办法:当涉及某个比较繁芜或主要的问题时,停下来请同学们举手后起来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当几个同学揭橥见地后,我再总结一下,在总结中自然也包括并接管了几个同学发言中谈到的意见。1957年,我同胡绳武同道第一次互助揭橥的关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那篇文章,本色便是我在一次教室谈论(那时叫作“习明纳尔”)中,对许多同学揭橥各种见地后的总结。我同胡绳武同道平时常常就一些学术问题谈天制定条约论。那次课后,我同他谈到那次总结的内容,他又谈了一些意见。我就以两人署名的办法在《文申报请示》(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在《学术月刊》)上揭橥了。这是我们俩互助写文章的开始。实在,那次的文章中也包含一些同学发言中的意见。平时,同学们听课后提出的问题和揭橥的议论,也使我受到启示,思路得到开阔。
还须要讲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有着不少精良的学生。听过我课的同学中,如朱维铮(1956年入学)、李华兴(1957年入学)、姜义华、王学庄与王知常(1958年入学)、王守稼(1939年入学)、张广智、王鹤鸣、朱宗震(1960年入学)等,他们后来在不少方面超过了我的造诣。如当时在史学界产生过不小影响的同班同学姜义华、王学庄、王知常入学不久就互助写了一本《孙中山的哲学思想》,署名是从他们三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合成的“王学华”。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研讨这个问题的著作,引起不少人把稳,打听这位没听说过的作者是哪个单位的,没想到是三个一年级大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我的促进浸染不言自明。
但讲课的头两年多,我险些全力以赴用于备课,一篇史学论文也没有写过。它的缘故原由前面已经说过:一来是传授教化的包袱很重,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边学边讲,已经穷于搪塞,哪里谈得上再做什么专题研究?二来是当时传授教化的紧张参考书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为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中的紧张问题都已说得很清楚,自己一时提不出还有什么问题须要研究。三来是那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除太平天国历史有简又文、罗尔纲、郭廷以、谢兴尧等师长西席有专著外,其他研究成果还很少。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第三研究所《集刊》揭橥了一批很好的论文,当时使我感到线人一新,可惜的是这个刊物出了两期就不出了。以是,纵然自己想做些专题研究,一时还感到无从下手。这对本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彷佛弗成思议,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这种稚子状况当初相称普遍。
我写的第一篇史学方面的文章,是揭橥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的《对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见地》。写这篇文章的缘故原由是:胡绳同道在《历史研究》1954年的创刊号上揭橥了一篇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影响十分大。他写道,“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期间的标志”。我已经教了一年多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分期的标准该当是将社会经济(生产办法)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稽核,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发展各个阶段中的详细特点”,并且就此对中国近代历史该当如何划分阶段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写这篇东西时,本来并没有想把它作为学术论文来写。只是在1955年春节时在办公室值班,用一天韶光写成的。当时年轻,刚满24岁,还有一股“初生之犊”的劲头,有什么不同想法就想说。写得还很长,就寄给《历史研究》,就像是一封比较长的读者来信,以是用的题目是《对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见地》,寄出了就了事,没有想是不是会被揭橥。实在,文章中有不少稚子的地方,而《历史研究》编辑部却很快就把它揭橥了。除删掉原有的一句“胡绳同道是我尊敬的前辈”外,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当时定期出版的史学专业刊物很少,除《历史研究》外,只有天津的《历史传授教化》和河南的《新史学月刊》,而且篇幅都很短。此外,《新培植》《文史哲》《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文申报请示》等综合性报刊上也有一些史学的文章,当然不会多。因此那篇文章在影响很大的《历史研究》上揭橥后,反应还不小。我同史学界不少朋友的“笔墨之交”便是从此开始的。
还要说到,胡绳同道丝毫没有因此见怪,一贯对我特殊好,这真表现了大家风姿。
这篇文章揭橥后不久,忽然接到中国公民大学举行校内学术谈论会的约请信。当时这类有外地学者参加的学术谈论会十分罕见。复旦不算闭塞,我在这以前却没有到外地去参加过学术谈论会。公民大学的约请信也没有说会上准备谈论什么问题。到那里后才知道,会议重点是谈论戴逸同道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文章中有很长一段是同我商榷的。因而有一个提到我名字的小标题。后来,我还同戴逸同道开玩笑说,我的名字用四号铅字排出来这还是第一回。会上我临时也作了一小时的答辩,大意是两点:第一,把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稽核,不是二元论,如从鸦片战役到太平天国失落败这段韶光,中国已走上半殖民地道路,但还没有涌现成本主义近代工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紧张只能是太平天国这样的旧式农人叛逆;这往后,海内的成本主义工业开始涌现,但力量还微弱,就涌现了改良主义思潮,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末,民族成本有了较大发展,新知识分子军队扩大,就有了辛亥革命。两者须要也该当统一起来稽核。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常日是渐进的,很难以哪一年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尺,因此常日可以用阶级斗争的主要事宜作为划分期间的界标,但不是历史分期的标准。会上也没有说谁是谁非。对这次谈论情形,《历史研究》又发了一篇比较详细的宣布。从此,我同戴逸同道便成为可以无话不谈的石友。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他当了十年中国史学会会长,我一贯做赞助他的副会长,往后又接续他当了六年的会长。多少年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抵牾,这也是当时十分良好的传统。
我写的第一篇可算学术论文的是《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抵牾》,揭橥在《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上。它同前一篇文章是同一年写的。为什么挑选了这样一个冷僻的题目?这也有段故事,缘故原由正在于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动手做学术论文。
那时,全国高档学校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的,只有北京大学的邵循正教授一人。他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好几位比较出色的人才,如李时岳、张磊、吴乾兑、赵清等。我就问复旦派去北大学习的戴学稷:邵师长西席是若何带研究生的?戴学稷说:他哀求研究生先坐下来系统地存心读篇幅很大的、收录晚清外交事情文献的《筹办夷务始末》,从这里动手,再扩大阅读有关的原始史料,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文稿,找出故意义而过去研究不足的问题,写出论文,把问题说清楚。这话给我很大启迪,于是依样画葫芦,就找出成为《筹办夷务始末》续编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地读。由于过去没有这样系统地读过主要的原始史料,也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成见,读起来都以为新鲜,创造晚清这段韶光内有关中外问题的许多事都同英俄在中国抵牾的须要有关,日本在甲午战役后一步步扩大侵华也同英国以前的对付沙俄在中国扩展的抵牾有关。接着,再进一步读有关原始资料,用来考验初步形成的意见是否符合实际,创造不符合实际时就推倒重来,如果以为大体符合实际就连续论证和加以充足。这样的论文,自然仍很稚子,文章主题也小,但毕竟是学步时跨出的第一步。而且因此原始史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独立地进行剖析,这路子是对的,并且养成了习气。如此走下去,再在实践中不断对论文如何写浸染心总结,对的坚持,不对的改进,对自己往后在学术研究上的上进是有益的。有人常说“悔其少作”,我却不悔,有如摄影本中不必把童年学步时的照片涂改或撕掉,由于这是历史的真实。
第二年,也便是1956年,我又在《复旦学报》上揭橥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一文。“护国运动”便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武装叛逆。它的发动者过去有各类说法,如: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等等,各说各的。我根据当时的原始史料,认为叛逆真正发动者是受过辛亥革命熏陶的云南新军一批中下层军官。后来,我听李根源师长西席的儿子、全国政协委员李希泌师长西席见告我:当年他父亲看了这篇文章后,很夸奖。李根源师长西席在清末时是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的老师),后来又是护国运动的总参议。他对我那篇论文切实其实定自然使我很欣慰,也增强了信心。当时我写文章不贪多,大体上是一年写一篇,力求每写一篇比以提高一步。这比写得很多而总在原地踏步要好。
末了,在复旦的发展过程中,还得讲讲我同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由于这也是在复旦历史系时起步的。当我最初从事史学写作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北洋军阀等的文章都写过,后来就把力量集中到辛亥革命研究上来。
为什么这样?由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资料实在太丰富。前辈史学家陈垣教授提倡对历史资料的利用要做到“竭泽而渔”。这对某一段古代史或某个专题来说,大概能够做到,但浩如烟海的近当代史资料却只能使人有“望洋兴叹”之感,除某些专题外,哪还敢讲“竭泽而渔”。怎么办?想到毛泽东同道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面面俱到,想谈许多问题,结果哪个问题都难讲清楚,还不如集中力量选一两个有代价的问题,多花点力气,下点苦功夫,把它说得比较清楚一些,使人看后多少有所得。
以是我和胡绳武同道在共同再三切磋后,就把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集中到辛亥革命上,在我们合写的150万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后记中还特地声明:“紧张的着眼点是想稽核一下: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落败的全过程是若何的。我们并不企图把它写成这个期间的中国通史。因此,全书的大部分篇幅是用在阐述和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发展和它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上。对这个期间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清朝政府的状况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只作为它的背景,做一些概括的解释,没有很多地展开。”这未必是最佳方案,只是根据我们实际力量所说的诚笃话。这部书后来得到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我想,既尽力而为,又实事求是,可能是比较恰当而切实可行的。
从复旦期间开始,几十年内,我长期地和胡绳武教授互助写了几部书和几十篇论文。我们两人在1947年起便是复旦大学史地系的同学,那时我是一年级学生,他是四年级学生。1952年,复旦历史系成立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我们两人都是它的成员。往后几十年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无论书本还是论文,险些都是互助完成的,直到1990年共同写完《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关于这个话题,我写过一篇纪念胡绳武同道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要讲到,除教文科根本课外,1981年我还教过五位中国近代史的“副博士研究生”,个中鹿锡俊后来成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后,我又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培养过一些中国近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博士研究生,这里许多人在学术上都有了很好的造诣,如复旦大学的汪朝光、唐洲雁、陈扬勇、迟爱萍、黄崑、马忠文,北京大学的张海荣、易丙兰、李秉奎、邓金林等。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大多是本着已有相称研究根本的问题来确定,辅导方法紧张是相互间的对谈谈论,因此,彼此的感情和传授教化相长的感想熏染也更突出。1998年1月至7月,我还担当过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同日本同行等学者有了较广泛的学术互换和友好交往。
话越说越远了,就此打住。有些地方已超越本文题目的范围,最初那两篇1966年前写的文章相称稚子,只是学步,本日也已没有多少代价,但本书的书名是“经历”,那么,同这个书名有关的主要事实(包括探索过程中成功和挫折的体会)彷佛仍可以聊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