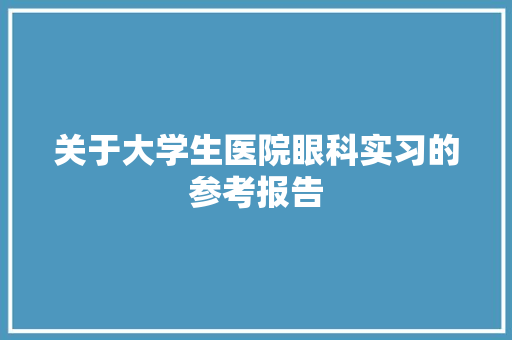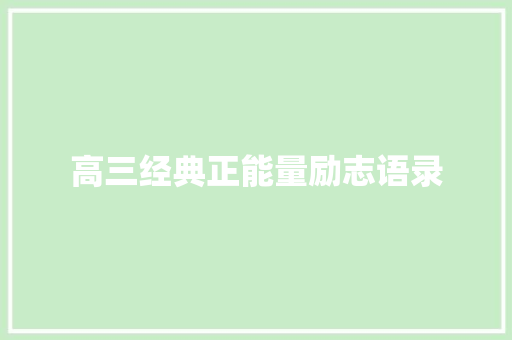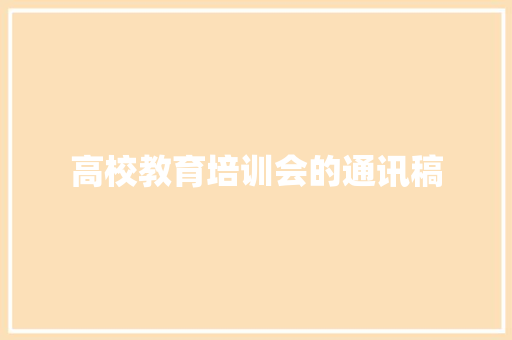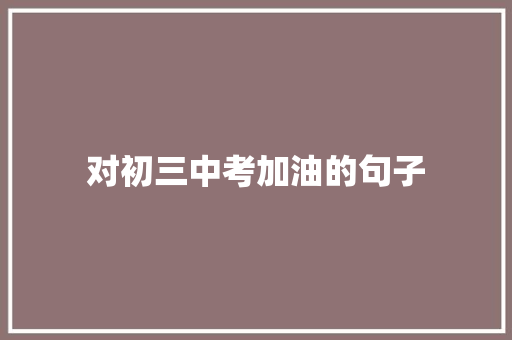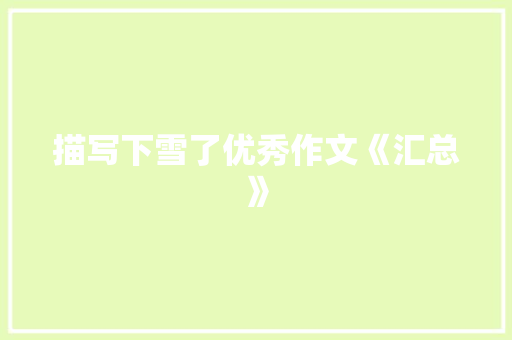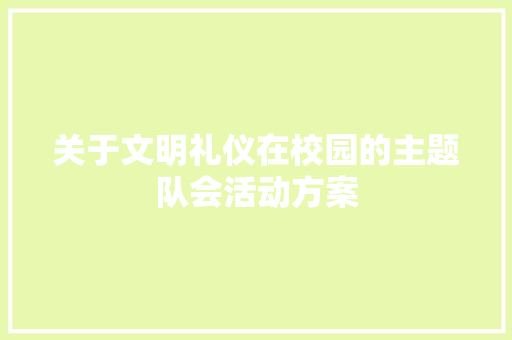这种认知该当不是与生俱来的吧,应是从大人们的言语表情中学习所得。而大人们的认知则该当是来自于一种崇尚白的文化,所谓“一白遮三丑”,还有“白里透红,分歧凡响”,及至现今的“白富美”。这也让我好奇,明明我们是黄种人,为什么会认为白便是美呢?而在自然界,我们并不认为白便是最美。我们看绿叶红花很美,青山绿水很美,碧海上苍很美,可是,如果我们的肤色是那样的,却不会认为那是美的。
器物也是。粉墙黛瓦之以是美,不仅仅只是有洁白的墙,还有青黑的瓦。台北故宫所藏的白玉苦瓜当然很美,余光中说“钟全体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可是翡翠西瓜也不赖,慈禧太后去世了都拿它陪葬,孙殿英又盗走,如今都着落不明。白衣飘飘固然不错,但锦衣华服却是色彩斑斓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画笔则大都是彩笔,况且历史上还有个美女墨客薛涛,以芙蓉花汁,制成深赤色小彩笺,这种薛涛笺乃至比她的诗和仙颜还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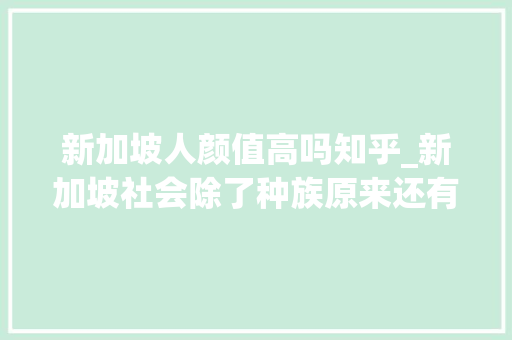
在浩瀚的色彩中,我们唯独对黑比较抵触。我们说黑店、黑幕、黑市、黑手、黑话、黑客、黑心肠、背黑锅、黑恶势力、阴郁的旧社会,都不是什么好词,只有“一枕黑甜”说的是睡觉惬意,由于好就寝不能有光芒侵扰,可以与甜美挂钩。但一觉醒来,就说“黑夜给了我玄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探求光明”。白山黑水语含褒义,可那个意思不是白色的山和玄色的水,而是特指长白山和黑龙江。人的皮肤也就千万不能黑。
究其原委,我以为这与行业分工有关。自古以来,大抵在阳光下暴晒的职业,总是处在社会底层,干最脏最累的活,过最穷最苦的日子。听说后来翻身做了主人,但工人还是倾慕坐办公室的,农人还是倾慕站柜台的。站柜台的便是现在我们说的售货员,也不是什么高层,但毕竟比农活轻松,收入也高些,最关键的是还不晒太阳,皮肤白白嫩嫩。虽然有指示说农人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反而最干净,但鲜有官家少女嫁给他们。
这种文化催生出来的大众偶像,古代一样平常是白面诗人,当代则是奶油小生。过去说才子配佳人,英雄配美女,总以为才子还是比英雄更受欢迎,由于佳人总是比美女还高一个档次。样板戏时兴的年代,虽然不讲颜值,但杨子荣总是比座山雕白净好看。后来改革开放,小白脸走俏,就有人呼唤高仓健,那是东瀛银幕上的一个硬汉形象。这种呼唤不仅没有任何效果,事到如今反而越走越远,小白脸摇身变成了小鲜肉,这些个花样美女,摇着兰花指,扭着小蛮腰,油头粉面,撒娇卖萌。
而新加坡的泳池边,却总是有很多白人男女在烈日下暴晒,他们彷佛并不喜好这一身的白皮囊,非要把它晒成深色才好。还有不少的华裔男青年,也在那里晒。我曾经和一个帅哥互换,他居然也说皮肤太白了不好看,黑一点显得更阳光,更康健,也更美。我还看到过一些很俊美的黑人青年,他们五官端正,身材健美,黑得实在很好看。这些都与我从前的认知大相径庭。
有一个黑人帅哥尤其让我印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在一条小路上徒步,劈面冲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黑人男青年。他冲着我大叫大囔,还用他的一只很长的手臂比划着。我不明就里,站在一边看着他傻笑。他与我擦身而过后,依然转头对我大喊大叫,连续用手比划。我依然站在原地,看着他频频转头,频频比划,一欠妥心,迎头撞上一棵树,瞬间人仰马翻。他从地上爬起来,折回来。我心想坏了,只怕是来找我麻烦了。未曾想他居然是来用蹩脚的中文见告我,行人该当靠左走,否则有些危险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新加坡的交通规则与我们不同,也是第一次见识黑人原来这么俊朗,还友善助人。
回忆起儿时关于白菜腊菜的趣事,我不仅哑然失落笑。由于我本来容貌平庸,身材也不高大,就算肤色再白也是白搭。不过我早就有了自知之明,也就不在意肤色深浅了。自从迷恋上户外徒步,我的皮肤就逐渐加深,特殊是新加坡的赤道烈日,没几天就把我晒得像个马来人了。我当然无所谓,但实话实说,我却以为人家黑得好看,我黑得丢脸,从前皮肤稍白,多少还有一点书卷气,现在搞得黑不溜秋,不伦不类了。虽然我并没有太多的外面焦虑。
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种错觉,这让我想到美真是一个繁芜的问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至少我们中国人在肤色的审美上与人家大为不同。我个人虽然对白肤之美有所质疑,但我还是不习气、不喜好自己那种黑咕隆咚的面貌,并没有从传统认知中解脱出来。这当然也无关紧要,人家以深色为美,我们以白色为美,用费孝通的话说,便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紧要的是我们呼唤的男性气质到底是什么?我们鄙视嗲声奶气,但清洁卫生、衣冠楚楚、举止文明、谈吐文雅却是必需;我们崇尚阳刚之气,但精细、细腻、温顺又何尝不是多元化男性美之一种。过去我们每每忽略外表美,说那是布尔乔亚或是“变修了”,但美丰仪是上帝的奖赏,帅哥总比挫男更让民气旷神怡。如果你是一位女子,你是选择林冲还是李逵?或者你不喜好武夫,而心仪文士,那你是爱潘岳还是张载?都是才子,美女潘岳每行于道,妇人都连手共萦,把果子投给他;而张载丑态堪憎,人家则以石掷之。
我们每每喜好矫枉过正,情由是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但过正总不是一种正常征象,过正之后还是要回归原位才好。现实是我们一次次矫枉过正,一次次滑向两极。说要看重仪表,他就来个靠脸用饭,矫揉造作,娱乐至去世;说要强调精神,他就搞得五大三粗,不修边幅,邋里邋遢;说要干革命,他就样板戏里男的没老婆,女的没老公,男女服装归于一统,革掉性别差异,扼杀人性与俏丽。过去是女人像男人,现在是男人像女人。
很多人对此咬牙切齿,大加训斥。尤其是对那些脸傅厚粉、搔首弄姿的男星,特殊看不顺眼。而他们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如痴如醉的粉丝。人们从忧心于大众偶像的女性化,上升到了忧国忧民的境界,认为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就会失落去战斗力,失落去原创力,失落去开拓进取的勇气与精神。厌恶之际,还送他们一个娘炮的蔑称。听说掩护妇女权柄的有关部门曾经哀求禁止这种称谓,说是对女性的歧视。但把有些女强人称为男人婆,却没听说是对男性的歧视。
我虽然也不认可这种娘炮男星,我也很少关注他们,不过我倒是思考过这种娘炮征象产生的缘故原由。时期发展到本日,我们已从农业文明走到工业文明,又从工业文明迈向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各种体力劳动乃至脑力劳动都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就连战役都已经改变了形态,那种单一的刚健粗犷之美,可能难以再成为时期的主流。不过在小白脸与大老粗之外,该当还有更丰富多元的美学元素,康健英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都是自己的选择。当代社会应有更宽广的审美场域,我们须要的可能不是痛斥,而是尊重和原谅。
生命之美,更为主要的,还是代价不雅观的塑造,是人生的克意精进,是个体的自主自强,是腹有诗书,是见识超迈,是才干卓越,是内在的热血、豪情、勇气和担当,是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的升华,是对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情怀与任务。而这种男子汉,正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极度稀缺的,他们才该当是全民瞩目、万众敬仰的明星。至于肤色的黑与白,那就太肤浅微末了。
END
(感谢诗与歌的旅行公众年夜众号授权转载,作者:蔡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