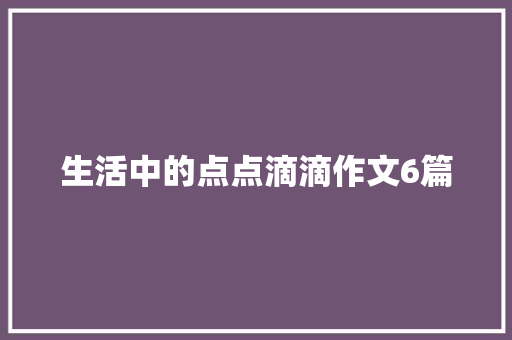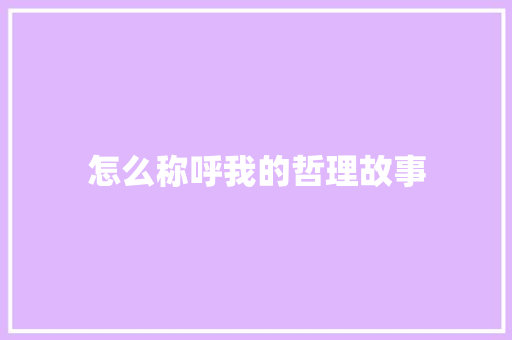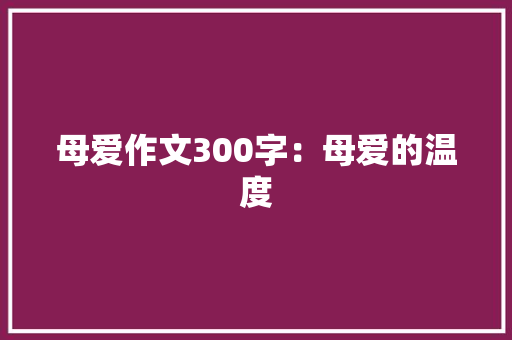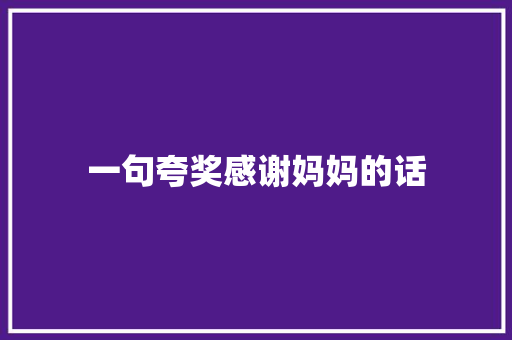我手头有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大约是二十岁左右拍的,穿着一件有细碎花案的布衣,面颊丰润,明眸皓齿,灿若晨星,一头乌发瀑布一样流泻在胸前。母亲年轻时保留下来的照片很少,基本上毁于文革,这张是后来从亲人那里索回的。

我停止了咀嚼,我的眼睛湿润了。透过泪光凝视着母亲。母亲像一座大理石浮雕,母亲的眼神像圣马利亚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一个儿子的心头。
在如潮涌动的哀思中,时常想起慈母在我身边最后的一段时光,真的很开心,很欣慰!仿佛上天眷顾我,一生倔强孤傲的母亲,竟然会离开熟住的老宅,搬来与我作伴!我一时兴奋莫名,简直太有成就感了!
在这样的时节里,我除了怀念母亲,还能去体会些什么?在这样的怀念里,我除了伤感,还能倾诉些什么?在这伤感的时节里,我除了倾诉,也只有倾诉了。
母亲的头发如雪一样白,岁月在母亲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痕迹。
看着母亲,我愣住了,灯光下映出了母亲瘦弱的身影,那佝偻的脊背,是为我弯的,那疲惫的神情,是为我留下的,还有那一双龟裂的手,也是为了我的生活而操劳的,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在瑟瑟的秋风中,我呆住了,站了很久很久。
妈妈,高高的个子,鸭蛋脸上有一个端正的鼻子。眼角上有一个端正的鼻子。眼角上爬上了隐约可见的几条鱼尾纹,但眼睛里还透露出一股灵秀的神采。
妈妈,临别时您到车站送我。看着您,我忽然感到一阵难过。您是四十岁刚过的人,可是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了,脸上也爬上了皱纹。这每一根白发,每一条皱纹都是您为工作为子女费尽心血的见证啊!
妈妈三十五六岁,生活的重担使她过早地失去了往日的绰绰风采,粗糙蜡黄的皮肤,夹杂银丝的头发,使人觉得她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母亲苍老的面容,就像隔天了的菜叶子,布满皱纹!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将母邗沟上,留家白邗阴。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
妈妈,那一年你突然离去让我心力交瘁悲痛的我,只能每夜走进梦里去扑捉你的颜容寻觅你的踪影
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但当我想到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个的时候,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
我是在什么地方呢?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儿弄不清楚。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门,走了进来,橘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于是我又想了开去,想到哥廷根的全城: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的古旧的城墙,斑驳陆离的灰黑色的老教堂,教堂顶上的高得有点儿古怪的尖塔,尖塔上面的晴空。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得,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仿佛从云堆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儿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但终于向我走来了。
窗台边殷红的茶花,在滴滴嗒嗒的雨声中,缓缓地沉重地绽放。我走到窗前,看着模糊的窗外,听着淅沥的雨声,忆起了那熟悉而久违的声音。哦,那是母亲的声音。好想好想再听听母亲的絮絮叨叨——可惜母亲已驾鹤西去!
看着母亲的照片,有时会想,青春真的易于流逝,倏忽之间,岁月让容颜老去,如草荣草枯,已是一秋。
母亲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深深期盼的光芒。这期盼,寄托着母亲的全部心愿:明理有为成人,那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
母亲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无比幸福的光芒。这幸福,是一种为使儿女免受苦难的幸福,是要把母亲的乳汁血和爱全部灌到儿女身上的幸福。
母亲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最大满足的光芒。这满足,比她自己的满足更充实。这满足,是一种全身心的付出,是一种生命的闪光。
母亲的一生,是最平凡的江南女子的一生。生命之消逝,不会有太多的人记得。但对她的儿女们来说,却是一生的记忆,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母亲已经走了,留给我深切的怀念,怀念那永远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