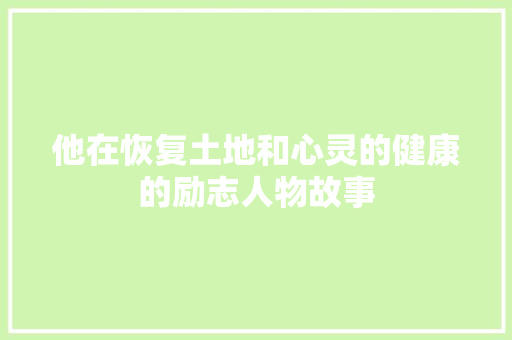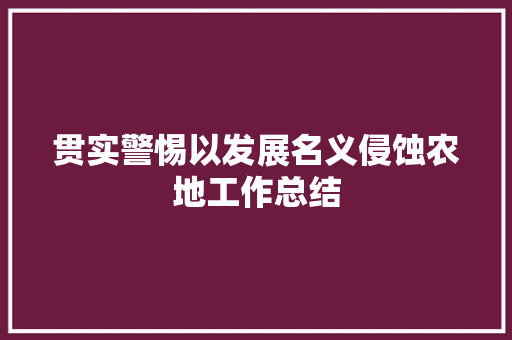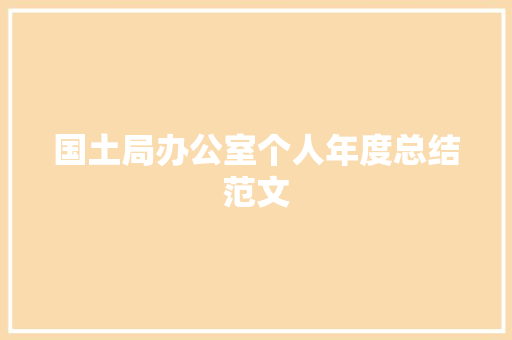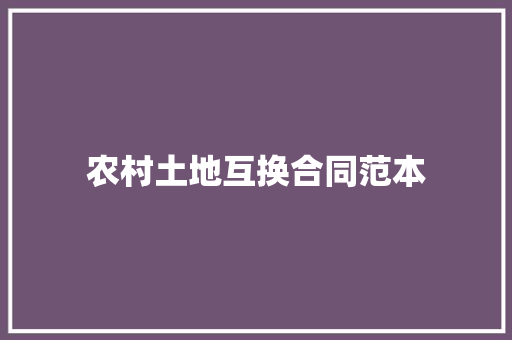奶奶家在东郊,房子带着一个小院子。院子的中央是一棵石榴树,我是极喜欢在树下玩耍的。树下是一个充满乐趣的冒险岛。蝈蝈、蚂蚱、蚯蚓,是土地馈赠给我的礼物。还有可恶的蛤蟆,亦是土地给我的惊喜。
它的叫声曾令我心惊,于是我“鞭其数十,驱之别院”。骑着大白鹅冲锋陷阵,是我的拿手好戏,我玩得不亦乐乎。有土地宽厚柔软的胸膛,我不怕摔倒,反而乐意四脚朝天,名正言顺地躺在它的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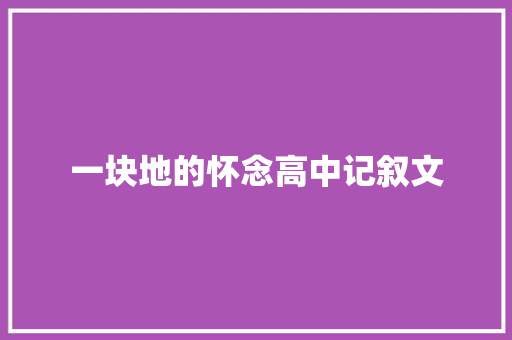
这座小院子背后,是几块庄稼地。土地是魔术师,一年四季,花样翻新的表演,让你眼花缭乱。栅栏外面的庄稼地春夏长稻米,稻米收割前套种玉米,有时又种茄子,还不时地出现西红柿。田头地垄里,你会惊喜地看见绿豆、红豆、四季豆、芝麻,倭瓜、南瓜、丝瓜也会不
期而遇,如果“刨根问底”,还会有落花生和土豆宝藏。
在我的记忆里,土地永远不会失去颜色土地的颜色就是庄稼的颜色。
春天,奶奶插下秧苗,土地就穿上了绿衣,是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绿,绿得神秘;夏天,因为西红柿的加入,土地变得热情,炽烈地燃烧;秋天,我最爱的就是秋天,秋天的土地是盛装登场,衣着不再单调,南瓜、玉米的黄,红豆、西红柿的红,茄子、芥菜的紫,绿豆、丝瓜的绿……土地被装点得如彩虹般绚丽,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娘在硕硕果实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冬天,土地本色亮相,暗黄的色彩,昭示着沉稳的性格,也预示着来年的丰收,看似平静的表面下,一切蛰伏在土地内部,来年的生命在孕育。
我行走在田间地头,看到的总是庄稼的事,听到的总是庄稼的私语。
稻米抽穗,茄子、西红柿挂满枝干,绿豆、红豆的苗棵发蔓拖长,芝麻开花节节高,粉色白色的花一簇一簇的。倭瓜开了一朵花,结了一个瓜扭,玉米溢满篓子,稻米灌鼓了麻袋,人心抹了蜜般的甜。那棵石榴树更是开得火红,红色在枝头流动,红得让我忍不住猜想,那灰色的麻雀一头扎进石榴树中,再出现时就应当是红色。庄稼的丰收,石榴花的怒放,空气里热烈蒸腾的气息,炙烤着我,让我着迷;植物动物的密语,让我倾心。蒲公英说,它要远行,做风的孩子;毛毛虫说,它要蜕变,做美丽的蝴蝶;杨树说,它要生长,做笔直的标杆……
庄稼、土地,就这么静静地待着,阳光照遍,月光洒满,星星看过,风儿拂过,雨儿洗过,蝴蝶飘过,虫儿叫过……
我亲近庄稼,融入它们的生长、繁衍,也悸动于生命的腾跃、奔跑和飞翔。我爱土地,看一眼这土地,内心就有了春色,是那种生的底色,也是心的底色。可是啊,曾经环抱过我的这片土地,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早已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下,不可复识其面目。城市这个浑身长满水泥钢筋和玻璃碎片的庞大怪物,不断吞噬、咀嚼它触手可及的土地,它把冰冷强硬的机器手伸向了奶奶的庄稼、土地,伸向了我的乐园,伸
向了我心灵的绿地!庄稼地周围插上了刺眼的五彩旗帜,钢铁战士伫立成军,马踏黄土,浩荡而来。庄稼像一个弱女子遇到残忍的强盗,马上溃不成军,支离破碎。土地的肌肤被划开,钢铁的骨骼强行植入,柔软的臂膀变得冷硬,不再温和,不再纯净。几只挥动的机器手,就这样将冰清玉洁的土地蹂躏。
巨资搭建的高楼最终在这里安营扎寨,野蛮殖民。面容冷漠的人们匆匆进出于丛立的高楼,为虚无的金钱、名利奔走于一个个封闭的空间,源源不断、前赴后继地奉献上自己迷失在金光涣散的时代里的灵魂和肉体。耸立的玻璃幕墙借着太阳的光芒耀武扬威,射向那一张张冰冷生硬的脸庞;道路两旁的绿化树憔悴低眉,原本鲜活的绿色,因城市的囚困而黯然消逝;汽车往来游走,土地失去了原来庄稼具有的纯净的植物气息,到处弥漫着失序放荡的金属味道。
美好的记忆只存在于最后伫立的玉米秆。土地失去了庄稼,农民失去了根,心灵的绿地也荡然无存。一块地,失去了庄稼,它的本性就泯灭了;一个人,失去了心灵,他的灵魂就消散了。肥沃的土地堆满沙砾,满眼的庄稼再无踪影,到处是钢筋混凝土的世界,到处是坚硬的地面与迷失的人心,土地、庄稼在现代的物欲面前痛苦而绝望地挣扎,道德、人性有的在罪恶的金钱诱惑下理所当然地消泯。
我不知道受伤的地什么时候可以疗愈伤痕,我不知道心灵的绿地何时可以复归还原。即使复归还原,迷失的心还可以纯净无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