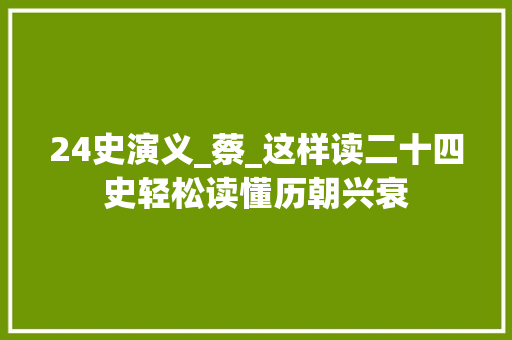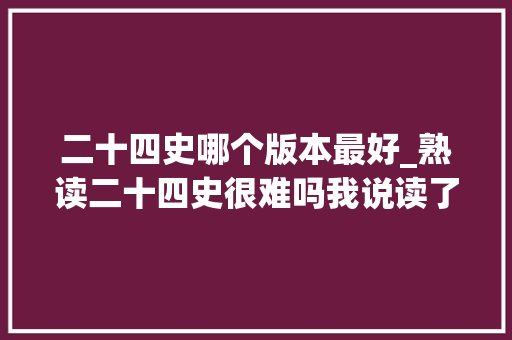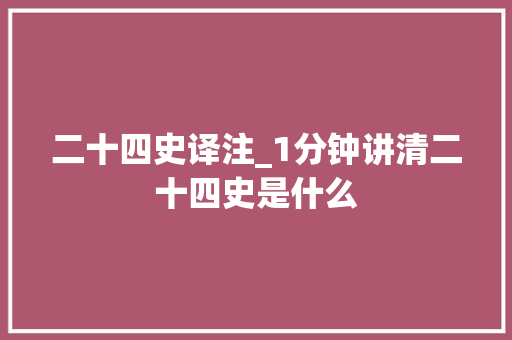丰泽园书房,占数最多的,听说便是“二十四史”
所谓“二十四史”,是过去中国人,对所有皇家钦定的“正史”的简称。从汉代《史记》,到清初修纂的《明史》,共有24部。韶光线索上,起自无知传说的黄帝(约前2550年),直到大明崇祯17年为止(1644年),皇皇五千年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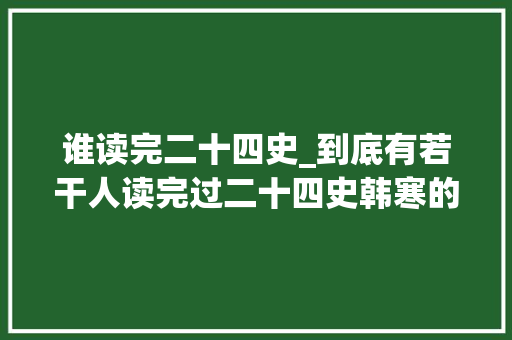
论字数,据统计约有4700万字。密密麻麻的字行,基本上席卷了中国数千年的公事秘辛,乃至五岳四渎、城阙翰仪、天地人文、日月星辰。人间间有几部这样的书?它一定是研史必经之路,馔玉炊金,舍此无二。“正史”之正,是正规之正,也是正途之正。
钱穆:“所谓中国,是文化中央之国”
对付这批坟籍,历代读书人,都是不敢轻心掉之的,开卷即益,能读则读。探旧迹,弄词章,不雅观风气,察景象,施权谋,鉴得失落,每每都从这里起步,听微决疑,澡雪深造。
可是,要读完这几排书,是个繁浩的大工程。我们看如今稍大点的市级新华书店,也都会有展售,基本都是摆列为满满特大一柜子,犹如一堵厚重的宫墙。
像我本人,论龄已直奔中年,依然念念记得,初次重逢这座白纸黑字所垒的历史圣殿的情景。那时,还在上初中,在福建小城龙岩,九一北路121号新华书店,这批书本寂然伫立在落地玻璃窗右侧,中华书局版,绿皮繁体竖排,琳琅夺目,摄民气魄。
每逢周末,骑着破自行车入城,都似蜂蝶误入烂漫花丛中,书眼相对,摩挲再三,倾慕难舍。想那时,午后的落日斜溢而入,岁月辉光,人书俱奋,真有胡兰成所吹嘘“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表面风雨琳琅,满山遍野都是本日”的觉得。
还记得,总价要2000元旁边。彼时,家里太后钦赐零费钱,一周不过三五块,是惊为天价的,只有咋舌敛缩的份。心中歆羡,久蓄于怀,乃至曾形之于梦寐,总胡想着自己快点终年夜成年,好有能力搬回家中,享受书城坐拥之乐。
如今的新罗区新华书店,我已十多年未过故地
可叹及壮,饥驱四方,至今还是奢求,而少时的痴想,也早已在庸凡生活零散风尘的堆积下,逐渐漫漶不清。
如今看来,“二十四史”不过常听常见书。林语堂在文章中称之为“大路货”,意思是如大白菜般,唾手可得。
可在古代中国,虽然印象中古人多见闻广博,彷佛无书不读,可对付“二十四史”能够达到“常见”这个地步,而且有条件读完所有正史的,实际还是屈指可数的。
当代史家黄永年,藏书敢与上图竞争,读书宏富,可也自认没读完二十四史,且说无此必
要知道,“二十四史”足有四千万字,这是啥观点呢?搬句套话,差不多便是“学海书山”。曾有好事者统计过,假设一个人逐日读数万字,一年读365万字,他需将近11年,才能全套读完一遍。以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历史上能做到这个地步而且有条件完成这个目标的,实在不多。归结起来, 紧张缘故原由我揣测至少有这么几点:
其一,最直接的道理,“二十四史”出全较晚,末了一部《明史》,待定稿已是乾隆四年。如此,按照“读完”哀求,已可以打消古人十之八九。
其二,清往后读书界也盛行“专业主义”,不是那个专业的,多不会去读。比如乾嘉学派的真正开山戴震,读书之多之精当世少匹,不止“十三经”文本全能背诵,且“注”也能张口就来,只有“疏”不完备牢记,只管如此,据《戴震集》的隐约透露,个别如《宋史》,他就读的不多。
安徽黄山市屯溪隆阜街戴震纪念馆
其三,过去人“读”的观点,与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所谓“读”,说“抠”更得当,必是细读精读。以是,出自《后汉书》的有名故事:“《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说的是,东汉首席学问家、汉学大师马融,这位庄墨韩一样平常的人物,都不敢说能读明白《汉书》。 他们所讲的“读”,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弄透彻。
其四,旧时没有图书馆,想读没有硬性条件。举个例子,到了清中叶,大学者章学诚的好基友汪辉祖,40岁多岁了,才有能力买得起一部史籍拿来读。而汪辉祖好歹也是做过县长的士绅地主。以是,古人要读书,真是不易。郁达夫《自况》诗中所谓“绝互换俗因耽
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清史稿,289册,最通畅版本
再比如,大师焦循,这位乾隆朝高官阮元的同里同学、学友兼姻亲,看他《雕菰楼集》自述,为买《通志堂经解》这部书(现价约3000元公民币),不仅卖掉良田数十亩,还变售了老婆陪嫁金簪,才换得回家研读。单反穷三代,爱书毁生平,真是惨淡。
也以是,明人沈佳有段话很盛行,似也可代表着过去多数读书人的不雅观念与实践:“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设复如宋人制科出题兼及十七史,不亦难乎?记诵繁居,足为心累,抑目力鲜及。吾人史学,大抵《通鉴大纲》与《文献通考》两书足矣。”
焦循,1763-1820,江苏扬州黄珏镇人
这话见于《明儒言行录·原序》,告诫的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之弊。用大口语翻译,便是读书要实事求是,装逼有害康健。
可较真求证起来,“二十四史”或说并世所有“正史”,真正读完一趟乃至多遍的,的确不乏其人。紧张齐集在清代康乾以来大咖中。
读完所有正史的,就我眼目所及,明之前文献不见有人申明、或揄扬。只是迟至17、18世纪,整套的正史读完的,开始陆续涌现,并且紧张集中在江浙地区。推测缘故原由,当是由于当地的书本刻印、流利,以及藏书家、图书馆是海内最为突出的,高端读书人又荟聚,也就有了条件完成这种高负荷、高难度、高水准的读书工程。
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存最早的私家图书馆,堪为明清江浙图书馆代表
在过去,黄宗羲是读完《明史》前二十一史的。由于其父黄尊素,在受到折磨致去世前,曾留下遗言,叮嘱他要博通经史,“不可不通经知史”。于是,青少年时期的黄宗羲,秉承父训,坚持两年,从天色初起(约凌晨4点旁边)到鸡鸣(当为6点半前后),“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逐日丹铅一本”,逐日不辍,终成其志,是经典案例。
顾炎武从著述看,该当是读完无误,乃至可能会背诵。他受祖父影响,很小时就开始陆续读《资治通鉴》、《史记》等史籍,而后数十年光阴,为了写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完成“经世致用”的宏愿,更是通读历代经史文籍。因四处奔劳,集书不易,不止是读,且是熟稔到背诵。
明亡后通过读史反省得失落,成为汉遗民们的一种共识
随后的万斯同、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从著作与时人转述来看,显然负责读完,他们也都写出了精湛的读书条记,可拿来做证据。
从这个层面看,清及以前,真读完所有正史的,实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天时地利等外在条件完备具备,可通读“二十四史”的,多涌如今民国。
贲园,号称“成都天一阁”,百年迈建筑,今存和平街
可考的,是吕思勉、顾颉刚、范文澜、钱穆、张舜徽诸人读过。为啥如此劳心费力,或为考证史实,或为写通史故。这些,在他们的文章著作中,有或明或隐的零散记载。比如大史家吕思勉,意在通史写作,据其高足黄永年估算,吕不仅“二十四史”研读完过,乃至“或逾四遍”。尤其是前四史,他读得更为仔细些。
再比如,晚清民国之际的蜀中史学家张森楷,他借助成都第一图书馆“贲园”(该园还在)的阅读便利,写出了《二十四史订正记》,看其序,便是读完过的。在比如,与王国维同时的海宁张宗祥,自称32岁时,就“点读二十四史毕”,他紧张目的是要利用藏书给各史作订正,为后世读者给出便利。
张舜徽,1911-1992,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读书,自少到老
读二十四的心愿与履历,长期供职于华中师大的当代名宿张舜徽师长西席,其辞吐可能最有代表性的。他说:
“少年期间,读古文辞,喜诵长篇气盛之文,手抄熟读,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稍长,又喜览大部头书,从无畏难退缩之意,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由七个月的韶光,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
后来年事稍大,又发愿通读《二十四史》,不畏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负责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的很仔细;重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
他是整整花了10年韶光,逐日天没亮就起床阅读,“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二十四史”不是爽文小说,要负责一过,委实并不随意马虎。
而像毛师长西席,在日理万机的事情之余,生平都勤力研读《二十四史》,据事情职员回顾,是通读了全书的,有些纪传,乃至反复斯义,研读了几遍。
昆剧《顾炎武》
别的,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才捷才,连《大藏经》这样的冷门,卷帙也并不输给二十四史,更与他“专业”关系不大,都会令人发指地过三遍,“区区”二十四史,该当逃不出他锐目的辐射范围吧。
再点名当代以来鸿儒博学,诸如陈寅恪、饶宗颐、余英时、许倬云诸大师,他们的多数作品,我多曾草草翻看过,他们是否读完所有正史,至少没见到直接证据,也不好遽下断言。
当代“博士”,“博”学不见踪影,“士”气也早已魂飞魄散
而这种论定之犹豫,也正反响读完二十四史之繁难,实非常人之事。这些大师,作为当代史学家,读史路径和存心,已经和乾嘉时期前辈略有差异,不是纯挚的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而是殊途同归地通过对历代史乘的省察与谈论,来申述继古开新的代价空想,并用这种代价理念,来期许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探索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出路。
此乃诸师长西席读史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们至今落寞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名山奇迹,百代之师;海上心情,千古昭然,是否读完二十四史,已是末事。
虽说当代人不读书,偃蹇而骄,可将包括《清史稿》(?)在内所谓“二十五史”“读”完的,论人头数量,可能真是当代人居多。
网上自称有史以来首次读完“二十四史”的“州里干部”
何以说的这么抵牾?由于到了当下,自称读完“二十四史”的,我平素浏览网页,创造比比皆是呀!
清点出人数,大概都可以去填海造地了。反正当代社会,不传谣,不反社会,过过嘴瘾是公民权利。像写出《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就曾经言之凿凿的流传宣传,“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明实录》、《清实录》,统共读过6000多万字的历史文籍”,至于真假虚实,和他不熟,不加评价。
当年明月,即石悦,与猫腻同为湖北宜昌人
连韩寒大师,这位整天劳碌于赛车、拍电影之人,当年都公开、反复说读完过“二十四史”。不过,不幸的是,张嘴就来的不经牛皮,随即被打脸,连带着那些年夜言,都成为学青们常常搬来谐谑的话,差不多成为万年笑话梗了!
韩寒与他的“二十四史”
显然,这是一个更为主要的警诫:对付一样平常人来说,假设所有正史,只是粗粗“读”完一遍,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左进右出,除了能在小姐姐们面前,吹吹牛作为标榜谈资之外,到底有啥意义呢?
韩寒
诸如此类的雅人,绝非一些朋友谩夸的“民间多高手”,更切确的说法该当是“民间多妄人”。真能沉潜个中,不弄花哨,转智成识的“扫地僧”,麟角凤毛,百年难遇,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譬如,躲在乡下半生也持读史籍半生的王夫之,完备是近三百年来独孤求败。
总之,再发一句不合时宜的感叹,往者已矣,来者难知,“二十四史”到底有几号人读过,委实一点都不主要。
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
更为主要的,是当下的人们,应该永久记得,书架上那一排排耸立着的倔强灵魂,还在如此这般无聊至去世的时期,肃然无言,护卫着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又犹如废渊篝火,在空谷中,始终闪动盈盈欲溢出的火光,默默等待来人,燎原于大地,燃烧在民气。
三千年读史,无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如有机会,实在该当去逐步地、仔细地聆听,那些传自远古的深奥深厚回响。这才是我们今日,闲谈这个话题最好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