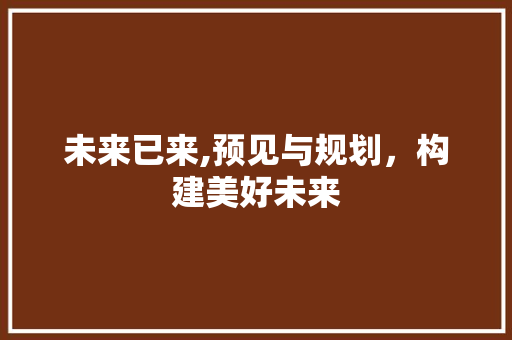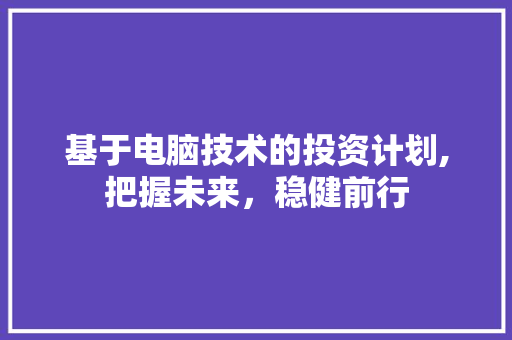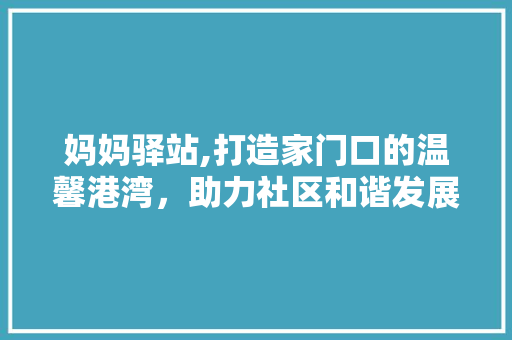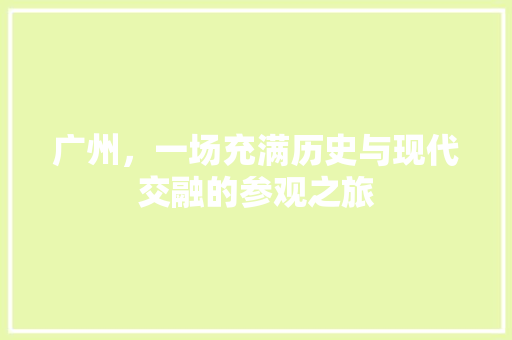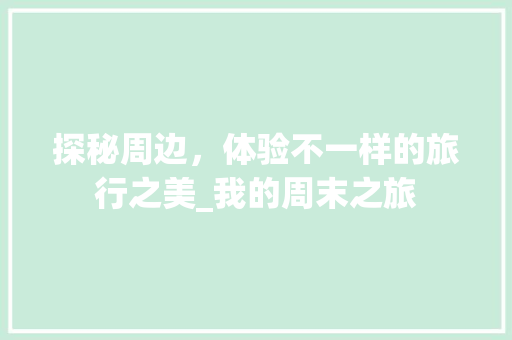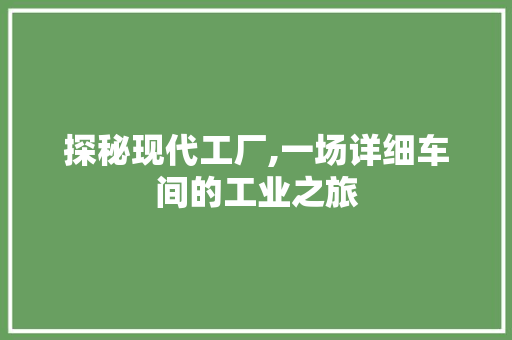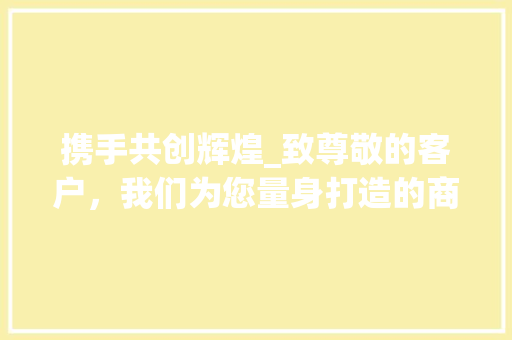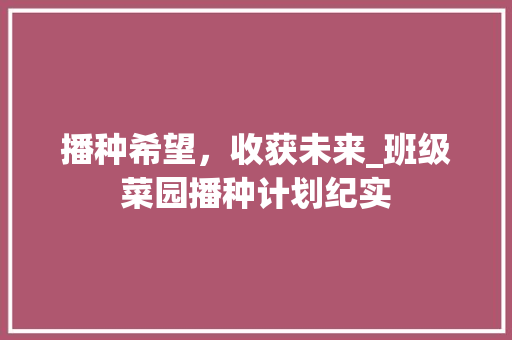夕阳斜斜地穿透窗棂,照在木质的茶几上。茶几朴实的木纹泛着悦目的光泽。
我努力地掌握着心头的烦闷和失落落,却仍有一些话脱口而出:“你看看买的这什么衣服,给楼下舞蹈的老太太穿都以为显老。让我穿着它去参加毕业仪式?呵!
就由于便宜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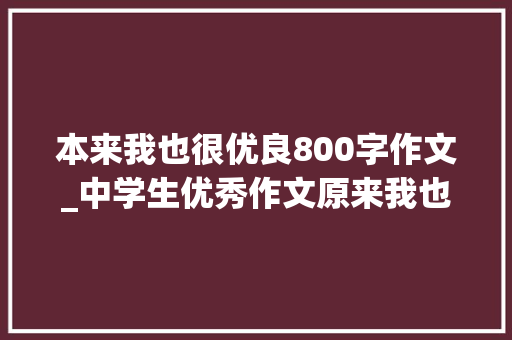
我的语气里是不想再掩蔽的气急败坏,它如同一把利刃,锋利地划过了傍晚的安谧宁和,划破了我和妈妈之间笼罩着的那层压抑疏离的薄纱,赤裸的伤口一下子暴露在这冷凝的空气之中,触目惊心。
妈妈的面色好似不如平常那么红润,眼眸也不复平日的通亮欢愉,一层黯淡的阴影渐次蒙上她的眼眸,起初浮现的一抹笑意逐渐溶解在她垮下去的嘴角。那件毛衣被她粗糙的双手反反复复翻动着,摩挲着。明明早已叠得方方正正,却仍要一遍遍假装想抚平衣服原有的褶皱,似是在极力粉饰着某种悲惨和落寞。妈妈缓缓举头,嘴唇有些抖动,终于发出无奈却清晰的回应:“我挑了良久呢!
不要就不要罢,来日诰日我就给你退了去……”
粗暴的闭门声打断了妈妈未了的余音,遮断了窗外的斜阳。我伏在桌上,麻木地挥舞笔尖。客厅中,传来细微确当心翼翼的声响,该当是妈妈正将衣服打理平整,塞进包装袋里去吧!
我的心忽而悸动起来,泛起迟到的懊悔。我极力不去想这些,希望烦躁的心绪能够在无尽的书写中归于沉着……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从无话不谈的伙伴,只剩下面前这克制而哑忍的互换?什么时候开始,妈妈曾给予我的带着亲情的深切友情,变成这样小心翼翼坚持的表面平和?
什么时候,那个心目中充满伟力的妈妈,变成了面前这个噜苏唠叨令人烦躁的母亲?
明天将来诰日的清晨,我匆匆忙忙洗漱好,来到桌前坐下。面前照例摆着热气腾腾的早饭。妈妈不知在厨房里忙活些什么,我偷偷转身瞥了她一眼:她略微发福的身躯此刻跟陀螺似的打着转,一下子案板,一下子锅炉,只见她灵巧快速地在两地一直转移。锅铲被她抡得高高提起,重重落下,仿佛奏响了一曲高亢的战歌。在这场锣鼓喧天、热火朝天的战役中,妈妈俨然是一位指示江山,胸有成竹的智囊。
我草草灌了几口温热的粥,正欲夺门而去,妈妈溘然从厨房里追了出来,带着一个小包。她将小包挂在我的臂弯,负责的叮嘱我:“妈妈给你带来菜,中午和同学分着吃哈……”妈妈的手自然伸了上来,又仿佛想起昨天的争执和烦懑,讪讪地停了手,究竟还是轻轻一提,将我折在里面的领口翻了出来,又将我肩上散落粘连的发丝逐一捡出,这才拍了拍我,示意我快走。
我怔在原地,比我矮了半个头的妈妈就在我面前。一阵冰冷砭骨的寒风从楼道口闯入,她彷佛微不可见的地抖动了一下,却极力地面不改色。在光影的投射下,她那丛生的白发在早已染烫褪色、蓬乱的卷发中愈显分明,面上是粉饰不住的一脸倦容疲态,却仍旧带着殷切的顾虑和疼爱……
我仿佛能够听到心灵深处的冰山轰然坍落,化作绵延春水,汩汩流淌,涤平了那些眇小的嫌隙和抵牾,一种笃定的爱和温暖,溢满了我的心扉……
在迷蒙的雾气中,我朝前走,往一个方向武断前行。迎面的寒风中隐约传来春天的气息。我想,在少年跋涉的路上,如果我们能穿透心灵的迷雾,便会创造我们从来未曾孤单,我们的亲人正伴着我们雕琢前行,以他们日渐老去的体魄和饱经风霜的容颜,坚实而笃定,绝不犹疑。
原来,我一贯都很幸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