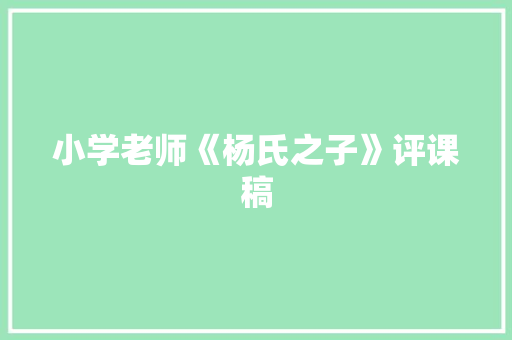这一段是《内篇》中历史意识、蜕变意识表示得最为突出的部分。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庄子对史前蜕变作出预测的部分作出解释。这一部分不仅笔墨艰深,而且存在一个《庄》书独特的表达办法的问题,当然也还存在一个理论阐述的问题,以故这一段笔墨的精确阐明,成了《庄》学史上迄今未曾办理的难点之一。为相识释的方便,兹先引出干系的原文: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聶许,聶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一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王引之云:“‘恶乎’,犹言‘何所’。”(《经传释词》)女偊以九“闻”相答。这在表层上是讲闻道之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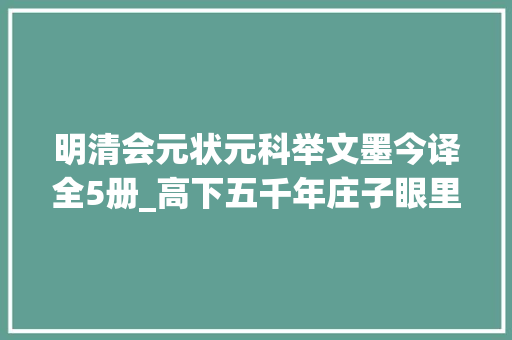
女偊的这一段答语,是本篇的一个难点。像王雱、胡文英干脆就绕开了它。王雱只是笼统地说:“自‘南伯子葵’至于‘疑始’之数子,皆庄子制名而寓意也。”(《南华真经新传》)胡文英仅注曰:“从空撰出许多名目,要亦是身体力行过来,非若后人妄为杜撰也。”(《庄子独见》)两人都别无其他的注释与解释。成玄英将这九个“闻”的过程说成是读书明理的过程,林希逸则仅将之算作是一个读书的过程,他们都只在其注释的末端提了一下“道”。但许多古代《庄》学家都将这个过程阐明成一个学道的过程,虽然在一些词的训释上有一些歧解。说这是一个学道的过程,显然就与上文女偊教卜梁倚的那一段话重复了。
“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吕惠卿释曰:“道以体之为正,则文墨所论者乃其副之而非正也,故曰‘闻之副墨之子’。然不能绵络贯穿而诵之,则不能究其本末而至于通,故曰‘副墨之子闻之洛诵之孙’。‘洛’之言‘络’也。子孙云者,言道之有生乎此也。已诵而通之,则见之明矣,故曰‘洛诵之孙闻之瞻明’。”(《庄子全解》)仅从对这三语的阐明上看,吕惠卿就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第一个“闻诸”是由于文墨是道体之副,为何要闻于副而不能闻于正呢?吕惠卿没有说。二、第二个“闻诸”是由于“不能绵络贯穿而诵之,则不能究其本末而至于通”,这是由于洛诵是通的条件,故闻诸焉;但第三个“闻之”,则是因通而见之明,故曰“闻之瞻明”,这就不对了,见之明是通的结果,而非条件。吕惠卿对下面三个“闻之”的阐明所采纳的都是颠倒结果为条件的阐明。
林希逸说:“‘副墨’,笔墨也。因有言而后书之简册,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书之墨,副也。‘洛诵’者,苞络而诵之也。依文而读,背文而诵,犹子生孙,故下子孙两字。‘瞻’者见也,见彻而曰‘瞻明’。”(《南华真经口义》)林氏关于“副墨”的讲授,释性袭为己注。林氏对“洛诵”的讲授,释性作了一些改动而袭取之,其改动紧张是用吕惠卿所说的“绵络贯穿”更换了“苞络而诵”四字。林氏对“瞻明”的讲授,释性略改而袭之(《南华发覆》)。然而,释性不明白的是,林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对“瞻明”的阐明,同上面两项是分离的。林希逸对下面三个“闻之”即“瞻明闻之聶许,聶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的阐明,也都是各自分离的,他只是总说了一句:“凡此数句谓道是读书而后有得,做出许多名字也。”(《南华真经口义》)
“子”“孙”二字,颇难堪解。古代《庄》学家中许多人都绕了过去,像陆西星、释德清、王夫之父子、林云铭、马鲁、陈寿昌、林纾等人。
上文已经说到,林希逸是将“子孙”解为读与背的。宣颖曰:“书本笔墨也,笔墨是文字为之,然笔墨非道也,不过传道之助耳,故谓之‘副墨’。又对初作之笔墨言之,则凡后之笔墨皆其滋生者,故谓之曰‘副墨之子’也。”“笔墨须诵读之,‘洛诵’者,乐诵也。对前辈读书者言,则今其孙也。”(《南华经解》)这样说来,“副墨之子”是后来滋生的笔墨,而后辈读书者则为孙,此种讲授,一以笔墨,一以人,标准不一致,予人以牵强之感。然而,刘凤苞从宣说(《南华雪心编》),王先谦对“副墨之子”的阐明引了宣颖的注(《庄子集解》),而对“洛诵之孙”,其注曰:“谓连系诵之,犹言反复读之也。洛、络同音借单。对古先读书者言,故曰‘洛诵之孙’。”(《庄子集解》)后面这个注,除了对“洛”字的阐明与宣颖不同外,其对文意的解释仍旧是取于宣颖的。
今之注释家中也有不少人绕过了对“子”“孙”二字的阐明,如王叔岷、曹础基、张耿光、陆钦、刘建国与顾宝田、欧阳超等人。
张默生、黄锦鋐注“副墨之子”引了宣颖注,而注“洛诵之孙”则引了王先谦注。杨柳桥注“副墨之子”亦引了宣颖注,而注“洛诵之孙”则曰:“笔墨本于措辞,措辞辗转相授,故曰洛诵之孙。”(《庄子译诂》)王世舜袭用宣注以注“副墨之子”,对“洛诵之孙”则注曰:“古书先口授而后形成笔墨。以是说副墨之子闻之洛诵之孙。”(《庄子译注》)依杨柳桥注,措辞在先,依王世舜注,口授在先,笔墨在后;怎么反而笔墨为子,措辞为孙了呢?对这样显著的不通,两人都看不出来。陈鼓应依陈启天释“子”“孙”为流传之意而注之(《庄子今注今译》)。然而,流传总是前代传到后代,怎么可能子闻诸孙呢?钟泰说:“书皆先口授而后著之竹帛也。曰子曰孙者,言其有所祖述也。”(《庄子发微》)无论是“流传”说,还是“祖述”说,当由前辈流传到子弟,子弟祖述于前辈,怎么会子闻诸孙呢?
这样一个眇小之处,难倒了古今所有的《庄》学家,成了《庄》学史上一贯无解的一个难点。
二办理“子”“孙”二字的训释,首先要从总体上来把握这段话。这段话是从“副墨之子”,讲到“疑始”,也便是说,它所述的是一个向上追溯的过程。林希逸所用以阐明的读和背,是读书的两个先后阶段,而宣颖之笔墨滋生及后代读书说,以及今人的先口授后著之竹帛说、流传说、祖陈说,都是一个由前及后的过程,均不符合这段话的总体阐述方向,因此,无一可取。
这个问题要从表达办法上阐明,副墨之子,是一种拟人的写法,“洛诵”之拟人化,连类而及,便称之为“孙”了,可见洛诵之孙是一种连类而及的写法。“子”“孙”一相对,就成了一个坑,古今《庄》学家纷纭跌了下去,或是自知无法阐明就绕过这个坑掉头走开了。
我在阐明《齐物论》中“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两语时曾说,昭文、师旷正是因同为妙善音律者方连类而及也。在寓言和举例中连类而及是《庄》文的一个特点,纵然到“杂篇”中亦复有此例。正是对这一点的不理解每每使得浩瀚《庄》学家对有关字句的诠释大伤脑筋。《大宗师》此处由子及孙,是连类而及表达方法之又一例也。
这里还须要澄清一个问题。林希逸说:“九个‘闻’字真是奇绝。”(《南华真经口义》)但庄子为何连用九个“闻”字的缘故原由,他没有磋商。宣颖说:“不过言由读书而深之乃至于得道,撰出如许名字,以经传之体例之,彷佛不雅观观,然庄子从来止因此文为戏,所云‘寓言十九’者也。”(《南华经解》)宣颖的评论有两个缺点:一、将庄子用九个“闻”字的这段话定性为“不雅观观”“以文为戏”是不对的。二、将所谓“以文为戏”视为寓言,也是错的。刘凤苞则曰:“后段彷佛以文为戏,而由浅入深,皆从体会而出。”(《南华雪心编》)刘氏这句话口气虽缓和一些,但仍认为这段《庄》文因此文为戏,既然因此文为戏,却又说成是皆从体会而出。刘凤苞完备不睬解《大宗师》这段话大有预测的内容,并非由体会而得。
九个“闻”字的由来,就在于上文“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一语。女偊的这一段答语是接着“闻”字而言的,在文中,女偊既然是人,则其所闻者也当是人,于是庄子乃将“副墨”拟人化,这里的“子”,本是人的泛称。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毛传:“舟子,舟人,主济渡者。卬,我也。”“之子”一词《诗经》中甚多。再举一例,《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郑玄笺:“之子,是子也……于是子之嫁,我愿秣其马。”“副墨之子”,用口语译便是副墨这个人。像“操舟之子”,翻译成口语便是驾船的人。古今注释家的一个凝固之处,在于只执定“子”为儿子义。
明白了“子”“孙”是一种连类而及的拟人写法,我们就可以不纠缠在“子”与“孙”的错位上,并且能够明白“子”的确切含义,从而可以确认这一段的追溯性子。明白了“闻”字于上文的由来,我们也可以判断,林希逸所说“形之言,正也。书之墨,副也”这个阐明是错的,宣颖所说“笔墨非道也,不过传道之助耳,故谓之‘副墨’”是对的,缺陷是宣颖没有解释这里的“道”的含义,他实在并不明白“道”在不同场合其含义有别这个道理。
在《大宗师》中,南伯子葵所说“子独恶乎闻之”一语,又是承上文女偊所说“吾闻道矣”而来,因此,此处之“道”当为大化无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明白女偊答语所阐述的,并非如宣颖所说“由读书而深之乃至于得道”的过程。它是用拟人的手腕——九个“闻”字表明,女偊的答语均采取了拟人的写法——阐述了极为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副墨、洛诵为一个阶段,瞻明、聶许、需役、於讴为一个阶段,玄冥、参寥、疑始为一个阶段。
三副墨、洛诵所代表的,是笔墨记载阶段源自口头传播阶段。陆树芝注“副墨之子”曰“笔墨所垂者”,注“洛诵之孙”曰“传诵所播者”(《庄子雪》)。这两个注比较好。虽然他对付何谓传诵没有作出解释。“洛诵”的阐明,以上引宣颖所注“乐诵”为佳。陈寿昌承宣说注得更为明白些:“洛,犹乐也。诵,成诵也。”(《南华真经正义》)乐诵者,乐于传诵或配乐传诵也,这正是口头传播阶段的状况。
瞻明、聶许、需役、於讴,所表示的是一个比口头传播更早的阶段。“瞻明”,上文已引林希逸的阐明:“见彻而曰‘瞻明’”,亦即看得清楚明白。“聶许”,陈寿昌注曰:“附耳密语,听之而心许也。”(《南华真经正义》)。此注实在是将两种阐明合并了起来,当往后者为是。“聶”,《说文·耳部》云:“駙耳私小语也”(《说文解字注》)。不过,在这里准确的阐明应为:耳间语,这一阐明古今《庄》学们均不知也,然《说文·口部》明曰:“聶,语也。”段注:“聶,取两耳附一耳。”(《说文解字注》)
“需役”,王叔之曰:“‘需’,待也。”(《经典释文》)后世《庄》学家从者甚众。林希逸、释性、陆西星、释德清、宣颖、胡方、陆树芝、陈寿昌、刘凤苞诸家均取此释,成玄英、林纾训“需”为“须”(《庄子集释》《庄子浅说》),均误也。“需”字完备可以、也该当从本字来讲授。“需役”者,为知足需求而力役也。
“於讴”,朱桂曜说:“‘讴’与‘於’同。《淮南·览冥训》‘区冶生而淳钧之剑成’,高注:‘区,读歌讴之讴也。区,越人善冶剑工也。’朱骏声曰:‘区,区越也,犹言‘於越’,瓯越、欧越皆同。’是‘讴’‘区’‘於’三字通也。《在寡篇》‘於于以盖众’,‘於瓯’亦犹‘於于’也。《齐物论篇》‘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于喁’义当同。此如后世之言‘伊吾’‘伊忧’,皆有声而不针言也。又‘讴’从‘区’,‘区’与‘俞’通……‘於’‘俞’皆感叹之辞。”(《庄子内篇证补》)朱说近是,唯《庄》文非感叹之辞,而是力役之际应和之词也。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我们的先人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揭橥见地,才逐渐的练出繁芜的声音来,如果那时大家抬木头,都以为吃力了,却想不到揭橥,个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便是创作。”(《鲁迅全集》)鲁迅这是讲创作发生在未有笔墨之前。然而,这段话所讲到的劳动时原始人协力产生应和之声,却可以用来阐明《大宗师》中的“需役”“於讴”两词。“於讴”处于“需役”之前,所表明的是唯有协力才能劳动。这是一种原始集群的劳动。
“聶许”一词,在我看来,是隐约地预测了人类措辞的产生。拙著《中国前期文化—生理研究》说:“措辞符号是人类意识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凝定,因而它就不易为个体意识所旁边,具有一种相对客不雅观的性子,这便是说,它有为某一人类集群所共同承认的内涵,并且这种内涵在一定的历史期间中还具有相称的稳定性。然而,措辞符号不仅存在范围有特定性,而且存在的时段也有限定性,以是这种客不雅观性又只是相对的。但正好是这种相对的客不雅观性,形成了某一集群中人们相互沟通并协力于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物质天下也由此而从仅被个人感知的纯主不雅观状态,转化为一种可供共同把握的客不雅观状态。许多认识论研究者彷佛都忽略了人类历史之初在人类认识上所发生的这样一场变革。反响论者把物质的客体性算作是先验的而非天生的,唯心论者捉住了天下须经由觉得方得被认识这一环从而流传宣传唯一真实的是觉得,都没有看到认知天下的天生性:从个人的主体知觉状态转化为共同把握的相对客体状态。人类所把握并活动于个中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相对客不雅观性子的认知天下。”“聶許”,“聶”之“两耳附一耳”义,表众人共同切磋之状,“許”并不如浩瀚的《庄》学家所注释的是心许,而是众人之共许,亦即某一集群中人类意识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凝定,也便是物质天下作为一种可供共同把握的客不雅观状态之形成。上文所引,《说文》之释“聶”为“语”,实在正是说的措辞的形成。
“瞻明”一词,在我看来,是隐约地预测了因措辞符号的发展,周围天下清晰起来的过程。拙著《中国前期文化—生理研究》说:“事实上,措辞的产生及其逐渐丰富的过程是十分困难而缓慢的。为事物创造名称是当时的最高智力活动。创造出来的名称,在特定的人类集群中世代保存、积累着,形成为该集群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又是直接同物质的把握相同等的。专有名词即代表了认识的范围。节制的名称越多,就表示被认识的物质事变越丰富,从而周围的环境也就愈清晰。那种模糊一片的浑沌景象,也就在更大程度上消散。名称是一束精神的光照,照到哪一个物质事变上,该事变便从连成一气的阴黑暗浮现了出来。”
上文说,瞻明、聶许、需役、於讴,所表示的是一个比口头传播更早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在劳动的协力中措辞的产生及因之而使周围天下清晰化的过程,显然,这席卷了一个漫长的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实在质是人类认知天下的形成。有了口头措辞与对天下的认知,方才能产生出口头传播的时期,亦即以口口相传为文化积累办法的时期。
“口头措辞‘寄形’于归天符号”(《中国前期文化—生理研究》),方才渐次产生出了笔墨符号,从而进入著之竹帛亦即笔墨记载的时期。“筑城和笔墨的发明已是文明时期到来的标志”(《中国前期文化—生理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副墨、洛诵、瞻明、聶许、需役、於讴,这六个词所追溯的历史跨度是巨大的。然而这样宝贵的历史内涵,从未为任何一个《庄》学家所曾丝毫窥及。从对这六个词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符合《庄》文内在意脉的居高临下的思路对付诠释的主要性。
措辞产生以前,还有更为悠长的蜕变过程,庄子连预测也预测不了,便以玄冥、参寥、疑始这三个词来表示这一蜕变阶段。
“玄冥”,成疏:“玄者,深远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称。”(《庄子集释》)“参寥”,李颐云:“参,高也。高邈寥旷,不可名也。”(《经典释文》)“疑始”,疑其有开始,无论生物的进化也好,还是从猿到人的过程也好,似都可以确定一个大致的出发点,然而,庄子无法明白“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的协力劳动产生了措辞之前的蜕变情形,他就只能用一个“疑”字了。“玄冥”,大体说的是韶光深远,“参寥”,大体说的是空间开阔,“疑始”说的是这个深远的、开阔的时空是否有起始,如果是问韶光空间的起始,那么这倒是一个疑而难以解释的问题。“疑始”一词,兼有上述这两层意思。
本文所阐述的《大宗师》中的这一段笔墨,预测性地追溯了史前之蜕变。从艺术上说,这段笔墨以九个“闻”字连串起了追溯式的阐述,并使之与上文“吾闻道矣”一语勾连,从而使得南伯子葵与女偊对话的寓言呈现出了一种整体性。
(作者:王锺陵,系苏州大学东吴国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9月10日
本期编辑:杨雪丹 常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