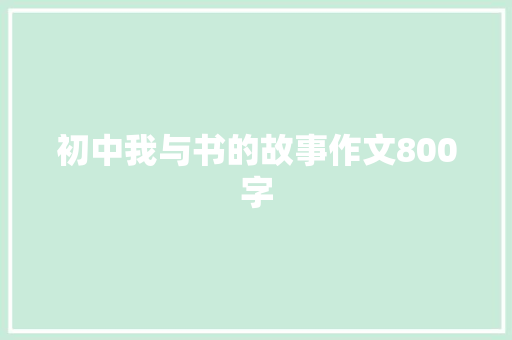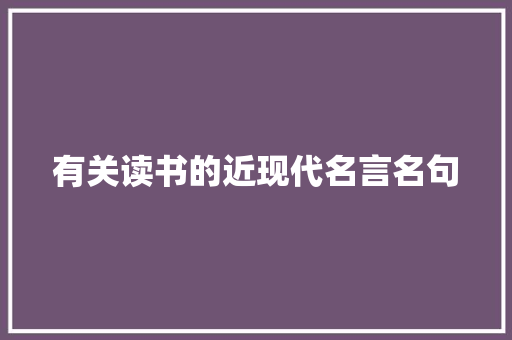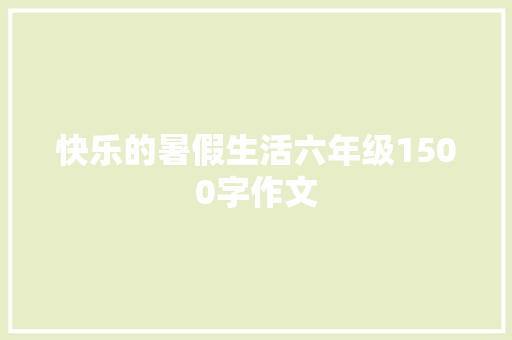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黄甫庄人,生于1883年,比鲁迅小两岁。父亲是个“绍发兵爷”,在他三岁时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寄居在叔叔家,常常被婶婶羞辱嘲骂,母亲不堪其辱,在他五岁的除夕夜吞金自尽了。范爱农兄妹随着祖母艰辛终年夜,1905年,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开办大通师范学堂,22岁的范爱农前去报考,并被录取。范爱农勤奋学习,成绩优秀,深得徐锡麟青睐。同年年底,范爱农跟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鲁迅前去欢迎,两人就此相识。
1907年,徐锡麟发动安庆叛逆,失落败被杀,范爱农作为翅膀被清廷取消留学费用,无奈返国,找不到得当的事情,只好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还曾被清廷派人抓捕,幸免。1909年,鲁迅返国,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第二年,在一次同乡聚会上,他们再次相聚。两个落魄的人惺惺相惜,惺惺相惜,范爱农常常来鲁迅家里饮酒谈天,日子超越越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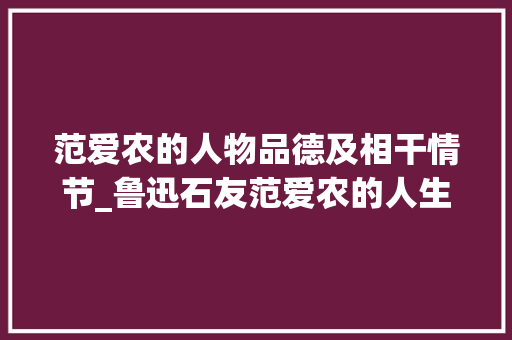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被任命为绍发兵范学校校长,请范爱农为监学,范爱农“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据当时一位学生回顾,鲁迅“温良敦厚,给人一种敬而爱之的觉得”,范爱农“一年到头穿着一身学生装,一双布底鞋,留着一个平顶头,衣着非常纯挚,像一个穷学生,教书时态度严厉,对学生尤其严明,总是整天闭着嘴,没有一丝笑颜。”
学校离鲁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每天办公完毕,范爱农便身着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来找鲁迅谈天。鲁迅母亲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点钟往后,范爱农才打了灯笼回学校去。
然而好景不长,也就几个月韶光,学校便由于经费紧张,人事繁芜,办不下去了,只好提前考试,提前放假。恰在此时,鲁迅好友许寿裳向教诲总长蔡元培推举了鲁迅,蔡元培说,我也早就听说过豫才(鲁迅本名)的大名,正要写封聘任函,现在你就赶紧替我写封信,让他赶紧来。这封聘任函对付鲁迅无异雪中送炭,鲁迅把去教诲部上班的决定见告了范爱农。范爱农很附和,但颇悲惨,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鲁迅到了南京,范爱农随即写来一封信,讲述自己在学校的困难处境。个中有“盖吾辈天生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去世而已,端无生理。弟自知不善巴结,断无谋生机会,光景绝望矣。”
鲁迅很快到了北京,范爱农又写来一封信,此时他已经被学生们驱逐出校了。过程大体如下。
一个星期日,两个跟范爱农平时有见地的同事让厨房给学生们开伙,按照校规,星期天补开炊事须要教务室和后勤室赞许,以是厨师没有听这两人的话,谢绝了。两人挟恨在心,遂在第二天早饭上指导学生们生事,声称饭里吃出了蜈蚣。当时范爱农恰好在场,他是监学,便命令厨师换掉重做,还训斥了厨师几句。不料午饭时,学生们又说饭里有蜈蚣,当时范爱农不在场,校长在场,带头不吃。众意汹汹,哀求换掉厨师。校长便让学生们征询范爱农的见地,范爱农说,让厨师们重做就行,如果做得还不好,可以让学生们自己带饭吃。
结果晚饭做熟,教员们和学生们都不来吃。去请也不来,摇铃也不来。范爱农说,此前说好的,嫌弃饭菜不可口可以自备,现在你们都没有自备,就请无论如何吃一点,众人还是不吃。范爱农怒了,说道,这是学校,不是饭铺,你们不用饭也不上课,如果想就此退学,那就赶紧回家,纵然你们几个退学了,学校还是还开。学生们于是都去用饭上课了。
第二天早饭,校长等众人坐好,忽然说,往后大家如果以为饭菜不可口,该当在用饭前就说,不能在用饭时才说。就像昨天那么搞,往后再犯,我绝不答应。学生们怒了,吃完饭一起找到校长,声言要罢课,接着把矛头对准范爱农,由于范爱农说过嫌饭菜不好可以回家的话,学生们声称,如果范爱农还在学校,他们就不上课。范爱农说,除非校长辞退我,否则我不走。校长于是开除了两逻辑学生。支持学生生事的两个同事于是带了几个学生,把范爱农的行李搬出了门房,并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范爱农就此失落业。
范爱农失落业后,断港绝潢,又去曾经逼去世过他母亲的二叔家蹭饭,没蹭几天,就被二婶赶了出来。此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老友,有的去了杭州,有的去了南京,有的去了北京,正在穷愁之际,一位报馆的年轻朋友伸出援手,约请他担当社外编辑。范爱农把此事写信见告鲁迅,鲁迅高兴地跟一起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寿裳说,范爱农进了报社,总算找到了一个用饭的地方。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范爱农和报馆中的朋友一起乘船出去玩,半夜酒醉,失落足落水而去世。
对付范爱农是怎么去世的,鲁迅在回顾文章中“狐疑是自尽”,情由是范爱农会拍浮,不随意马虎淹去世。这个推论得到了鲁迅二弟周作人的附和。周作人说,范爱农“彷佛很有厌世的方向,这是在他被赶出师范以前所写的信里,也可以看出痕迹来。”这个痕迹,便是第一封信中写的“盖吾辈天生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去世而已,端无生理。弟自知不善巴结,断无谋生机会,光景绝望矣。”
我们复盘范爱农短暂的生平(30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便是“性情决定命运”。范爱农也知道自己的性情短板,便是“天生傲骨,不善巴结”,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情商低,不长于处理人际关系。这导致他“断无谋生机会”,终极酿成悲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范爱农之以是混得这么惨,还有一个缘故原由,便是没有“一技傍身”。我们以鲁迅作为比拟。鲁迅也是被学校排挤出局,但他很快得到了教诲部的新事情。教诲总长蔡元培虽然也是绍兴人,而且是光复会的会长,但他从来不因私情照顾熟人,许多人去找他都碰了钉子,为此不无怨言,有人找到同盟会的某大佬说情,该大佬无奈地说,进别的部还行,进教诲部我也没办法。鲁迅之以是能进教诲部,绝非跟蔡元培有私情,事实上当时他根本不认识蔡元培。蔡元培之以是聘任他,皆因鲁迅是有两把刷子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跟兄弟周作人一起搞文艺,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寄返国内揭橥,小有名气。他还是章太炎的学生,旧学功底非常深。他们的好学乃至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把稳,当时的日本媒体登载,清国留学生中有姓周的兄弟俩,学习非常刻苦,非常难得。以是鲁迅的大名,蔡元培是听说过的,鲁迅的才能,蔡元培也是见识过的,因此许寿裳跟蔡元培一推举鲁迅,蔡元培立时便答应了。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校徽便是请鲁迅设计的。
比起鲁迅,其弟周作人就差点。鲁迅去教诲部上班,周作人一贯在杭州教书,直到几年后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鲁迅为了给周作人找事情,多次出入蔡元培府邸,自称“晚生”。周作人到了北大,怕教不了书,每越日间把讲稿写好,晚上交给鲁迅修正,第二天自己誊抄一遍,交给北大教务处审阅存档印发。就这么过了一年多,周作人才在北大站住了脚,逐步得到了同行认可。
鲁迅刚到北京时,也曾试着给范爱农找个事情,可是一来人生地不熟,自己还没有打开局势,没有人脉,二来范爱农没有一技之长,想给他找个得当的事情也很难。毕竟自古以来“长安居,大不易”,帝都最不缺的便是人才。
险些在创作《范爱农》的同时,鲁迅又写了小说《孤独者》。小说中的“我”和“魏连殳”便是现实中鲁迅和范爱农的翻版,但是鲁迅给了魏连殳一个悲壮的结局。现实中的范爱农潦倒穷困而去世,小说中的魏连殳却在被学校开除后,为了活下去,当了一位师长的幕僚,过了几天颓唐奢靡的生活。
《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同样有着一身傲骨,但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是有差异的。“我”对现实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相对客不雅观、镇静、务实而沉稳一些。“我”能将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挣扎化为一种淡定的应对,换言之,能够适应社会,但是魏连殳却弗成。
周作人把范爱农去世的写信见告鲁迅后,鲁迅悲愤非常,彻夜难眠,写了三首诗祭奠。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落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迈异域。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洌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师长西席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最得意的一句便是“白眼看鸡虫”,由于范爱农常常喜好翻着白眼看人。
鲁迅的文章镇静沉郁,非常耐读,值得反复读,多次读。这套鲁迅作品集,十册只需几十块钱,物美价廉,喜好的朋友可以买一套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