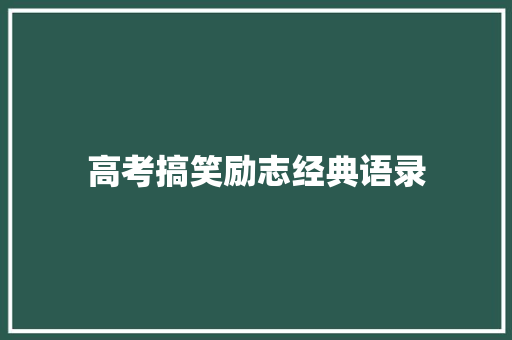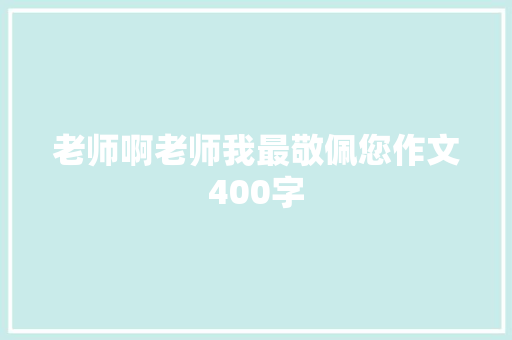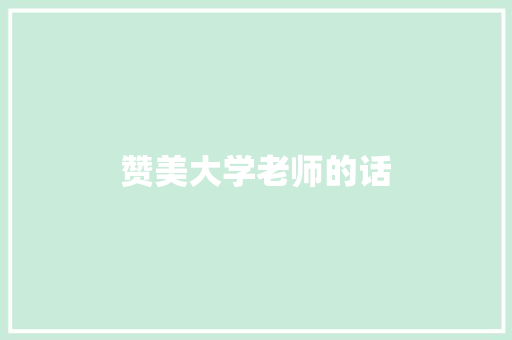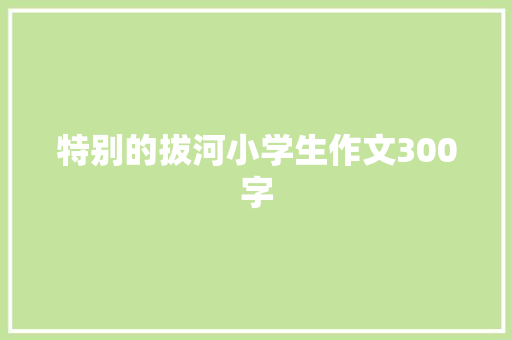一
2022年8月7日,那是悲痛的一天,忙着收拾老师的后事到凌晨,回家路上在手机上记下简短的感怀:“昨天下午在北医三院陪老师走过了他89年人生的末了一程。将近40年的师生情意,亲如父子,我握着他冰冷的手臂,脑袋一片空缺。吴老师一辈子内敛宽厚,总是在体谅照顾别人,到末了都是在照顾家人和学生,住进医院当天就走了。开好的化验许多都没有做,进药的胃管都没来得及插上就心脏骤停。年夜夫说这是他这种病人离世最没有痛楚的一种办法。祈愿老师在那边没有酷暑和病痛折磨,和您的好老师好同事好朋友们一起连续纵论历史、笑傲人生。”老师晚年对我说得最多的话便是要从容、淡定、脱俗。他自己的人生便是一贯在践行着这样的目标,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对死活毁誉他已经看得十分通透。而我,即便知道老师走得安详洒脱、了无憾事,但心里依然悲痛难抑,觉得心底最主要的地方溘然间被抽空了。将近四十年的受教,迷茫时的慰谕和劝勉,困顿中的鼓励和接济,暴躁时的棒喝和开悟,而今阴阳两隔,再也看不到老师慈祥的脸庞、永久笑眯眯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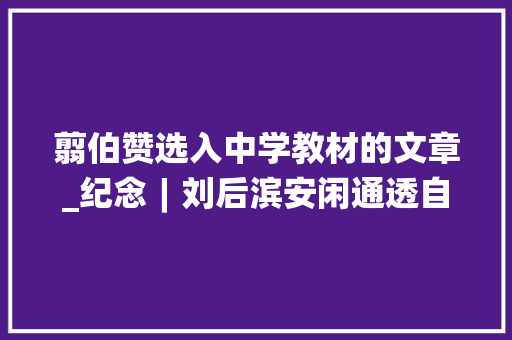
2022年春节在吴宗国师长西席家吃饺子
末了一次和老师较永劫光确当面交谈,是2022年8月5昼夜晚。当天上午和老师的小儿子通话,得知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危在夙夜迟早。赶到家里,老师一边吸氧,一边虚弱地向我嘱托几件事情。一是要我对接山西公民出版社的编辑,吸收与阎守诚老师合著的《盛唐之子:唐玄宗的成败》,并分送干系职员。我用微信转发了书影,并当场打开给他看。他说昨天阎守诚老师也来过电话,要了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以便发稿费。二是要我联系刊发《论传授教化带动科研》一文,他重复以前多次提及的话,要我全权处理此文的揭橥。此文于2022年9月26日揭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题为《论历史学科的传授教化带动科研》。现在想来,这两件事是老师对我的末了请托,大学历史学的传授教化、科研和人才培养,纵然不是他生命中的全部,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事情。
《盛唐之子:唐玄宗的成败》书封
吴老师1934年出生于南京市,籍贯江苏如皋。195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附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58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担当汪篯师长西席和邓广铭师长西席的助手。他留校不久就帮忙汪篯编写《中国史纲要》的隋唐五代部分,是这部由翦伯赞主编的经典教材的最年轻的作者。他主持修订《中国史纲要》(高下册),后来得到了首届全国精良教材一等奖。1983年任副教授,年届五十;1990年任教授,199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担当博导时已经六十有余。老师曾较永劫光担当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系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分外津贴,1999年6月退休。2018年是吴老师在北京大学执教60周年,学生们帮忙他整理了论文集作为纪念,题为《中古社会变迁与隋唐史研究》(高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教满甲子,桃李遍天下。寿年届九十,人生复何求?
追随老师近四十年,我很少听吴老师谈起他曾经的求学经历,更不见他炫耀和利用自己的师承关系。那些学术圈中鼎鼎大名闪闪发光的名字,仅仅是听说过就以为身价倍增,而吴老师在他们身边事情多年,朝夕相处,却不愿借此抬高自己,从不迎合,也不攀附,淡淡地做自己。记得读书时有几次碰着其他老师津津乐道地评论辩论往事,或是在回顾录里看到关于某位师长西席的某件轶事,我也曾好奇地求证于吴老师,吴老师总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毫无猎奇和夸耀之心。但只要涉及到传授教化传统和学术传承,则会很负责的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关于如何当好一个大学老师,如何做到传授教化带动科研,吴老师不知道给我讲过多少次。我从1991年硕士毕业到中国公民大学任教以来,传授教化中碰着任何问题,都会求教老师,他也时常结合自己的实践给我传授传授教化履历,其间也会涉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和掌故逸闻,例如各位老师如何上好通史课,翦伯赞在主编《中国史纲要》过程中如何统稿之类。他很看重自身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脉络中承前启后的位置,自觉地担当起他的老师辈与下一代之间学术传承的义务,延续着他们的学术生命。他的老师是民国一代学人,他自己真正走上讲台完全授课及辅导研究生,则要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时期的缘故原由,他本人揭橥学术论文并不算多,而且差不多和规复高考往后入学的学生辈同时开始揭橥文章。他获评副教授和教授的年事都略晚于同龄人,辅导的研究生数量有限。但他始终怀抱着强烈的任务感和自傲心,教书育人,默默奉献,恬淡自处,以言传身教担当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传承托命之人的角色,不掺杂着任何个人的功名利禄。吴老师在隋唐五代史乃至全体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培植中,无疑发挥了主要的浸染,虽无显赫之声誉,但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0年代中后期在读的学生中间,他的影响力无疑是相称广泛而持久的。
与吴宗国师长西席合影
二
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去世前的十多天,7月26日,我去蓝旗营府上探望,此前7月8日,祝总斌老师去世,原来我一贯在犹豫是否将祝老师去世的见告吴老师和师母。不料我坐下不久,师母就直接问起祝老师后事如何安排的。显然他们已听到,我只能如实相告。给他们先容了祝老师后事安排的大致情形,包括历史学系设立哀悼室,以及学生们去昌平陵园安葬骨灰的各种细节,我打开手机微信给他们看了一些现场照片。吴老师神色凝重地看着祝总斌老师安葬现场的照片,过后,与师母对视少焉,轻轻点头。吴老师和师母刘念华老师相知相爱半个多世纪,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老师们口中几十年传颂的恩爱夫妻。例如,何芳川老师在世时,在联欢会团拜会等场合多次和我们学生辈讲起吴老师和师母的浪漫往事。多数情形下,我们去家里看望,老师除了学术话题,其他问题谈的不多,都是师母在和我们互换。这次,见吴老师点头,师母接着说:“你给我们先容这些,看照片,是对的,不要担心我们,我们很想知道。”那时,吴老师已经病得很重,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祝老师是吴老师几十年从教生涯中的至交好友,是在1980年代往后帮助他平稳从事传授教化科研的学术伙伴。1995年初,我报考在职博士生的时候,教诲部还没有批复吴老师的导师资格,吴老师要我填报祝老师的博士生。等到9月份入学的时候,正式批复下发了,祝老师说那你还是由吴老师辅导。事实上,他们是我在学术道路上受教最多、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在2022年的7月8日和8月7日,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失落去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最敬仰的两位导师,有时候不免抱负,另一个天下是什么样子?没有生的烦恼,老的折磨,病的痛楚,去世的恐怖,是所有挚爱亲朋终极团圆的地方。两位学术伙伴,几十年共事北大,半世纪的死活友情,学术上的相携合作,在那个天下里,还会连续罢……
生活中的吴老师,话不多,更少流露情绪。而师母激情亲切豁达,视吴老师的所有学生亲如子女,每当学生到家中探望,都是师母抢在前面,激情亲切接待,提及时政大事、家常琐事滔滔不绝,吴老师总是笑眯眯地听着,温和而宽厚,你在说,我在笑,那便是“家”最该当有的样子,我们能够想象的家的所有温馨都在那里了。这也是我作为学生,在教室之外从吴老师身上学到的更主要的东西。对家人,对同事、对朋友,对学生,关心的话说的不多,却一贯温暖着所有人。一个人,集魁伟高大的身躯与温良柔和的心性于一身,没有人比吴老师更自然天成。
吴老师对自己的每一位老师和学术上的同事都怀着敬爱和尊重,纵然有一些误解,也从来都报以最大的善意,加以化解。他在任何场合,不争,不怒,相信公道清闲民气,公开言谈总是顾及他人感想熏染。吴老师是如此心地善良,心胸豁达,醇醇然有古君子之风。有一次北京大学召开纪念邓广铭师长西席的会议,吴老师写好了发言提要,给我当面讲了一遍,回顾邓师长西席在鲤鱼洲干校搬牛粪和后来谢绝作序、反对编书的几件往事,他犹豫再三,想到可能会引起其他先生长西席的遐想,终极决定不参加这个会议。在我读硕士研究生的那几年,吴老师每年都会带着我去给王永发兵长西席拜年,他说王师长西席是汪篯师长西席的同学,就犹如自己的老师一样,希望我多听王师长西席的课,多向王师长西席请教。我也负责实行吴老师的安排,在王永发兵长西席完全开课的末了一个学年,在每次课前,我都早早来到蔚秀园王师长西席家期待,替先生长西席拎着一大袋子的传授教化用书,扶他逐步走到第一传授教化楼的教室。
2010年中国公民大学唐宋史中央成立大会合影,从左至右为:罗永生、叶炜、吴宗国、刘后滨
三
我与吴老师近四十年的师生情缘,始于1985年的秋日。是老师教室上的讲授让我第一次感想熏染到了学术的意见意义和魅力,是老师的谦和鼓励给了我战胜自卑的勇气和信心,也是老师的帮助和引领,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重绘了我生命的底色。我走上西席岗位,并一贯在大学任教,毫无疑问是吴老师言传身教的结果,也是吴老师一次又一次存心用力拉扯的结果。
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正是大学西席地位和收入最低的历史期间。我成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希望我能够从政,最好能进大机关。那个时候我已经跟随吴老师多年,主要人生问题都会向老师求教,由于老师是除了父母以外最可信赖的亲人。找事情的过程中,公民大学的沙知教授给吴老师打电话,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去公民大学任教,吴老师大喜过望,认为留在高校非常适宜我的人天生长。我父亲得知后,当即来信反对,他认为含辛茹苦供我上完了大学又读研究生,居然还是去当一个老师,这与当初考上大学时家人和宗族的期望相差甚远。毕竟我是规复高考后本县第一个应届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当地刘氏宗族自宋朝出了多少位进士往后能够再次进京读书的人,在我身上寄托了全体宗族的厚望。我不知如何说服父亲,吴老师亲自给我父亲写信,一个大学教授用一个识字不多的农人可以看得懂的道理,耐心奉劝,他说公民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往后许多高等干部都将是你儿子的学生,比他自己当干部还厉害。老师以满心的善意去理解和化解一个农人朴素的心思和希望,我父亲一贯珍藏着这封信,这是他这一辈子收到的最主要的信件。
1992年中国各界都涌现了“下海潮”,一韶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时我在历史系党总支见习,碰着了担当企业高管的系友极力劝诱,生活的困难也让我产生了换个事情的动机。我胆怯地去和老师商量,吴老师没有训斥和说教,只是耐心地给我剖析教诲发展的方向,指出我个人的上风和劣势,鼓励我坚持下来,不要由于面前的困难而动摇。在那前后,他去韩国和日本做访问学者,回来后买了彩电,生活条件得到改进。他说你们不要灰心,我到六十岁时达到的生活水准,你们三四十岁时一定能够达到。在险些看不到希望的困境中,我能一贯坚持在大学里教书,仅仅是由于我相信吴老师的话!
我对老师的亲近和信赖来自本科上通史课的体验。二年级的上学期,吴老师给我们班讲授四个学分的中国古代史(三)隋唐五代宋辽金段。教室里初次见到老师,挺立高大的身躯,谦善和蔼的脸庞,令人如沐东风,几堂课听下来,条分缕析的讲述,层层递进的评析,我真正感想熏染到学问的魅力。学习根本薄,家庭条件差,身体有缺陷,我因自卑从不敢在教室发言,也不敢在辅导韶光提问。教室条记上有大量缺字和错别字,须要课后去查书补正,吴老师有一次在二院108课后答疑时创造了我的问题,等到结束时把我留下,他推着自行车和我走了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和大学者走得那么近。我鼓足勇气,怯怯地说自己对历史学很有兴趣,但觉得根本太差,与同学们的博闻多识、对答如流比较,实在相形见绌,完备没有信心。吴老师悄悄听我说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永生难忘的话:你能够考上北大,数学分还不低,解释你智商没有问题,纵然是中等之才,只要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将来一定会做出成绩。那是改变我生命轨迹的话语!
一位在《中国史纲要》教材上和翦伯赞一起列入作者名单的老师,说我将来能够做出成绩,那是何等主要切实其实定啊。刚入学的时候,我只知道翦伯赞,由于中学教材上读过他写的《内蒙访古》,其他作者如吴荣曾、田余庆、许大龄等老师,包括邓广铭师长西席和汪篯师长西席,只有到上了课后才知道的。
1985年秋日的那一次校园溜达,吴老师引发了一位极度自卑的学生对学术的美好憧憬和强烈兴趣,我暗自下定决心,要随着吴老师一贯读下去,成为一个像老师那样有学问的人。从此,我一下课就到图书馆,迫在眉睫地阅读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魏晋隋唐史的干系书本。大学的后两年,除了吴老师开设的隋唐史,我还选修了王永兴、许大龄、张广达、祝总斌等师长西席开设的课程,田余庆师长西席的“东晋门阀政治”,由于韶光冲突,是借同学的教室条记补修的。等到1988年的毕业学期,我在王永发兵长西席唐代制度史教室上写的作业《唐代法律“三司”考析》得到了“五四”科学论文奖,吴老师更是对我大加讴歌,并辅导我修正,向《北京大学学报》投稿,后来揭橥在1991年的第二期。这篇处女作的完成,是我上大学期间最长自傲的事情。
由吴宗国师长西席辅导的硕士论文
从本科通史课上的初相识,得手把手辅导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鼓励并带领我一步步走进学术天下,吴老师不仅没有嫌弃我的猥琐和贫寒,还年夜方寄寓了学术传承的期望和义务,不带有任何学术之外的功利目的。从一个放牛娃,发展为一个大学西席,除了负责做一个好老师,我也没有任何可以回报老师的。
老师的知遇之恩重如泰山,点点滴滴刻骨铭心,但要诉诸笔墨,却不知如何落笔,从何提及。我的出身与经历,决定了我永久都达不到老师的从容、淡定和脱俗的境界,但老师的为人与为学,一贯是我努力追寻的高度。只是,大半生的韶光,在事务性的泥潭里愈陷愈深,老师当年不遗余力帮助我方案的人生蓝图,眼看其实现的可能越来越小,心里就不由得慌乱。今年的8月7日,是老师的周年忌日,约了几位师兄弟,到老师的墓前祭奠。瞩目着墓碑上老师慈祥和蔼的遗容,不由得泪湿了眼眶。那一刻,我溘然明白自己要做出一些主要的人生选择,一起捡拾的芝麻和西瓜,究竟要丧失落一些,最好的归宿便是回归老师的期望,做一个从容实在的读书人和教书人,找回老师曾经给我重绘的生命底色,或许这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