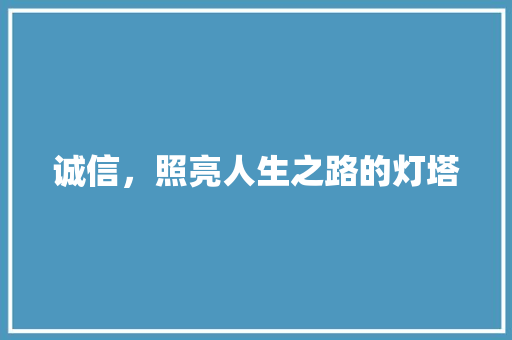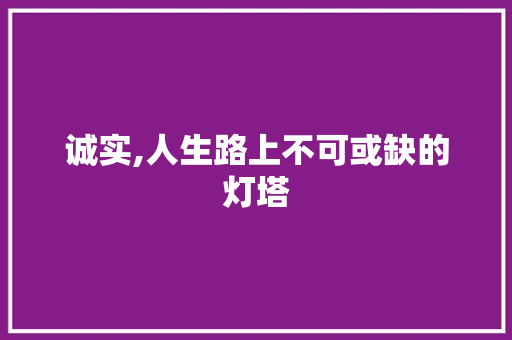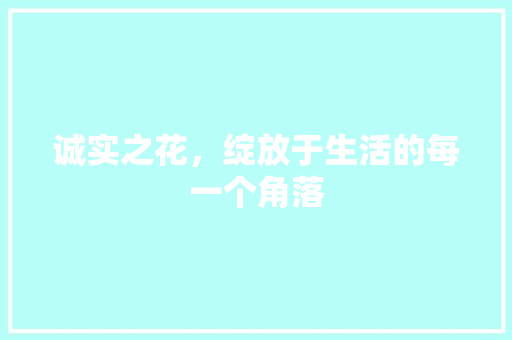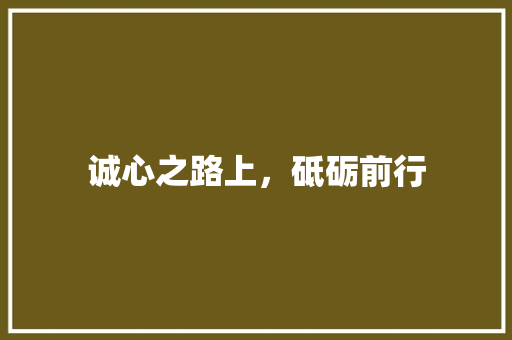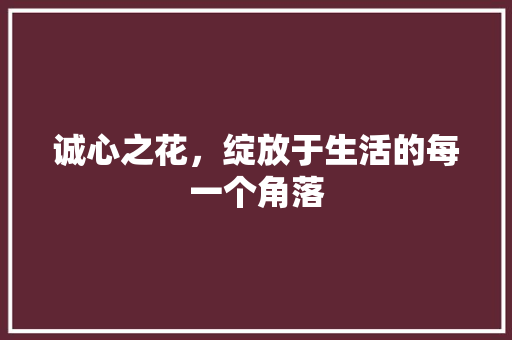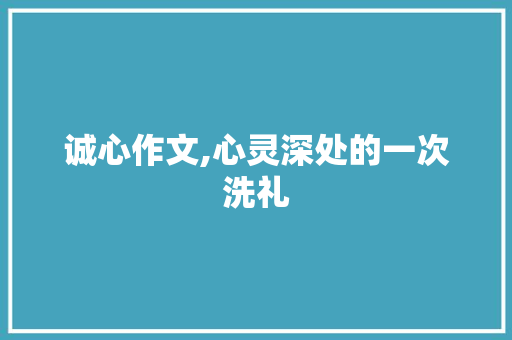那年秋日,我读小学低年级。入夜了,我们一家人,同往常一样,默无一言吃晚饭。一盏戴灯罩的小石油灯,放置在桌子中心。
饭后,各自捡收好碗筷;母亲抹完桌子,就到碗柜案板上洗碗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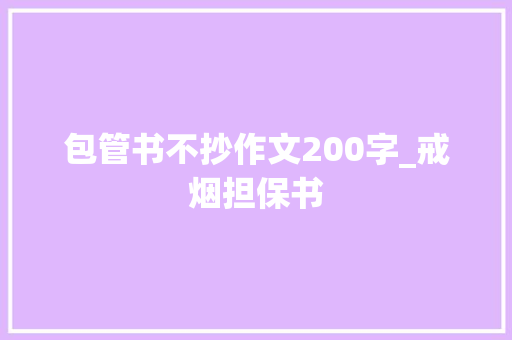
“雄伢子,拿张纸和圆珠笔来!
”父亲坐回桌边座位,溘然说话了。
我走到窗户旁青砖墙前,从挂在一根长“洋钉”上的书袋里摸出圆珠笔和和练习本,在父亲侧面坐下来。
“我念,你写。”父亲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边把石油灯移到我前面。
“担保书”,父亲念道。
我有些莫名其妙。父亲是向来不过问我们兄弟姐妹的事的:一是他在大队戴着“花帽子”(我父亲对够不上乌纱帽的大队干部的戏称),白天黑夜总有开不完的会,管不完的闲事(父亲把调度轇轕称为“管闲事”),在家韶光很少;二是我们姊妹都还“蛮乖”的,以是,纵然他有了点空余韶光待在家里,也只是坐在房内窗下的书桌边,看看书,或记点日常开支帐,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互换。不知今晚是怎么回事?
容不得细想,我连忙随父亲的口述记录起来。
担保书字数不多,当年的小字格子纸不敷一个页面。前面的大意是:我现在跟人一起吸烟,这是一种不良习气,今后一定改正。末了一句,虽已时隔多年,我却还能记得很真切:“往后如果再吸烟,就烧手指头,并关禁闭三天。”“禁闭”二字,头次听到,我不懂,就看着父亲,小声地说那两个字不晓得写。父亲在另一页纸上写好,让我抄下来。写完,父亲看了,小心地把那页纸从我的练习本上撕下来,折半好,放进衣兜里,起身,打动手电筒出去了。
我弟弟当时在哪里,在干什么,我没有了印象。不过,我想,大概他就陪站在桌边,不无担忧地看着父亲和我;大概倚靠在窗台下,期待发落。由于他是我的影子,我干过的所有的“坏事”,他也全都有份。
那时,我们生产队聚族而居在乾嘉年间修造的老宅院里。与我年事相仿的小伙伴有十几个,我们常聚在一起,玩耍吵闹。记不起是谁提出了吸烟玩的主见,得到了大家(包括女孩子)的齐声应和,几天后,不少人的衣兜里都藏了一个包裹着烟丝的小薄膜袋,烟丝来自几个家里有大人吸烟的小伙伴,他们偷出来,分给大家。趁着家里大人们都出集体工去了,我们就凑在一起,各自滚个“喇叭筒”,点上火,装模作样吧嗒吧嗒起来。看着从口里鼻孔里出来的青烟逐步升腾开来,我们彷佛觉得到了大男人才能享受的神仙般的逍遥乐趣。
吸烟玩的闹剧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我写担保书之前,小伙伴们早已不吞云吐雾了,就像婴幼孩童玩玩具一样,玩过之后就丢开了。
我更是在他们之先就不敢吸烟了。隔壁生产队有个同学,他父亲是工人。一天下午,我与他一起放牛,来到一个山坳里的水塘边。把牛綯缠到牛角上,让牛下了水塘,我俩就坐在塘基上看牠们沐浴。他取出一包未启封的“岳麓山”喷鼻香烟,说是偷了他父亲的。他递一根给我,看我鼻孔里不出烟,说是“太不像了”,请教我抽。烟入喉咙,我以为很不舒畅,头晕眼花的,便仰面躺在地上。过了好一阵子,脑壳轻松了,才坐起来。他笑我:你吃不得烟,才吃两口就醉到了。
当年的那一群小伙伴,除三个人之外,其他的人,一贯都不会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