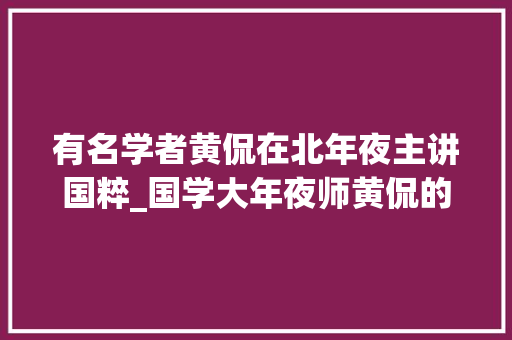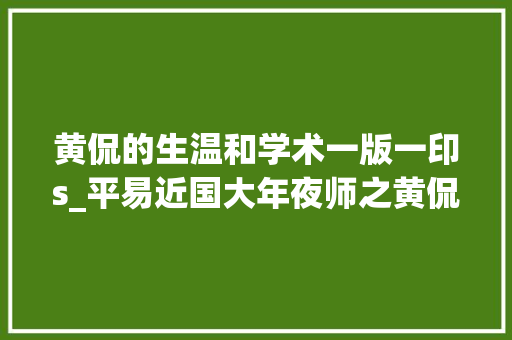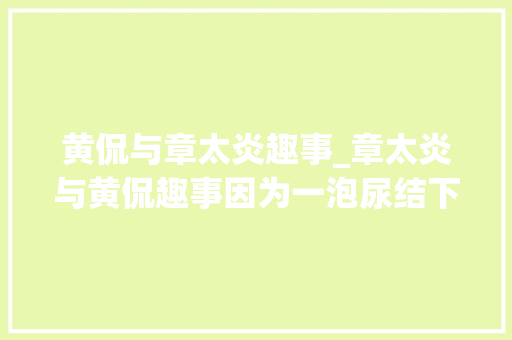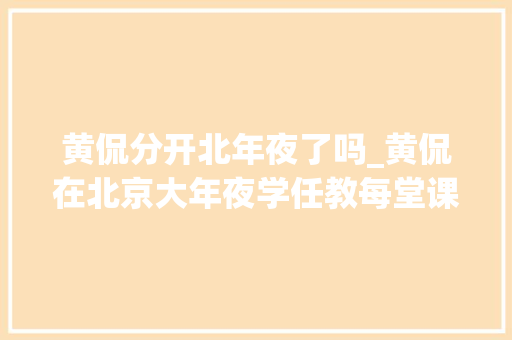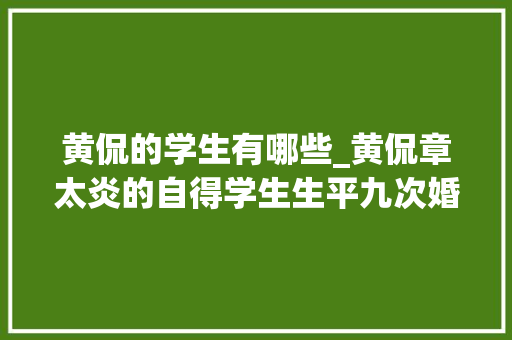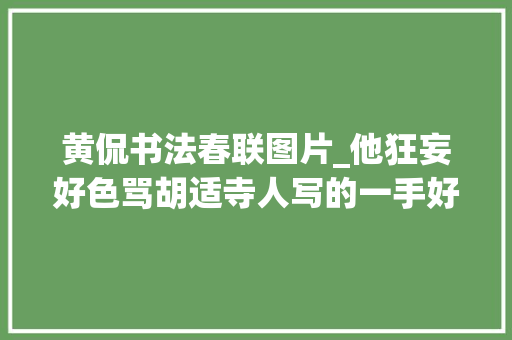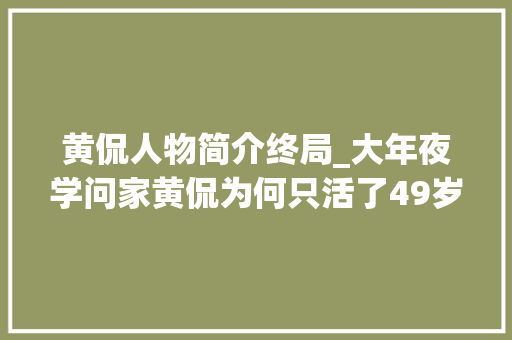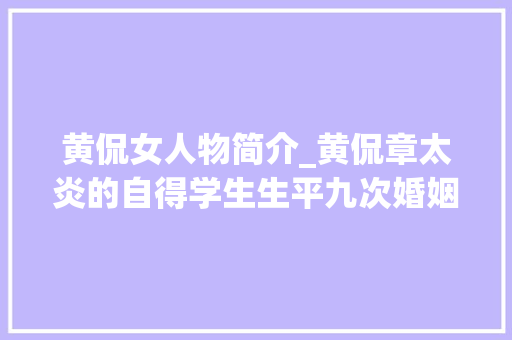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
第三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点上。” 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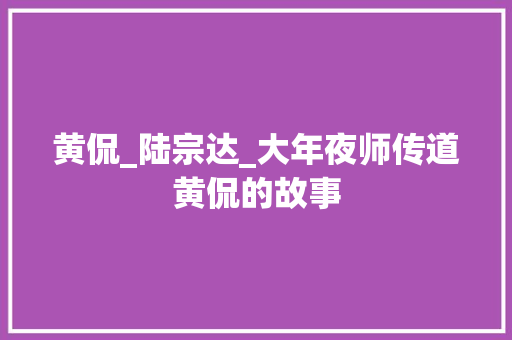
黄侃说:“标点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于心,这笔墨之学,你已得大半,不用再点了。往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再翻这书了。”黄侃将书扔进书堆里,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当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顾说:“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伙头解牛。”
据他的学生回顾,黄师长西席传授教化还有更特殊的,他不是光用措辞教这个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呆板的书,假如一样平常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师长西席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以是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纵然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弗成。”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恳切。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学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逐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赛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以是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逐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作业,准备嫡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往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措辞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传授教化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见告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二十四种。后黄侃又哀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文籍,由于唐以前留传下来的文籍为数不多,随意马虎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今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黄侃并且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揭橥笔墨,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见地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黄侃更因此身作则,五十岁前不著书。
黄侃读书,喜好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负责,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末了,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末了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发言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由于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黄侃生平最大的家私,便是书本。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本,自然是每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冒死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地去买,钱寄出后,每天愿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乃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摧残浪费蹂躏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若何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乃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若何苦劝,开出的报酬多么优厚,黄侃都禁绝许。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以是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劳苦收藏的书本终极却横遭他人挥霍。“一8226;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迁居,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黄侃曾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奋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但慎于著述。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五十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 ”,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个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烦懑,以为不祥之兆。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去世,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谈论:
黄侃五十前不著书,而寿止五十,可惜。
邮购书的那段与我相契合。
教陆宗达圈点说文解字,此学习之法甚妙。
读书是一种独立的传统。就像政治有传统,商业有传统。
谷园
2016.10.28